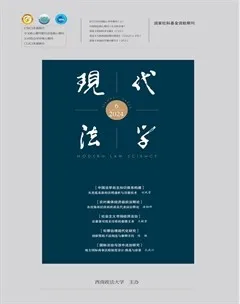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關系的現代化重構
摘 要:自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我國的法秩序中從“類型化法律術語”轉變為“專用型法律概念”,但這一概念所指代的現實對應物一直模糊不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致力于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重建和發展提供新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保障,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重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律關系。為此,應當按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改革目標,著力打破“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理論藩籬和制度迷思,然后按照“經營性—非經營性”標準合理解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相關規定,從而最終建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分別享有并行使部分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制度。
關鍵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集體土地所有權;中國式現代化;政經分離;憲法解釋
中圖分類號:DF413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4.06.05
一、引言
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在農村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將近5億人,不在城鎮落戶的農民工及其家屬有2億人,村民委員會改居民委員會、鄉鎮改街道后,已經成為城市居民但依然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人有2億多。①為了維護數量眾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運行管理,2024年6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以下簡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立法過程中,社會各界對什么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爭議比較大。【參見王春霞:《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分組審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二審稿建議保障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決策管理中的作用》,載《中國婦女報》2023年12月29日,第2版;陳錫文:《當前農業農村的若干重要問題》,載《中國農村經濟》2023年第8期,第15-17頁。】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是因為,雖然現行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了規定,但在廣大農村地區,這種特殊的經濟組織或者沒有建立起來,或者只是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影子”存在(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套班子,兩塊牌子”)。
《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城鄉融合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2-23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區域性經濟組織,包括鄉鎮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此,妥善處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關系,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運行機制的關鍵所在。不過,誠如下文將要揭示的那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在該領域的規定依然存在許多模糊之處。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以下分別簡稱《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在調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關系方面亦存在一些規范沖突。
按照體系融貫的要求,厘清法律規范的內涵、明確各類法律規范彼此之間的關系,是法學研究的任務和使命。鑒于此,本文擬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引,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等法律的相關規范為分析對象,重新研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關系。法律概念既是法律體系的“基石”,也是處于不斷變化和發展中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實踐的“容器”,因此,本文擬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規范內涵和概念變遷史為主線開展相關研究工作。
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術語性質的歷史變遷及面臨的問題
開展法學研究應高度注意“抽象概念思維”與“類型思維”的差異。在前一種思維中,人們需要通過不斷剔除那些彼此具有意義關聯但并不必須組合在一起的“要素”,從而形成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概念。在后一種思維中,人們需要完成的工作并不是剔除而是結合,即需要通過描述事物的整體特征來描述事物的共通性。【參見[德]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全本·第6版),黃家鎮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版,第574、580頁。】基于上述思維和法律術語性質的差異,下文將嚴格遵循“類型—概念”分析框架來梳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法律術語內涵和性質的變遷史,然后,在此基礎上分析這一術語所指代的社會現實在當下面臨的問題。
(一)作為農村中各類合作社統稱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1950年,中華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第1條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工人和城市勞動人民中組織的消費合作社,在農民中組織的供銷合作社,在城市和鄉村小手工業者、家庭手工業者中組織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以及其他經過省以上合作社聯合社批準組織的特種合作社,均為合作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1956年6月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已廢止)第1條則規定:“農業生產合作社(本章程所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都是指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勞動農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組織。”
由此觀之,在20世紀50年代的法律規范中,一方面,“集體經濟組織”屬于對“生產資料所有權已經轉變為集體所有的各類合作社”的類型統稱,而不是具有特定法律內涵的專門性法律概念,現行法所使用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術語在當時所指涉的社會對應物,是農村中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各類合作社,而不是某種特定類型的農村合作社;另一方面,“集體經濟組織”廣泛存在于城市和鄉村的許多行業領域,“城市集體經濟組織”這一術語在當時也被廣泛使用并被社會接受。
存在于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各類合作社,能夠被統一歸屬于“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是因為它們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一,這些合作社均屬于通過生產資料、資本或技術與人的結合而形成的企業類經濟組織。比如,農業生產合作社屬于“社員”與“土地和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的結合,農村供銷合作社則屬于“社員”與“日常消費品、生產資料以及多余的農產品和副業產品”的結合。其二,雖然這些合作社是企業類經濟組織,但并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致力于通過經濟活動實現成員共同經濟利益、消除中間剝削、避免貧富分化。【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ICA)1995年通過的《關于合作社特征的宣言》(The Statement on the Cooperative Identity)提出,“合作社”的本質是“一個由自愿團結起來的人組成的自主聯合體,通過其共同擁有和民主控制的企業(enterprise)滿足成員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需求和愿望”。在1954年4月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胡喬木代表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對《憲法修改草案(修改稿)》進行說明時也指出,“國營企業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集體經濟組織有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這是因為兩種企業的自主權含義不一樣”。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頁。】其三,集體經濟組織與基層社會治理主體在組織功能層面彼此分離,并不存在職能交叉或重疊的問題。比如,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農村而言,行政管理職能由鄉鎮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機構村公所等政治組織承擔。【參見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功能則在于按照“各盡所能,同工同酬,按勞取酬”的原則開展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并履行向國家交納公糧和交售農產品的義務。【參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已廢止)第2條、第5條。】
(二)作為人民公社內設機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1958年之后,一方面,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互助、互利的集體經濟組織”;另一方面,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原則上實行一鄉一社,公社的社長,就是鄉長”【《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1962年9月27日通過,又稱“農村六十條”,已廢止)第1條、第5條、第9條。】。因此,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政經合一”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農村中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各類合作社,與鄉鎮人民政府、村公所等政治機構一道被合并到“在組織生產的同時又組織生活,實行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機構和公社的管理機構的合一”【劉少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 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而作(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載《前進論壇》1959年第10期,第12頁。】的綜合性社會組織之中,成為人民公社的內設機構,無法繼續維持其自身作為獨立經濟組織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定要使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術語,其用來指代各類“社隊企業”也許更為合適。【事實上,目前城市中的集體經濟組織的法律性質依然是企業。比如,現行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第4條第1款就規定:“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以下簡稱集體企業)是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實行共同勞動、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
人民公社體制在社會組織體層面的變化,給農村地區的土地等財產的歸屬帶來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在農業高級合作社體制下,農民要成為合作社的成員,就“必須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已廢止)第11條第2款、第13條第1款。】,即必須通過經濟投入才可以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是,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遷入和長大到十六周歲而入社的社員不要補交股份基金;遷出和死亡的,也不能抽走股份基金”【《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載《紅旗》1958年第7期,第16頁。】。換句話說,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的基本依據是戶籍、年齡、職業等社會因素,而不是財產、技術或資本等經濟因素。由此,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身份與作為行政管理概念的“農村村民”身份,亦無嚴格區分的必要,所謂“政經合一”的基本要義正在于此。
(三)作為專用型法律概念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因為“政社合一”式的人民公社體制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所以在改革開放后迅速解體。到1982年初,“全國農村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2年第8期,第316-326頁。】。為了適應這種社會發展要求,1982年憲法修改委員會提出,應“改變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體制,設立鄉政權,人民公社將只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組織形式。這種改變將有利于加強農村基層政權建設,也有利于集體經濟的發展”【彭真:《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彭真文選(一九四一——一九九○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頁。】。為此,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第95條明確要求在鄉、民族鄉、鎮重新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第8條第1款則規定:“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
由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由憲法修改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術語。【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憲法》第21條第1款也使用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術語。該款規定:“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鼓勵和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街道組織舉辦各種醫療衛生設施,開展群眾性的衛生活動,保護人民健康。”】不過,從術語類型和概念內涵來看,《憲法》第8條第1款第2句所規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然是對第8條第1款第1句中的“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各類生產、供銷、信用、消費合作社”的類型化統稱,而不是具有明確規范內涵的專用型法律概念。另外,該部《憲法》第8條第2款規定:“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第3款規定:“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可見,在1982年,“集體經濟組織”依然廣泛存在于城市和農村,并非農村中獨特的經濟現象或組織類型。
然而,作為純粹經濟組織的“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1982年以后并沒有普遍建立或有效運行。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缺乏作為獨立組織的必要職能。其一,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農業生產勞動從“集體勞動”轉變為“自主勞動”,既不需要集體進行過程化管理,也不需要集體對勞動生產成果和相關收益進行統一分配,因此,“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對于集體成員(社員)不再具有人事工作管理職能。其二,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曾經提出,政社分設后的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職能主要在于,“首先要做好土地管理和承包合同管理;其次要管好水利設施和農業機械,組織植保、防疫,推廣科學技術,興辦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以及其他產前產后服務”。但由于土地承包經營權在相當長的周期內基本保持穩定(第一輪承包期是15年,第二輪承包期是30年),承包地的合同管理并非一項日常事務。同時,農業生產領域的產前產后服務,可以由供銷社、信用社、農工商聯合公司及隸屬于政府的農林技術推廣站、畜牧獸醫站、農業機械站、經營指導站等企事業單位完成,“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農業生產事務領域并非不可或缺。
值得注意的是,1982年的憲法修改委員會既不認為“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當時農村中唯一的集體經濟組織,也不認為“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是落實“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最合理方式。比如,權威憲法解讀意見指出,1982年《憲法》第8條的規定“表明人民公社不是唯一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這就為以后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留下了余地”【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頁。】。由此觀之,當時的決策者對于人民公社解體后如何發展集體經濟并沒有明確的結論,而是希望通過“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經由基層實踐來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組織形式。到1984年時,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依然規定,“政社分設以后,農村經濟組織應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設置,形式與規模可以多種多樣,不要自上而下強制推行某一種模式”。
問題在于,1982年《憲法》除了在第8條、第95條等條文中規定了農村中的組織建制問題外,還在第10條第2款中規定了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問題,即“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由于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組織實現形式尚處于探索之中,集體土地出現了所有權歸屬主體不明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86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已廢止)、1986年6月通過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后續修正或修訂版本,都曾試圖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歸屬主體作出界定。【《民法通則》(已廢止)第74條第2款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8條則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各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訂時,“村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等術語被“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術語取代。2019年,《土地管理法》第三次修正后,第11條最終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的,由鄉(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遺憾的是,相關規定既不清晰,也存在概念循環界定的問題。
出現這種法律發展結果,主要是因為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在全國沒有普遍建立起來,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卻根據1982年《憲法》第111條在全國得以普遍設立。基于上述社會現實,在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起草的過程中,主導性的法律意見認為,“村委會承擔一定的經濟職能,有利于發展農村經濟,也有利于增強群眾的凝聚力,更好地開展村民自治運動”【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201頁。】。因此,該法第4條第3款最終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在全國農村中得到進一步推廣。為了適應這種社會發展情況,1993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和1998年修訂的《土地管理法》徹底刪除了“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兩個術語。到1999年,《憲法》原第8條第1款最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15條修改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參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經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和飼養自留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此從“類型化法律術語”轉變成為“專用型法律概念”,而且這種專用型法律概念不再使用“農業”來限定集體經濟組織的組織職能,而是使用“農村”這一行政區劃或空間概念來描述和界定自身。
雖然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15條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界定為專用型法律概念,但是在過去20余年間,該術語既存在“憲法上有規定,現實中不知為何物”的問題【比如,當內蒙古自治區的一個鄉人民政府將集體土地的所有權確認給當地一家磚瓦廠時,土地管理部門主張這種所有權確認結果違法,理由是磚瓦廠并非法律所承認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但當地實際上只有村民委員會,并無除鄉鎮企業(原隊社企業)以外的其他集體經濟組織。參見[荷]何·皮特:《誰是中國土地的擁有者——制度變遷、產權和社會沖突》(第2版),林韻然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270頁。】,也長期面臨“憲法上有地位,民法上無人格”的尷尬。為了解決后一問題,201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已廢止)第96條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與機關法人、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均確定為獨立的“特別法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完全繼承了上述規定。但“特別法人”亦屬于類型化統稱性術語,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特別法人的“特別”之處,依然處于模糊不清的狀態。
三、“集體土地所有權”術語內涵的歷史變遷及面臨的問題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律關系之所以模糊不清,除了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這一術語自身內涵及所指代的社會現實處于持續變動之中有關外,“集體土地所有權”這一術語及所指代的社會現實不斷發生變化,也是重要的因素。其中的歷史變遷常常被人忽略或低估,因此應當予以著重分析。
(一)我國法秩序建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原因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土地國有化而非集體化才是社會化生產及人口增長和集中的必然要求,因為“不管合作勞動在原則上多么卓越,在實際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就始終既不能阻止壟斷勢力按照幾何級數增長,也不能解放群眾,甚至不能顯著地減輕他們的貧困的重擔”【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列寧則進一步指出:“土地國有化就是全部土地收歸國家所有。所謂歸國家所有,就是說國家政權機關有獲得地租的權利,并且由國家政權規定共同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規則。”【列寧:《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11-12月)》,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1-302頁。】正是在上述政治理論的指導下,蘇聯不僅建立了領土與國家土地所有權合二為一的法律制度【1918年蘇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第3條第1項、第2項規定:“為實現土地社會化,廢除土地私有制,宣布全部土地為全民財產,并根據土地平均使用的原則無償地交付勞動者使用。”】,而且明確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領土不僅是國家權力的空間界限,而且是國家獨享的所有權之標的,是全民的財產”【[蘇]卡山節夫等:《蘇聯土地法教程》,杜晦蒙譯,大東書局1951年版,第100頁。】的所有權理論。依據這種可被稱為“領土型國家土地所有權”的理論,雖然蘇聯也有集體農莊等集體經濟組織,但這些組織并不享有土地所有權,只享有該農莊范圍之內土地的經營管理權。
我國沒有建立“領土型國家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而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建立了國家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這兩種相互獨立的土地所有權。直到今天,根據現行《憲法》第6條的規定,“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共同構成了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于這種制度安排,1956年時,國務院指出:“土地歸合作社集體所有,容易為廣大農民所接受,也同樣可以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正常進行;如果實行土地國有,反而可能引起農民的誤解。”【廖魯言:《關于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說明》,載《中華人民共和Js9Kzbbk+LkxFPRIbB+wa3qIZoKiWmjVd+fPFUzL+7o=國國務院公報》1956年第29期,第767頁。】在1982年修改憲法的過程中,又有許多意見主張將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全部國有化,但主導性意見認為,“我們民主革命沒收封建土地分給農民,現在要把農民的土地沒收歸國有,這震動太大。如果國家需要土地,可以通過土地征用解決”【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4、412、417、425-426頁。】。
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業合作化時期(1951—1956年),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其一,這種土地所有權與村公所土地行政管理權的客體并不完全一致,因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屬性是一個從事農業生產的經濟組織而不是社會行政管理組織,其只吸收農業用地、耕畜、大型農具等主要農業生產資料作為自身所有的財產,宅基地、辦公用地等生活資料及非主要農業生產資料并不入社。【比如,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6年6月30日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已廢止)第16條第2款的規定,社員原有的墳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其二,集體土地所有權依然屬于私法中的財產所有權,因為“社員有退社的自由。要求退社的社員一般地要到生產年度完結以后才能退社。社員退社的時候,可以帶走他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數量和質量的土地,可以抽回他所交納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資”【《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已廢止)第11條。】。
(二)“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形成及延續至今的原因
1958年之后,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政經合一”體制,因此,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權利客體從農村中的農業用地擴展至宅基地、道路、未利用地、公共服務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等人民公社行政區劃范圍內的所有土地【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1962年9月27日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第21條第1款規定:“生產隊范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空間范圍與人民公社的行政區劃范圍實現了高度重合。特定人民公社行政區劃范圍之內的所有土地空間均屬于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客體,因此,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與蘇聯“領土型國家土地所有權”高度相似的特征。這種特殊的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財產法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與“行政區劃意義上的政權管理空間”的混合特征,因此,我們可將其稱為“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在這種特殊的土地所有權條件之下,由于土地逐步蛻變成為可以通過行政手段進行調配和劃撥的自然資源,其財產權屬性不彰,因此,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主體被理解為在人民公社生活和從事勞動生產的全體集體成員。而且,所謂的“全體集體成員”既包括過去和現在的全部集體成員,還包括未來潛在的集體成員。同時,這些“未來潛在的集體成員”無須通過資產投入,而是可以僅基于出生、血緣、婚姻等因素就成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的組成部分。
1982年《憲法》將“政經分離”“政社分設”作為自身指導原則之后,“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歸屬主體面臨著重新厘清的問題。畢竟,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與“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等經濟組織分離為相互獨立的組織之后,如何合理劃分原人民公社體制下各類集體財產的具體歸屬主體,就成為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然而,“政經分離”“政社分設”改革并未在組織法層面和財產法層面同步推進。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公社在當時還是普遍存在的,一下子取消了,可能會在農村引起混亂,人民公社的財產、生產資料、生產秩序就可能像成立人民公社時那樣引起混亂和破壞。要取消人民公社,也需要有過渡期”【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親歷新時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頁。】。這里所謂的“需要有過渡期”并不是說“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無須改革,而是說“政社分開的具體實施,這是一件細致的工作,各地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不要草率行事”【彭真:《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彭真文選(一九四一——一九九○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頁。】。
在1982年修改憲法的過程中,主導性意見曾提出,“現在中央發文件,政社分開,其他的關系不變。要變的話,由農民自己去變”【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頁。】。由此可見,當時的決策者希望通過進一步改革和實踐探索來尋找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主體的具體改革方案。遺憾的是,由于1986年以后國家開始“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頁。】,農村土地所有權制度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淡出了決策者的視野。
(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給集體土地所有權帶來的挑戰
如果農村中依然只存在基層群眾自治組織這一種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組織類型,那么,“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改革問題也許還可以繼續擱置。但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頒布意味著,農村中同時存在兩種可以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組織,需要對這兩種組織在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和行使領域進行職權和職責劃分。
上文提到,雖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2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但又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眾所周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僅適用于耕地、草地、林地等農業用地,而作為地理空間的“農村土地”并非全部由農業生產用地構成,其還包括大量的生活用地(如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公共設施用地(如道路、橋梁、供電、防洪等用地),公共服務用地(如行政辦公、科教文衛、社會福利設施、文物古跡等用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以及未利用地(如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那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究竟只代表成員集體行使農業用地的所有權,還是行使農村區域全部土地的所有權?
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5條的規定來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土地領域“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的對象,不僅包括發包農村中的農業用地,還包括辦理農村宅基地申請、使用事項,使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或者通過出讓、出租等方式交由單位、個人使用,分配、使用集體土地被征收征用的土地補償費等事宜。【另外,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36條的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集體所有的建筑物、生產設施、農田水利設施,以及集體所有的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通等設施和農村人居環境基礎設施,都屬于集體財產,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但問題在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亦有權討論并決定“土地承包經營方案”“征地補償費的使用、分配方案”“以借貸、租賃或者其他方式處分村集體財產”“從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等事項。【參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2018年)第24條第1款、第25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64條第1款規定:“未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可以依法代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該規定是否意味著,當某個區域成立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后,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將徹底退出各類集體土地的所有權行使領域?
另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64條所規定的“代行”顯然無法解釋為“代理”,因為在法律層面,一個尚未設立的組織是無法被代理的。但如果將此處的“代行”解釋為“代表”,那么,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成員集體的關系就需要厘清,因為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5條的規定,還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事實上,雖然“農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這一規定,已經作為我國法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斷得到強化【參見《民法典》第261條第1款。另外,根據《民法典》第262條的規定,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依法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但集體土地所有權究竟屬于獨立的“組織體”(集體成員集體—所有),還是屬于“未組織化的個體農民的集合所有”(集體成員—集體所有),答案一直并不明確。
四、農村集體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關系的模式選擇
從現有研究來看,學界多從組織法角度尋找重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關系的法律路徑。參見高圣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中的四對基本關系》,載《政法論叢》2024年第5期,第33頁;夏沁:《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集體資產的經營管理權能》,載《學海》2024年第3期,第25頁;劉歡:《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的終止》,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第86頁;屈茂輝:《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制度三論》,載《現代法學》2022年第1期,第162頁。但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改革目標來看,該領域實際上還存在另外一種解決思路,即通過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集體土地財產運行機制,來優化和完善農村土地歸屬主體的組織和運行方式。為此,下文擬以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歸屬主體和權利行使方式為主線,分析農村不同集體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關系各種不同模式的利弊,并在此基礎上尋找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要求的法律解決方案。
(一)模式Ⅰ:一個集體土地所有權+一種組織單獨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
這種模式的特點是:(1)將特定農村地域范圍內的全部土地理解為一個統一的土地所有權,并要求將“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確定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2)由于“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被理解為“未組織化的個體農民的集合”,無法直接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被設立為具有法律人格的獨立主體,并由后兩者代表“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3)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代表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優先序”。如果特定農村地區成立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行使所有權,否則,由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代表“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行使所有權。
自1982年以來,模式Ⅰ在我國的法律中不斷得到確認和鞏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64條的規定也存在模式Ⅰ的影子。不過,當下不宜繼續按照這種模式來處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集體”在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和行使領域的法律關系。理由有二:其一,雖然模式Ⅰ在組織法層面落實了現行《憲法》自1982年以來所確定的“政經分離”“政社分設”精神,但這種組織法層面所進行的改革,會因為財產法層面“經營性土地—非經營性土地”的混雜而失去應有的意義乃至流于形式。在這種模式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應當經營管理農村中的經營性土地(如農業生產用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還需要承擔農村中所有生活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公共服務用地及未利用地的管理職責,而后一種“管理”屬于公法意義上的行政管理而非私法意義上的經營管理。其二,如果按照模式Ⅰ來理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集體”在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和行使領域的法律關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應繼續實行“政社合一”體制。但如此一來,不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1條確立的“規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運行管理”立法目標難以實現,其第5條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依法代表成員集體行使所有權,履行支持和配合村民委員會在村黨組織領導下開展村民自治職能的規定難以落實,而且有違我國1982年《憲法》設定的“政經分離”“政社分設”原則。
(二)模式Ⅱ:一個集體土地所有權+兩種組織分別代表行使部分所有權
該模式的基本內容可總結為:(1)將特定農村地域范圍內的全部土地理解為一個統一的土地所有權,并將“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設定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人。(2)“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依然是由個體農民組成的“無法律人格的聯合體”而非獨立的組織。該“農民集體”享有但并不直接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而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代表“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3)與模式Ⅰ不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并不單獨全權代表“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行使全部集體土地的所有權,而是按照“經營性—非經營性”標準分別代表“作為整體的農民集體”行使部分集體土地所有權。【在現有理論研究成果中,尚未發現明確支持模式Ⅱ的主張。不過有學者提出,農民集體可以將能用于投資的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等用益物權通過出資方式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作為后者的財產,從而在農民集體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形成以集體經營性土地為標的的投資關系。參見于飛:《“農民集體”與“集體經濟組織”:誰為集體所有權人?——風險界定視角下兩者關系的再辨析》,載《財經法學》2016年第1期,第50頁。】
該模式具有以下優勢:(1)在理論層面,這種模式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的理論藩籬,又部分廓清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集體”三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因此,該模式有助于在組織法和財產法兩個層面繼續落實現行《憲法》所確定的“政經分離”“政社分設”原則。(2)在法律規范理解和適用層面,這種模式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40條第1款建立的規則保持了一致,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將集體所有的經營性財產的收益權以份額形式量化到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作為其參與集體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據”。由此,集體經營性土地由三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農民集體行使所有權,非經營性土地則由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代表農民集體行使所有權。(3)這種模式還有助于落實“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防止內部少數人控制和外部資本侵占”【《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發〔2016〕37號)。】等改革要求。
不過,這種模式的缺點也很明顯。一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按照產權明晰的原則代表農村集體行使經營性土地所有權,用于識別和確認村民身份的出生、戶籍等標準,就無法繼續用于識別和確認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因為經營性土地的權利行使和收益分配需要按照財產權所要求的“產權明晰”原則運行。但是,如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與農村村民的構成方面出現重大差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在實踐中就無法代表“同一個農民集體”。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有學者認為,可以考慮將集體資源性資產的所有權歸屬主體確定為農民集體,而將集體經營性資產的歸屬主體確定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見高海:《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關系之二元論》,載《法學研究》2022年第3期,第30頁。】這種方案并不科學,也難以落實。原因在于,這種方案需要同時對“農民集體”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進行組織化構建,而這不僅意味著需要在《民法典》中增加“農民集體”這一新的特別法人類型,還需要同時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集體”三個特別法人的組織職責和成員資格。當然,如果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視為法人化和實體化的“農民集體”的內部組成機構,上述問題就將不復存在,但這種思路要求在法律層面制定“農村集體組織法”而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同時,現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民法典》關于“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規定,還應修改為“村民委員會是農民集體組織的內部機關”。即使暫不考慮此種思路是否超出了目前的立法規劃,以及是否會帶來“農民集體實體化二遍苦”【陳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構眾說窺略——有關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律形式變革的稿件編后感》,載《法學研究》2022年第3期,第60頁。】的問題,僅從合憲性角度來看,這種方案亦不可行,因為現行《憲法》反對將“農民集體”發展成為“政社合一”“政經合一”的組織。
(三)模式Ⅲ:兩種集體土地所有權+兩種組織分別享有部分所有權
這種模式的基本內容是:(1)在特定的行政村內部,農民基于不同的社會需求和社會目標,可以組建自己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組織,這些組織體都屬于“農民集體”的法律實現形式。(2)《憲法》第10條第2款中的“集體所有”,應被解釋為“由農民集體成員所形成的集體組織—集體所有”而非“作為松散個體的集體成員集體—所有”。(3)“經營性—非經營性”集體土地分別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所有,其所有權的來源分別是這兩個組織各自成員的授權。(4)具體到特定的行政村內部,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所擁有的部分集體土地所有權具有“統一、唯一”的特征,只能落實為一個統一的集體土地所有權,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部分集體土地享有的所有權,可以根據尊重歷史、兼顧現實、程序規范、群眾認可的原則,落實為一個或多個集體土地所有權。
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其一,可以通過打破人民公社時期所形成的“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理論藩籬,重構農村各類集體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法律關系,從而在堅持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為集體經營性土地的市場化改革提供堅實的財產法基礎。其二,可以在組織法層面更加清晰地界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集體”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說,“農民集體”只應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而非獨立的法律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則是各自獨立的法律主體(特別法人),分別對集體經營性土地和非經營性土地享有并行使所有權。
這種模式也會遇到理論層面的質疑和規范層面的挑戰,不過,這些質疑和挑戰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首先,有研究者從民法層面提出,基于土地所有權的排他性,特定地域范圍內只有一個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只能成立一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此,每一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特定地域范圍內都是唯一的、排他的,同一地域范圍內可能存在其他經濟組織,但不能再成立另一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參見何寶玉:《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歷史沿革、基本內涵與成員確認》,載《法律適用》2021年第10期,第15頁。】“所有權的排他性”原則確實要求同一塊土地上不應當設立兩個以上的土地所有權。不過,前述判斷不應被理解為同一個行政區劃或基層群眾自治空間范圍內只能設立一個集體土地所有權。從當前的實踐層面來看,在一個行政村內部,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內集體經濟組織分別對不同地塊享有土地所有權,亦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因此,只要在空間層面厘清鄉集體經濟組織、村集體經濟組織、村內集體經濟組織及它們與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各自土地所有權的邊界,并不存在一塊土地上擁有雙重或多重所有權的問題。
其次,有人可能會從歷史角度質疑,既然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最初源于個體農民或農戶的私有土地入股,為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只擁有集體經營性土地而不是特定地域范圍內所有農村土地的所有權?這種質疑不能成立,因為從集體土地“三級所有”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農村中的許多道路、公共服務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及未利用地,既不是私人所有的土地,也不屬于初級合作社和高級合作社所有,它們在1958年以后被一次性納入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范圍之內并延續至今。因此,就組織體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而言,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擁有農村區域全部土地的所有權。同時,就像有學者主張的那樣,只有經營性資產才可能產生經營性收益。非經營性資產不宜納入折股量化的范圍,而應當由集體統一管護運營,讓其成為集體成員的公共服務效益,不能依據股份分配集體公共服務,或者因為股份額的不同在公共服務享受上有所差異。【參見韓松:《農民集體成員的集體資產股份權》,載《法學研究》2022年第3期,第5頁。】因此,非經營性集體土地歸屬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所有,既具有歷史合理性,也具有現實必要性。
再次,還有人可能會提出,集體土地屬于現行《憲法》第12條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而非其第13條所規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因此,“行政區劃型集體土地所有權”正是現行《憲法》所規定的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本質性特征,不能改變。這種意見亦不能成立。理由在于,我國的集體土地所有權確實具有特殊性,因為其并不是“私人所有權的標的”【相比而言,雖然法國法中也有“集體所有權”這一術語和相關制度,但《法國民法典》將那些用于私法人和公法人的集體財產視為“某種個人所有權的標的”,并要求法人的集體所有權同樣服從個人所有權的各項制度。參見[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爾:《法國財產法》(下),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648-650、665-667頁。】,而是致力于發展國家生產力的“生產關系的調整器”【[俄]Я.Л.別爾曼:《馬克思主義與民法典——蘇俄人民司法委員會民法典草案制定之探討》,宮楠譯,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23年第1期,第70、79頁。】。但上文梳理的歷史發展脈絡表明,現行《憲法》并未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主體、權利客體及權利運行方式作出明確的決斷,而是希望在此領域保持憲法規范的開放性,通過后續的改革和探索來形成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集體土地所有制。集體土地所有權“統一、唯一、不可分割性”只是一種未經反思的粗糙觀念,其既無法適應現代工商業社會中社會主義公共財產自身的復雜性、多元性及功能差異性要求,也不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性要求。【有研究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是:一方面,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確保市場經濟的發展增強和鞏固公有制的地位,降低市場失靈帶來的風險,促進社會主義的平等價值的實現。這種研究結論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參見韓大元:《中國憲法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范結構》,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2期,第19頁。】
最后,只要現行有效的法律得到嚴格落實,即使按照模式Ⅲ建立“經營性集體土地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所有權,非經營性集體土地由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制度,亦不會脫離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的軌道。理由是:其一,非經營性集體土地自身不能進入市場流通。經營性集體土地歸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之后,《土地管理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民法典》等法律既禁止此類集體土地所有權轉讓、抵押或擔保,也禁止將集體土地所有權分割為個人所有,因此,可以防止集體內部少數人控制的問題。其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6條第2款所規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適用有關破產法律的規定”,也可以有效避免外部資本對集體土地的侵占。事實上,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就曾提出,“力爭用3年時間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證確認到每個具有所有權的農民集體經濟組織”【《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2009年12月31日)》,載《人民日報》2010年2月1日,第1版。】,只是這種政策主張沒有明確哪些類型的集體土地所有權應當確權登記給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以,最終的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只能采用“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按‘××村(組、鄉)農民集體’填寫”【《國土資源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財政部、農業部關于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的若干意見》,載《中國國土資源報》2011年11月10日,第2版。】方式進行落實。
在村民委員會與集體經濟組織的關系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是否支持本文提出的“兩種集體土地所有權+兩種組織分別享有部分所有權”模式?從該法的起草說明來看,答案應當是肯定的。因為起草者明確指出:“按照憲法和有關法律、黨規的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均為特別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成員集體行使集體財產所有權,主要負責經濟事務;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主要負責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兩個組織在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下各司其職,相互配合,相互支持。”【陳錫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草案)〉的說明——2022年12月27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24年第4期,第598頁。】
不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要負責經濟事務”和“村民委員會主要負責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這個標準依然比較模糊。結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構建產權明晰、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改革目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的相關規定應當作如下解釋:首先,該法第36條第2款中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應當解釋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而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由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依法代表“成員”而非“成員集體”來集體行使集體土地等財產的所有權。其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作為兩個不同的組織,分別對集體經營性土地和非經營性土地享有并行使所有權。同時,未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64條的規定依法代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行使對經營性土地的經營職能。最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第19條第3款規定了“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得改變集體土地所有權”,其規范要求在于“不得因為設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而將集體土地所有權分割為成員私人土地所有權”,而不在于禁止將集體土地所有權按照“經營性—非經營性”標準劃分為不同類型的集體土地所有權。
五、余論
當然,如果按照“兩種集體土地所有權+兩種組織分別享有部分所有權”模式來理解和適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并借此重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集體土地所有權之間的法律關系,就需要在集體土地領域明確“經營性土地—非經營性土地”的分類標準和運行規則。在此領域,大陸法系所發展出的“公產—私產”法學理論和法律技術具有啟發意義。【參見程雪陽:《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產權行使機制的完善》,載《法學研究》2018年第6期,第151頁。】就我國農村地區的集體土地所有權的歸屬和行使而言,“經營性集體土地”主要由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承包地、可供有償出讓的宅基地及其他可進入市場流通的未利用地構成,這些土地可以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享有并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其他不宜進入市場流通的農村生活用地(如無償分配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公共設施用地(如道路、橋梁、供電、防洪等用地),以及公共服務用地(如行政辦公、科教文衛、社會福利設施、文物古跡等用地),則可以根據歷史和習慣,繼續由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或鄉鎮人民政府分別享有并行使集體土地所有權。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中央文件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資源”【《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發〔2016〕37號)。】界定為資源性資產,但這種分類方法主要是一種政策性表達。從法律表達和規范實施層面來看,“資源性資產”這一術語主要用于描述那些尚未進行開發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一旦這些資源可以被人類穩定地開發和利用,就需要根據各類自然資源自身資源秉性和利用價值分類納入“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框架。事實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也采用了這種法律表達方案,其第36條、第40條共同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資源性資產中,可以依法入市、流轉的財產用益物權,屬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性財產。ML
Modernizati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CHENG Xueyang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Suzhou University,Suzhou215006,China)
Abstract:Since th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in1999,“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have gradually changed from“typed legal terms”to“special legal concepts”in China’s legal system,but the actual counterpart of this concept has been vague.The Law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new legal framework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D8bmdDSs+LFDkhOZGeUHFA==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but this legal goal can only be effectively realized by reconstructing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First of all,we should follow the reform goal of“developing a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building the clear property right and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mechanism,and granting farmers more adequat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sts”propos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strive to break the theoretical barriers and institutional myths of“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type”.Then,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should be reasonably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operational or nonoperational”standard,so as to finally establish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the rural grassroot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respectively enjoying and exercising part of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Chinese modernization;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constitution interpretation
本文責任編輯:邵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