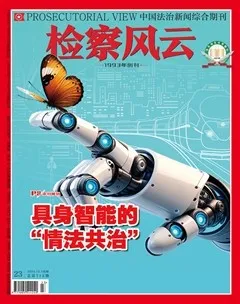以科學合理的考核助力高質效辦案

王延祥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三級高級檢察官,上海市檢察機關“批捕辦案能手”,二分院優秀公訴人,復旦大學法律碩士,全國檢察理論研究人才。
最高檢強調:取消一切不必要、不恰當、不合理考核,并不是取消所有考核,更不是不要管理、放任“躺平”。筆者認為這正是一個契機,對現有的考核制度進行調整和優化,以科學、合理的考核機制,促進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高質效辦案,不斷提高檢察管理科學化水平。
10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檢察院就“一體抓好檢察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質量管理,推動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落到實處”召開專題電視電話會議。最高檢黨組決定取消一切對各級檢察機關特別是基層檢察機關的不必要、不恰當、不合理考核,不再執行檢察業務評價指標體系,不再設置各類通報值等評價指標,不再對各地業務數據進行排名通報,一體抓好“三個管理”,是落實黨中央關于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決策部署的重要舉措,有利于構建更加科學合理、切合各地實際的檢察管理制度,引導各級檢察機關、廣大檢察人員樹牢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切實把主要精力放到法律監督的主責主業、履職辦案的本職本源、高質效辦案的價值追求上來,更好地回應基層呼聲,推進基層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
壓縮指標數量
檢察機關的考核指標品種較多,包括檢察業務指標、綜合工作指標、公共目標指標等。指標設定的出發點是好的,旨在以考核方式既能提高辦案質量,又能落實專項任務、強化檢察管理、培養專業人才。但是,在考核運行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一是考核層級上層層加碼。如,最高檢設定了38項39個檢察業務指標,但各地在落實中又增加了“本土化”指標。二是考核內容上名目繁多。如,各地在業務指標外又設定了各種綜合性考核指標。三是考核方式上剛性較強,給基層檢察人員造成了一定的壓力。四是考核結果用途局限,考核結果主要用于院排名和被考核人員獎金發放。五是考核體系尚不能完全涵蓋檢察官的業績,在提拔任用干部時,還需要考察其是否獲得過市級優秀公訴人、辦案能手等。為此,應當建立符合檢察工作規律的考評機制,去除那些違背高質效辦案本質要求的考核指標和方式。
首先,考核指標要控制總量。根據最高檢“只減不增”的指標精簡優化要求,應當對“屬地化”指標進行系統梳理,刪除不易客觀反映辦案質效的指標。對于考核指標,應當通過上級院備案審查制度。其次,考核項目“問計于民”。在考核項目的設定上,應當確保檢察人員參與,充分聽取檢察人員的意見,通過座談會、調查問卷等方式,聽取被考核人員的意見,以保證考核項目貼近檢察工作實際。再次,考核事項同類合并,對于近似和相似的指標可以同類合并,如,監督效果相同且履職方式相近的考核指標可以合并為一類。同時,對指標的合并與去留,還需要透析其后的法理基礎。最后,多部門可以聯合考核,以提升效率。
優化考核流程
為了提升考核質效,還應當聚焦過程精簡,讓檢察人員輕裝上陣,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高質效辦案和高質效監督上,辦實事、促發展。
其一,簡化考核程序。檢察考核工作,除了需要報送表格和清單外,還需要提交對應的每一項指標完成情況的證明材料。筆者認為,對于宏觀指標,只要提供簡要說明即可;對于微觀指標,盡量減少證明材料。同時,盡量推行電子材料,通過考評信息系統上傳即可。其二,實行一考多用。一方面應當優化整合多部門、多條線、多項目的考核,推進“多考合一”,另一方面檢察考核材料應當實現互聯互通,實現“一考多用”,防止多頭考核和重復考核。其三,降低考核頻率。在考核時間上,有季度考核、年中考核、年度考核等。為把握考核實體效果,應推進考核“瘦身”,減少考核頻次。其四,公開考核結果。對檢察人員的考評過程、考評依據和標準、考評組成人員等事項,應當向檢察人員公開,讓其了解自身所處位置和長項、短板,查漏補缺并改進工作。
注重結果導向
檢察考核的目的,是為了發現存在的問題,檢驗檢察工作成效,以促進高質效辦案。如果單純以留痕多寡、上報材料數量為標尺,會助長形式主義。因此,進一步完善考核方式,應當由考材料、查痕跡,轉向考成效、重實績、看潛績。
其一,考評機制應當符合司法規律。檢察“產品”呈現為“四大檢察”案件,不能簡單地以計時、計件方式衡量。因此,應當堅持定性定量結合,突出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定性,即通過數據分析研判,發現檢察工作整體性和趨勢性問題,并提出前瞻性對策,發揮數據的校驗功能;定量,即考察辦案數量、辦案時間、延伸工作等,發揮數據的評價功能。對于難以量化的檢察綜合業務,應當以辦文、辦事、辦會的效果來認定。其二,考核指標、考核工作應當發揮導向和激勵功能。其三,考核結果應當以外部正面評價為標準。外部正面評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本院以外的檢察機關,即上級檢察機關和條線對本院的評價、其他檢察機關對本院的總體評價和公認度;二是檢察系統外部,即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的感受度、獲得感和滿意度。其四,以精準“畫像”推進結果運用。從檢察官融合履職、組織需要、群眾感受度的視角,對檢察官進行全面性、精細化的“畫像”。在考核廣度上,除了辦案以外,還應當涵蓋全面履職的內容;在深度上,除了受案數、審結數、辦理時間等基礎性指標,還應嵌入案件類型、難易程度等數據設計。“畫像”結果應當與干部選任、評先評優及追責懲戒相結合,以提升辦案質效。
強化數字賦能
在檢察考核工作中,應當在明確功能定位的基礎上,深化人機交互,通過數據比對和碰撞,實現智能化和精準化。
第一,明確功能定位。數字化考核系統應當以檢察人員全面發展和檢察院整體實力提升為目的,數字化設備應當通過不斷“深度學習”,提供平等高效、智能便捷的服務,提升算法的精確度;系統操作人員應當通過組織培訓,深化人機交互,加強監督監管,以構建不受時空限制的檢察考核網。第二,豐富應用場景。在設備智能化硬件提升的基礎上,打通縱橫兩方面的業務條線壁壘,構建立體化考核載體和平臺。在應用場景中構建層次化的指標體系,以促進高質效辦案的核心指標為中心,以檢察綜合履職的基本要求為半徑,使考核網絡既能覆蓋檢察監督的方方面面,又能在檢察網絡中凸顯檢察生態的重心和要求,以類型化引領專業化,實現高質效辦案的目標。第三,優化精準匹配。檢察工作的職業倫理和法律技能具有特殊性,智能和數字設備應當在海量數據沉淀和算法基礎上,以檢察工作的專業性為邏輯起點,通過對海量數據信息的甄別,提煉出符合檢察規范和法律邏輯的應用范式,通過精準識別,將源源不斷生成的檢察履職數據資源與考核指標的設置進行精準比對,強化人工智能和考核的匹配度。第四,動態迭代升級。檢察工作的優劣,關鍵在于是否契合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為此,應當對數字化考核應用中的模塊,適時適度進行改造和優化,建立符合群眾需求的法律指標,推進智能考核轉型升級,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需要,引領檢察辦案和監督專業化。通過動態調整考核指標設置,實現“供給側”和“需求側”有機融合,既能夠符合檢察工作的發展愿景和檢察人員的預期訴求,又能夠將檢察制度優勢借助數字化賦能轉化為“三個效果”相統一的結果。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編輯:沈析宇 1755562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