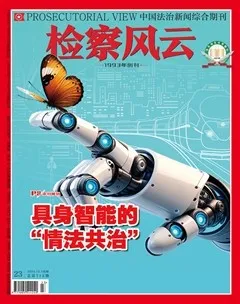新質(zhì)生產(chǎn)力與新人口紅利
發(fā)展新質(zhì)生產(chǎn)力,對人力資本提出了新的需求,特別對高素質(zhì)的技術(shù)技能型、管理型及創(chuàng)新型人才數(shù)量、類型尤其是質(zhì)量都提出革命性要求。為正確理解和有效回應(yīng)這些新需求,最大程度化解新質(zhì)生產(chǎn)力與其日益增長的人力資本需求之間不相適應(yīng)的矛盾、促進二者良性循環(huán),需要以產(chǎn)業(yè)的視角,基于人力資本與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的互動機理,創(chuàng)建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資本開發(fā)策略體系。
在系統(tǒng)性制度安排下,持續(xù)提高人力資本積累、提升全要素生產(chǎn)率、保持較高投資回報率,通過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持續(xù)創(chuàng)造“新人口紅利”,從而破解中國經(jīng)濟在特定發(fā)展階段“成長的煩惱”。
新質(zhì)生產(chǎn)力應(yīng)運而生
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始終緊密相連。站在全球與產(chǎn)業(yè)角度看,蒸汽機、電氣化、信息化革命分別改變了之前的生產(chǎn)模式,提升了經(jīng)濟生產(chǎn)效率,每一次產(chǎn)業(yè)變革都能促使經(jīng)濟在一個時期內(nèi)高速發(fā)展;而隨著生產(chǎn)模式逐漸成熟,當(dāng)時的傳統(tǒ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空間逐漸縮小,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與生產(chǎn)方式實現(xiàn)一次次迭代與升級。
如今,人工智能(AI)、機器人、物聯(lián)網(wǎng)、自動駕駛汽車、3D打印、納米技術(shù)、生物技術(shù)、材料科學(xué)、能源儲存、量子計算機等新技術(shù)群體出現(xiàn),吹響了新技術(shù)革命的集結(jié)號。
每一次新工業(yè)革命,無不以創(chuàng)新為基礎(chǔ)孕育新的產(chǎn)業(yè)和新的業(yè)態(tài),第四次工業(yè)革命概莫能外。新質(zhì)生產(chǎn)力既包含新的知識、技術(shù)、發(fā)明、創(chuàng)造引領(lǐng)下的新產(chǎn)業(yè),也包括通過業(yè)態(tài)融合而產(chǎn)生的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這些新產(chǎn)業(yè)、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都是時代變革中優(yōu)秀的可愛靈魂孜孜不倦的創(chuàng)新產(chǎn)物。一批批掌握技術(shù)和駕馭市場的造物者們,正創(chuàng)造出經(jīng)濟界的一個又一個新物種,共同構(gòu)成了生動鮮活的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生態(tài)。

世界正經(jīng)歷的新工業(yè)革命即第四次工業(yè)革命,國內(nèi)謂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ǎn)業(yè)變革。與前三次工業(yè)革命有所不同的是,此次變革讓人力資本、知識、管理等生產(chǎn)要素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顯著上升。知識與技能的迅速迭代和創(chuàng)新,大大增加了經(jīng)濟社會對人力資本的需求。人力資本正在成為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最重要的生產(chǎn)要素,并成為提高經(jīng)濟活動生產(chǎn)效率的關(guān)鍵因素。
當(dāng)前中國經(jīng)濟進入追求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新階段,必然對經(jīng)濟增長內(nèi)涵與質(zhì)量提出更高要求,新質(zhì)生產(chǎn)力也必將迎來進一步加速的勢頭,從而對提升人力資本等各項生產(chǎn)要素水平提出全新需求,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人力資本積累勢在必行。
新一代勞動者所具備的技能、水平和素質(zhì),又會反過來,以摧枯拉朽的力量不斷改變和重塑經(jīng)濟形態(tài),充當(dāng)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持續(xù)動力。在新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和新的生產(chǎn)要素交互促進的歷史過程中,也勢必要面臨一系列新挑戰(zhàn),同時會產(chǎn)生一系列新需求,值得學(xué)術(shù)層面和政策層面共同關(guān)注,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為此,有必要圍繞新質(zhì)生產(chǎn)力對人力資本的需求進行研究與觀察。首先要結(jié)合事實特征與理論邏輯,厘清和找準(zhǔn)背后“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真問題。
釋放新人口紅利潛能
倘若將數(shù)據(jù)與現(xiàn)實相互參照,從近年來各地近乎白熱化的“搶人大戰(zhàn)”中也不難發(fā)現(xiàn),一方面,具備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高素質(zhì)人才備受青睞,供不應(yīng)求的供求矛盾突出;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特別在人才數(shù)量、分布、層次等方面與產(chǎn)業(yè)升級和經(jīng)濟轉(zhuǎn)型的要求之間適應(yīng)度和匹配度低、供需錯位的情況也較突出(一些城市為此提出了所謂“產(chǎn)才融合”的政策方針試圖緩解這方面的突出矛盾)。
由此可見,當(dāng)前人力資本存量與新質(zhì)生產(chǎn)力和產(chǎn)業(yè)發(fā)展對人力資本尤其是高端人才的迫切需求之間存在著較大缺口。但與此同時,與傳統(tǒng)生產(chǎn)力相比,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相關(guān)行業(yè)的崗位數(shù)目和薪酬溢價都出現(xiàn)一定程度下滑——盡管這很可能并不符合一些人對新興行業(yè)應(yīng)當(dāng)比傳統(tǒng)行業(yè)收入高的感性預(yù)期。受此疊加因素的影響,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與其日益增長的人力資本需求之間的矛盾隨之更為凸顯。
內(nèi)生增長理論將人力資本視為“增長的發(fā)動機”。“發(fā)動機”跟不上勢必影響運行速度,甚至可能引起“熄火”。當(dāng)前,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和職業(yè)教育的迅速發(fā)展,勞動力人口素質(zhì)的持續(xù)提升是不爭的事實,2021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9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提高尤為明顯。但是對比發(fā)達國家,仍有差距。
與此同時,中國人口結(jié)構(gòu)正在發(fā)生巨大變化,受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居民生育意愿、國家相關(guān)政策影響,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程度加深已是不可逆轉(zhuǎn)的趨勢。在此背景下,為了讓“第一次人口紅利”消失與“第二次人口紅利”獲得之間不出現(xiàn)真空期,避免“人口負債”,有賴于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積累創(chuàng)造新的增長源泉,使之成為一個總按鈕,在延長“第一次人口紅利”周期的同時釋放“第二次人口紅利”潛能。
對于第二次人口紅利或“新人口紅利”,有學(xué)者將拓展傳統(tǒng)人口紅利(數(shù)量型人口紅利)與創(chuàng)造新型人口紅利結(jié)合起來,其中,新型人口紅利包括就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型人口紅利和素質(zhì)提高型人口紅利。這些重要論斷可以稱之為“新人口紅利論”(因兩次人口紅利一脈相承,實則是由數(shù)量型轉(zhuǎn)向質(zhì)量型,如果借用以生物進化論為基礎(chǔ)的演化經(jīng)濟學(xué)視角也不妨謂之“人口紅利演化論”)。
從“新人口紅利論”出發(fā),獲得新人口紅利很大程度上將有賴于加速人力資本提升,換言之,新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就是“人力資本紅利”。如果說,新質(zhì)生產(chǎn)力與傳統(tǒng)生產(chǎn)力之間的新舊動能轉(zhuǎn)換,是中國經(jīng)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實現(xiàn)轉(zhuǎn)型升級的關(guān)鍵;那么,傳統(tǒng)人口紅利消退和人力資本紅利的此消彼長,將為以人力資本為核心動力的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提供不竭動力。
掌握競爭發(fā)展主動權(quán)
經(jīng)濟增長模式轉(zhuǎn)變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大幅提高了勞動者技能需求,人力資本密集成為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的突出特征。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離不開人才的支撐。持續(xù)提高人力資本水平,既要夯實教育基礎(chǔ),加強人才培養(yǎng),也要加強軟硬環(huán)境建設(shè),完善理順相關(guān)機制,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人盡其用。
從長遠看,隨著經(jīng)濟水平提高、教育發(fā)展以及相關(guān)政策支持,中國經(jīng)濟的人力資本紅利將進一步釋放,助力新質(zhì)生產(chǎn)力成長。但鑒于當(dāng)前中國的人力資本投入滯后于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將造成經(jīng)濟增長動力不足,通過有效的政策設(shè)計因勢利導(dǎo)地促進人力資本加快積累進程,就成為既立足長遠又迫在眉睫的必然選擇。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舒爾茨、貝克爾等人創(chuàng)立的“人力資本論”翻開了經(jīng)濟思想史中可以稱為“人本經(jīng)濟學(xué)”的新篇章。經(jīng)濟學(xué)回到“人”身上,就好比文藝復(fù)興沖破中世紀(jì)迷霧,自然是劃時代的事情,意義怎么強調(diào)都不為過。而且人力資本存量水平最重要的取決因素在于“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因此相比于其他要素而言,人力資本作用于經(jīng)濟增長的過程相對“慢熱”。
盡管見效慢,但其影響既廣又深遠,尤其對中國這樣從要素驅(qū)動轉(zhuǎn)向創(chuàng)新驅(qū)動過程中的國家而言,即便是促進經(jīng)濟增長因素中最熱門且對勞動生產(chǎn)率貢獻最被看好的技術(shù)進步衡量指標(biāo)——全要素生產(chǎn)率(TFP),諸多研究表明,其背后起決定性作用的“推手”也還要歸功于人力資本。而全要素生產(chǎn)率的大幅提升,正是新質(zhì)生產(chǎn)力蓬勃發(fā)展的核心標(biāo)志。
在百舸爭流的時代大潮中,誰能抓住機遇,誰就能占領(lǐng)先機、贏得優(yōu)勢,真正掌握競爭和發(fā)展的主動權(quán)。歷史性戰(zhàn)略機遇不容錯過,形成并發(fā)展新質(zhì)生產(chǎn)力,實現(xiàn)傳統(tǒng)生產(chǎn)力向新質(zhì)生產(chǎn)力的轉(zhuǎn)化,成為搶占發(fā)展制高點、培育競爭新優(yōu)勢、蓄積發(fā)展新動能的“先手棋”。
(作者系國研新經(jīng)濟研究院創(chuàng)始院長、新經(jīng)濟智庫首席研究員)
編輯:薛華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