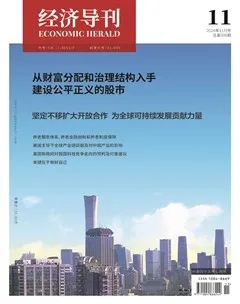關鍵在于做好自己
中美之間的沖突是結構性矛盾
中美之間的沖突,本質上是結構性矛盾導致的,我在此引用一些數據和案例加以說明。中國這30年在經濟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少有的。30年前德國、日本人均GDP是中國的80倍,韓國是30倍,香港將近40倍。馬來西亞當時是中國的10倍,泰國是中國的7倍,菲律賓和緬甸是中國的3倍,印度也比中國略高一點。
今天形勢已經完全逆轉了。德國從當年的80倍變成了4倍,日本、韓國大約都是3倍,其他國家都已被中國超越。印度今天人均GDP只有0.26萬美元,是中國的五分之一。中美對比也發生較大變化,1981年我國GDP是美國的6%,1991年是6.2%, 2001年達到12.7%,2021年達到74%。這種對比實在太強烈了,毫無疑問,這將帶來中美雙方結構性的一些沖突和矛盾。
科技方面同樣如此。我曾長期在科技部工作,也長期研究科技戰略和政策,可以說是這幾十年中國科技變遷的親歷者、見證者。2003年,國家啟動中長期科技規劃論證和編制,當時我們在高科技領域沒有幾個拿得出手的東西,連跟蹤都非常吃力。現在呢,可以說已經發生了格局性改變。比如,我國航天領域的載人航天、空間站、登月都已變成現實。當年衛星定位導航是“卡脖子”工程,今天北斗已經實現了超越,我們不再受制于人。
大飛機是我20年前在科技部期間曾經深入研究的一個領域。我國20世紀80年代啟動了運10,后來無疾而終。我介入大飛機戰略研究的時候,大多數部門都認為做不了,做出來也無法商用。今天我們的C919已經飛上了天空,而且已經批量投入商用。
新能源汽車也是如此。20年前論證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曾有新能源汽車的方案,曾經被否定了。 通過十年來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結合今天打了一個翻身仗,奇瑞、吉利、比亞迪等后來居上,為中國汽車正名,讓中國汽車大批量走出國門。

5G更是如此。當年我們做3G都勉為其難,所以當時中國發布 3G移動通信標準時是世界上唯一使用三個標準的國家,相當于為一個電信服務付出三倍的成本,原因就在于當時我們的通信技術有較大差距,不敢肯定TD到底能不能正常商用,只能選擇妥協。今天,中國5G已經全球領先,這也是華為被美西方圍剿的根本原因。
還有載人深潛器。全球現在擁有能夠到達海底萬米深淵,而且能夠正常開展工作的深潛器的國家,只有中國。這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深潛器,而是一個完整的技術體系,表明我們在控制、材料、通訊、照明、動力和系統集成等諸多方面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在深海這個只有極少數國家才能到達的極地,中國人也來了。
基因測序儀過去百分之百依賴于美國,不僅完全受制于人,而且意味著我們的生物數據隨時可以被別人拿走。今天我們已經實現了超越,華大智造自主研制的測序儀,在性能、成本和安全性方面都已領先于世界。前年華大智造與世界最領先的美國illumina公司在美國打了一場知識產權官司,法院判定對方是惡意侵權,賠償3.34億美元,這是到目前為止,中美知識產權糾紛中最大的對華賠償額,也表明我們已經開始從技術學習者走到了技術引領者。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特高壓輸變電、煤制油、煤制氫、盾構機、核磁、三代核電、核聚變、高溫氣冷堆、核磁共振、量子通信、基因工程等等。中國科技井噴式的突破,完全打破了西方長期以來居高臨下的“躺贏”。這些變化基本上都是在這20年內發生的,毫無疑問,給中美關系乃至中國與整個西方之間的關系帶來了新的變數。
中國與美西方關系的新變數
國際關系的背后是利益,今天中美、中西關系的逆轉也是如此。20世紀80年代,美國強迫日本簽訂了廣場協議,通過市場準入、關稅和匯率等政策壓制日本,給日本造成了30年的發展停滯。1995年,日本GDP是德國的兩倍,是中國的8倍,是英國的4倍,是韓國的10倍,占到了美國GDP的73%。日本在半導體領域完全超越美國,這是令人震驚的奇跡!30年后一切都發生了反轉,現在中國GDP是日本的4.5倍,美國是日本的6倍,德國已經超越日本了。20世紀90年代曾經在中國稱雄的日本家電企業索尼、松下、東芝、夏普、三洋,都已成為明日黃花。美國強加的一個廣場協議加上一個半導體協議,基本上把日本打趴下了。
高科技領域之爭并不是意識形態問題,本質上是利益之爭。美國對發達國家日本尚且如此,更何況中國呢?新加坡前駐美大使陳慶珠說,美國對高科技產業的態度,就是“是我們的”,特別強調這是他們的領地,是不可以自動讓渡的。20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與北京大學周其仁教授有一個對話,那時中國還只能做服裝鞋帽和加工貿易,就是所謂“7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而當時一件襯衫賺一塊錢,這樣的交易模式各得其所,相安無事。周教授問:假設有一天當中國也決定制造大飛機的時候,美國人會怎么看?一生高揚自由主義旗幟的薩繆爾森當即不假思索地說,那將是美國永遠的痛。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是《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最近他有一段話:“如果中國一直專注于制造和銷售低端產品,到底實行什么樣的主義,社會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甚至素食主義也好,我們根本不感興趣,也不會去關心。我們只關心能否購買中國的低端產品而已”。這是他的原話,他的全球化其實只是希望中國作為西方的“奶牛”而已。

讓他們感到失望和震驚的是,中國這些年的發展變化太多太大了。2002年《人民日報》有一則關于十六大報告的報道,提出到2050年中國經濟有望達到世界第二的愿景。而僅僅10年后,中國超越了日本,現在已經是日本的4.5倍。從1990年到2023年,中國GDP增長38倍,印度增長5倍多,其他國家增速都低于4倍,意大利、日本是負增長。全球熱議的百年未有之變局,主要就是指中國崛起。
美國對中國科技的打壓不斷加劇
因此,美國對中國科技的打壓毫不奇怪,而且只會不斷加劇。以華大基因為例,從2018年開始遭受“301調查”,進入美國制裁名單,其4家下屬機構被美國列入負面清單,可以說打壓力度一輪超過一輪。他們運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禁止向中國傳輸人類數據,目標直指華大。他們的《生物安全法案》直接點名的四家公司中,有三家是華大的(華大基因、華大智造和華大CG)。美國有一家CSET的國家智庫,最近專門出臺了一個報告《中國,生物技術和華大基因——中國混合經濟如何扭曲競爭》,長達111頁的報告對華大做了全面、細致的分析,其中特別強調“華大基因已經成長為一個國際競爭對手,在生物技術領域承擔著與華為在電信領域相同的角色”,這是他們打壓華大的全部理由。
目前美國對華大基因的打壓是用舉國之力,我將此概括為“四全”:第一是全政府,包括商務部,國防部、國務院;第二是全社會,不僅僅是企業競爭對手,連NGO、大學和科學共同體也都跟進;第三是全方位,不僅僅是貿易,已經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學術交流、人員往來都受到限制;第四是全西方,不僅僅限于美國,許多西方盟友也行動起來了。過去長期與華大密切合作的一些歐洲國家,比如德國、丹麥、瑞典、英國等,也都紛紛與華大科技脫鉤。甚至中東一些長期合作伙伴也明確表示,美國正在向他們施壓,要求切斷與華大的合作。
2023年德國政府制定了一個專門針對華大的內部政策,即華大的設備再好不許買;華大的服務再好不許用;用華大的設備測出來的數據廢掉,換上美國的設備重做;跟華大合作完成的論文不許發表;華大主導的技術聯盟不許參加。由此可見,美國不僅硬實力很強,軟實力也非常強大,可以調動全球的力量來對付中國的一家企業。
中美之爭的關鍵是科技戰
面對日益復雜和嚴峻的地緣政治環境,我們如何應對?我認為關鍵是做好自己。中美之爭的關鍵是科技戰,上甘嶺戰役就是科技戰。很多人談到金融戰、貿易戰,但是最較勁的奪命之戰是科技戰,決定雙方最終命運的也一定是科技戰。在美國的打壓下,中國能不能向死而生,也一定是在科技戰上。科技戰不是遭遇戰,而是持久戰,我們并非束手待斃,而是面臨許多歷史性機遇。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研發投入全球第二,如果按平價購買力計算是全球第一。全時研發人員為全球第一,PCT專利為全球第一。全球投入研發最多的50家企業中,中國占了12家。我們不能自以為是,也決不應當妄自菲薄,而是要全力做好戰略布局。

第一,科技發展正面臨著深刻的變革。今天很多人談到了人工智能,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同樣的,生命科學領域也在醞釀著重大變革,由此帶來的影響絲毫不比AI更小。尤其是AI和BT的結合,也許能夠超過我們今天所有人的想象。變革就是機遇,變革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有所作為。我們必須集中力量,把科技戰作為核心之戰,全力做好科技發展的戰略布局。
第二,引導資本、人才等資源加速流入民企。中國科技創新的希望在民營企業。目前民企新技術發明占到70%,企業研發投入的絕大部分也來自民企。華為每年投入研發1600億元,華大基因年投入也高達27億元。這種長期穩定地專注于一個方向和巨量投入強度,而且是高度開放和市場導向的研發模式,決定了企業已經走到科研前臺,形成了經院式科研無法達到的技術創新能力。如何讓民企在中美科技戰中擔當起應有的角色,甚至是主力角色,需要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抓緊研究部署。
第三,新型舉國體制的最大變量是市場化。我們經常談到我國的體制優勢,談到我們發展歷程中舉國體制起到的作用,其實美國也存在舉國體制,而且其效率并不在我們之下。僅僅一個阿波羅登月計劃就有11萬人、3000多家機構參與,長達14年,這難道不是舉國體制嗎?今天馬斯克能夠一飛沖天,其背后依托的不僅是單純的市場力量,而是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的高度融合。SpaceX的核心技術平臺基本上都在NASA,第一筆研發經費是NASA給的,第一個60多億美元訂單也來自NASA,這是NASA有史以來最大的單筆訂單。當馬斯克處于巨額虧損的時候,美國的創業資本仍然蜂擁而至,不斷推高其市值。正是這種全社會匯聚起來的技術、資本、人才和市場力量,成就了一個傳奇的馬斯克。新型舉國體制不應該是不惜代價、不講成本,新型舉國體制應與市場力量融合,其最大的變量就在于市場化。市場化程度越高,舉國體制就越有生命力。
第四,調整創新體系建設中的政府角色。我在政府部門工作多年,對政府在科技發展中的角色定位深有體會。過去我們在傳統體制下確實做了太多不該做,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營造創新生態方面又往往使的是反勁,以致再多的投入可能都是事倍功半。比如評價機制,論文導向、數量導向是誰引導的?學術行政化、學閥化日益突出,背后力量是誰?科研力量分散重復、惡性競爭,與政府科技資源配置有沒有關系?面對日益嚴峻的科技戰,我們迫切需要深化體制改革,科學確立政府在市場體制中的作用和定位,在創新體系建設中吸引和推動市場力量參與,促進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的高度融合。

第五,對重點領軍型科技型企業提供特別救濟。現在有1300多家企業被美國列入負面清單,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的高科技領軍企業。在美國的國家治理模式下,只要列入負面清單,幾乎所有的機構都將選擇后退和脫鉤,這是真正的舉國之力。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對相關企業的有效救濟機制,許多被打壓的企業處于孤家寡人之境。當企業正在沖鋒陷陣的時候,如何得到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支持配合,這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編輯 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