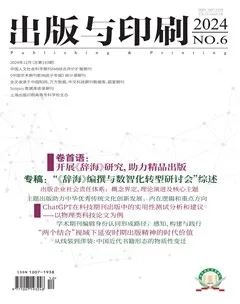“兩個結合”視域下延安時期出版精神的時代價值
關鍵詞:“兩個結合”;延安時期;出版業;出版精神;時代價值
一、引言
延安時期,指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經過長征到達陜北至1948年中共中央撤離陜北的13年時間。其間,面對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和日本侵略者的猛烈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一批優秀的出版人和出版機構,克服造紙、印刷、發行等方面的困難,戰勝一系列客觀不利條件,篳路藍縷、開拓創新,以富有延安色彩的出版精神,開創了在經濟文化欠發達地區高質量發展出版業的成功范例。回望這一時期的出版業,正因為其形成了一系列優良出版傳統,契合了“兩個結合”,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得以承前啟后,為新中國出版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筆者將這些優良出版傳統稱為延安時期的出版精神,以彰顯其與“延安精神”一脈相承的聯系,通過梳理這一時期出版精神的內涵和體現,探究其對推動當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時代價值。
二、延安時期的出版業概況
作為中國革命的政治文化中心,延安在黨中央的寬松文化政策下吸引了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奔赴,為出版業的發展凝聚了寶貴的人才資源。黨中央把出版宣傳工作視為文化戰線的生命線予以高度重視,先是恢復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緊接著新建了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加強出版管理工作。在此背景下,出版業總體上呈現繁榮發展局面。這一時期主要的出版業務及概況如下。
1.圖書出版業概況
這一時期的出版機構大體分為三類:一是專門的圖書出版發行機構,如解放社、新華書店、華北書店等;二是既發行報刊又出版圖書的綜合性出版機構,如解放日報社、八路軍軍政雜志社等;三是兼營圖書編輯出版的機關、團體、學校等,如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1]98
據統計,從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延安地區出版的圖書總計855種,涵蓋多個學科門類。其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類圖書占比最高,曾高達43.56%,[1]100-101指引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文學藝術類讀物方面,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等被英國、美國、蘇聯、法國等翻譯出版,產生了良好的國際影響,魯迅藝術學院編寫的《世界文學名著選》等滋養了大批革命文藝青年;教育出版方面,以辛安亭為代表的教材編審專家,先后編寫了第一套小學、中學教材,以及《邊區民眾課本》《中國歷史講話》《日用雜字》《識字課本》《農村應用文》《干部識字課本》《干部文化課本》等通俗課本讀物40余種,受到熱烈歡迎,促進了根據地教育事業的發展;自然科學讀物方面,新華書店和大眾讀物出版社出版了《怎樣放羊》《怎樣種棉花》《消滅害蟲》以及《婦嬰衛生》《農村衛生》《解剖學》等圖書,指導了邊區農業科學的發展和衛生常識的普及。這一時期的圖書出版,講究通俗化、實用性,促進了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傳播,為促進邊區文藝、教育、農業、醫療、衛生等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2.報刊出版業概況
報紙方面,建成了以《解放日報》為中心的黨報系統。1937年1月29日,《紅色中華》改名《新中華報》,延續《紅色中華》的順序編號,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陜甘寧邊區黨委機關報。1941年春,中央政治局將《新中華報》與新華社編發的《今日新聞》合并,出版大型日報《解放日報》,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黨中央要求各根據地出版發行自己的機關報,以進行廣泛的輿論動員,《邊區群眾報》等陜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于1940年左右先后創辦。至此,延安地區建立起從中央到區縣的縱橫交織的五級黨報體系,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黨報系統。
期刊方面,黨刊是先鋒,之后相繼出現了一系列大眾期刊。黨刊中,創辦最早的是1937年4月創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影響力較大的是1939年10月創刊的《共產黨人》,其發行范圍不僅在延安、陜甘寧邊區,還輻射到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以及國統區的黨組織。大眾期刊中,以文藝類刊物居多,同時還有《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等面向不同讀者群體的期刊,活躍了閱讀氣氛,極大地豐富了讀者的精神生活。這些期刊雖然大多因為經濟困難而于1941年停刊,但普遍積累了良好的讀者基礎,并于新中國成立后相繼復刊。
3.印刷業概況
由于缺乏鉛印條件,延安地區的印刷事業是從油印、石印起步的,直到1937年中央印刷廠在延安清涼山誕生后,才有了鉛印技術工人和鉛印設備。此后,八路軍印刷廠、青年印刷廠等相繼建立。對于印刷工作的重要性,毛澤東主席曾多次強調:“印刷廠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廠生產精神食糧,辦好一個印刷廠,抵得上一個師”[2]。受此鼓舞,印刷人自力更生,開展技術革新,克服紙張、油墨等物資困難和排字、切書等技術問題,保障了黨中央一系列重點出版物的出版。這期間,涌現出祝志澄、萬啟盈等黨的印刷業領導干部,以及曹國興等印刷技術人才和佟玉新等勞動模范。其中,曹國興是中央印刷廠的刻字工人,憑借卓越的創造才能和高度的勞動熱忱鉆研技術的提高和工具的改良,如制造了切木刻坯的機器來代替手切勞動,使生產效能提高了近四倍,成為印刷業的技術創新模范;佟玉新是中央印刷廠總務處管理員,負責水房燒水工作,通過改造灶門尺寸、調整爐條高度和間隔距離、改進燃料等實現了節能增效,被推選為全邊區的“機關節約模范”。中央印刷廠積極樹立和宣傳這些職工榜樣,開展勞動生產競賽,大大推動了印刷數量和質量的提升。
4.發行業概況
這一時期,黨中央領導的發行業的最大成就是新華書店的成立及發行網絡的拓展。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創刊,封面署名“陜西延安新華書局”,自第21期(1937年10月30日)起正式標明“陜西延安新華書店”,中央黨報委員會編譯的書刊也一律用“陜西延安新華書店”名義總經銷或發行。1940年1月,“陜西延安新華書店”改名“新華書店總店”,主要任務是發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和馬列叢書、抗戰叢書。新華書店總店成立后,積極響應黨中央《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等政策,在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建立分店,并通過門店零售、郵局郵購、書報下鄉、流動售書等方式靈活推進發行工作,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思想、傳播先進思想文化的主要陣地,影響力逐漸輻射全國。
三、延安時期的出版精神
延安時期黨領導的出版業與國家、民族呼吸相連、命運與共。出版人作為出版業的能動主體,其思想站位決定著出版物的選題方向,其業務技能影響著出版物的質量,其道德品格影響著作者隊伍的建設和讀者群體的發展,可把出版人的優良傳統概括為職業精神。出版機構作為出版組織,是出版人奮戰的空間場域,不僅彰顯著出版人精神,更在業務開展中體現出社會擔當,可把出版機構的優良傳統概括為事業精神。梳理和提煉這兩類精神,不難發現它們共同的精神之源是“兩個結合”。
1.出版人的職業精神
(1)出版為“械”、鞠躬盡瘁的獻身精神
這一時期的革命出版人,從事出版不是為了賺取商業利益,而是把出版活動同現實斗爭結合在一起,把出版物視為教育讀者、鼓舞讀者、武裝讀者頭腦的有力武器,表現出獻身出版業的巨大熱情。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和新華書店成立后,調任的出版發行人員有的是黨的地下工作者,有的是紅軍老戰士,有的來自陜北公學,有的來自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他們為打破敵對勢力對革命出版物的查禁與封鎖而積極斗爭、不畏犧牲,為新華書店發行網的建立作出巨大貢獻。《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輯楊松,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秉持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和奮斗精神,在疾病纏身的情況下于一個月內寫出29篇社論,堅持逐字逐句對每天的報紙內容把關,終因過度勞累而病逝。俄國著名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說:“一個沒有受到獻身的熱情所鼓舞的人,永遠不會做出什么偉大的事情來。”延安出版業取得的成就,離不開革命出版人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的支撐。
(2)團結作者、服務讀者的奉獻精神
這一時期的出版人,團結作者、心懷讀者,以“甘為他人作嫁衣”的奉獻精神,極大地促進了優秀革命思想文化讀物的出版。1937年年初,在《魯迅全集》的出版過程中,胡愈之列出編輯分類大綱,籌劃成立了以蔡元培、茅盾、宋慶齡等人為主的編輯委員會,并組織了包含鄭振鐸、王任叔、唐弢等作者在內的26人共同編校整理,還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巧妙地使書稿通過審查,以卓越的組織協調能力,使《魯迅全集》得以高質高效問世。對此,魯迅先生的遺孀許廣平贊嘆道:“六百萬余言之全集,竟得于三個月中短期完成,實開中國出版界之奇跡。”[3]為了使不同購買力的讀者都能買得起這部著作,胡愈之將其分成20卷出版,并推出甲、乙、丙三種不同裝幀形式的版本,進行差異化定價,同時實行預約折扣制,以滿足讀者的不同需求。在延安時期復雜的政治局勢、艱苦的出版條件下,這種高超的文化中介能力反映的是對普遍聯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原理和方法論的靈活運用,值得今天的出版人認真學習。
(3)精益求精、敬業無私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包括精益求精、專注、敬業等方面的內容。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席曾直接參與《解放日報》等報刊的編輯工作,“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對擬發表的文章進行增添、刪改,使其中的思想得以升華”,“加一字、刪一字、改一字均用心斟酌”,“連發表的時機與具體的字號都一一說明”[4]。在審定《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兩條路線》等書稿時,他做了大量的編輯校對工作,逐一核對引文的原文,并親自校對《論持久戰》等自己作品的清樣。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深深影響了當時的革命出版人。延安時期的刊物編輯在審讀來稿時,不看作者姓名,只看作品質量,以敬業無私的精神嚴把質量關,這也是這一時期出版業繁榮發展的一大原因。延安時期曾擔任《中國青年》編輯,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青年》雜志社總編輯、作家出版社總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和社長的著名作家兼出版人韋君宜,就以公平公正著稱,認為“當編輯要不怕得罪無名作者,還要不怕得罪作家,沒這點骨氣當不了編輯”[5]。這種工匠精神,體現的是求真務實的馬克思主義作風。
(4)攻堅克難、開拓創新的奮斗精神
惡劣的政治環境使延安時期的出版業物資極度匱乏,但革命出版人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戰勝客觀不利因素,使延安出版業一次次迎來希望的曙光。西北抗敵書店的開業,就是常紫鐘和同志們在一沒資金、二沒房子、三沒柜臺的情況下,在窯洞中用舊貨架和破木板搭建書臺促成的。鉛字版《解放日報》等黨報的問世,是中央印刷廠萬啟盈等人,將從上海購得的印刷機拆分重組后裝在三口棺材里躲避層層搜捕實現的。1939年,國民黨開始對延安經濟封鎖,邊區紙張極為短缺,青年科學家華壽俊嘔心瀝血反復試驗,用陜北的馬蘭草創制成質量優良的馬蘭紙,解決了眾多出版物的印刷用紙問題,使陜北告別了缺紙、只有劣質紙的歷史。印刷專家蔡善卿,用延長油礦的油渣燒制油煙,請著名工程師沈鴻制造了軋油墨機,解決了印刷油墨的問題。出版人這種攻堅克難、開拓創新的奮斗精神,體現了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探索規律、追求真理并反復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出版觀,至今彌足珍貴。
2.出版機構的事業精神
(1)緊跟時局、與時俱進的先進精神
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是共產黨人的鮮明特征。延安時期的解放社、新華書店、大眾讀物社等出版機構,自成立起就緊密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大量發行馬列主義叢書、黨的領導人著作以及《抗日戰爭叢書》《抗日戰爭參考叢書》等時事政治類圖書和黨報黨刊,并且向敵后抗日根據地拓展發行網點,影響力很快擴及全國十幾個省市,把革命的種子撒遍祖國大地,體現出鮮明的戰斗性和緊跟時局的先進性。
為了服務邊區群眾的生產生活、滿足群眾的精神需求,這些出版機構還策劃、出版了大批文藝類著作和圖文并茂的通俗類讀物,其中包含不少傳播優秀傳統文化的讀物,如秧歌劇類圖書有二三十種。隨著整風運動的開展,這些出版機構又與時俱進,結合實際需求調整圖書品類,出版了大量有關整風運動的出版物,成為全國思想運動和革命出版事業的風向標。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出版機構的先進性體現在其積極服務黨的中心工作、自覺引領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2)聯系群眾、普及文化的服務精神
圖書出版發行方面,為了聯系和動員人民群眾支持抗戰、促進文化的普及和傳播,延安新華書店除了出版發行政治理論類著作,還出版發行了《識字課本》《衛生常識》等一大批圖文并茂的通俗讀物,并專門組織工作人員下鄉教授知識,掀起識字運動,降低文盲率。為打通流通環節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讓更多優秀文化讀物到達群眾手里,新華書店積極創新,探索了多種發行方式:或直接派人送書上門;或通過邊區通信站寄發;或通過外縣轉運;或提供樣書供翻印;或通過郵局寄發;或通過軍車運送;或開辦郵購;或組織下鄉團體、小販代銷。[6]
報紙出版發行方面,為幫助群眾看得明白、聽得清楚,陜甘寧根據地黨報《邊區群眾報》從創辦起就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除了刊登群眾需要的服務信息,還盡量使用方言詞匯,改編陜北秧歌、說書、信天游等用在稿件中,使語言通俗易懂、形式活潑,取得了“粗識字的人能看懂,不識字的人能聽懂”的效果。更為可貴的是,該報推出了獨特的“審稿”機制:召集全社成員開會集體審稿,邀請文化程度比較低的炊事員和勤務員來讀稿、聽稿,邊審邊改,直到大家滿意、一致通過。主動聯系群眾的精神,使該報獲得了群眾的信任并被親切地稱為“咱們的報紙”。此外,該報還通過發展通訊員、建立讀報組等方式普及文化,主動服務群眾,幫助群眾提升文化水平,起到了文化啟蒙的作用。
(3)團結內外、放眼國際的開放精神
為廣泛團結知識分子和邊區群眾,擴大宣傳力量,延安出版機構非常重視對文藝類圖書的出版。如秧歌劇類圖書,富含地域特色,具有深厚的群眾基礎,約占戲劇類圖書出版品種的六成。同時,出版機構也放眼國際,引導讀者了解世界局勢。例如,延安時期出版了約27種外國文藝類譯著,其中蘇聯作家作品約23種,[7]讓讀者能更深刻地了解國際環境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胡愈之策劃出版了斯諾(EdgarSnow)的《西行漫記》,該書第一次通過外國記者的視角講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及紅軍的真實面貌,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此外,《解放日報》還開辟有國際新聞版,經常刊出《蘇德戰爭形勢圖》等地圖的預售廣告,引導讀者關注國際形勢,體現了放眼國際的傳播視野和開放精神。
(4)重視學習、鼓勵創新的改革精神
“如果再過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8],這是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時期經常說的一句話。整風運動中,毛澤東主席以《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號召全黨,使得“比業務、樹榜樣”成為延安各行各業的新風。以中央印刷廠為例,其積極建立培訓機制、開展全員學習,并樹立典型榜樣、鼓勵業務創新。具體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招收16~20歲的學徒工人,讓他們進行兩年的學徒培訓后正式上崗,培養出版后備軍;②重視繼續教育,建立日常學習制度,不定期開設培訓班,提升職工的思想覺悟、文化水平和業務技能;③編印內部的《印刷周報》為員工講解印刷技術,與八路軍印刷廠內部的《印刷月報》交換,開展業務交流;④樹立曹國興、佟玉新等勞模榜樣,開展業務競賽,激發創新活力。管理制度上的創新為中央印刷廠培養了大批業務骨干,奠定了新中國出版印刷業的人才基礎。據統計,從1939年1月到1941年4月,中央印刷廠調往晉東南、華中、晉綏、綏德警備區、晉察熱、大青山、山東、晉察冀,以及八路軍印刷廠等革命根據地和邊區內印刷廠的人員共9批31人,促進了各地出版印刷業的發展。[9]
四、延安時期出版精神的時代價值
傳播技術的迭代更新深刻改變了出版業的環境,使出版物的內容、載體和受眾的閱讀習慣等都發生了變化。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當下的出版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答好堅守與變革的時代問卷?唯有從主體和客體、國內和國際的雙向維度出發,才能明晰延安時期出版精神的時代價值,找尋到推動我國出版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密碼。
1.提升黨性修養,傳承出版家精神
延安時期涌現了大批出版人才,比如艾思奇、何思敬等馬列著作翻譯出版人才,丁玲、韋君宜等文學出版人才,辛安亭、董純才等教育讀物出版人才,萬啟盈、華壽俊等印刷技術人才……他們以高度的政治覺悟、深厚的人民情懷和崇高的職業道德、廣博的知識素養、扎實的業務技能成為這一時期的優秀出版家。其中,艾思奇既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又是作家、翻譯家,同時也是《哲學與生活》等暢銷著作的作者和《中國文化》的主編、《解放日報》的總編輯。他被毛澤東主席譽為“在理論戰線上的忠誠戰士”,彰顯出卓越的出版家精神。
出版家精神,歸根結底,是一種黨性修養。黨性修養是通過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鍛煉、自我改造而達到共產黨員黨性的某種程度,包括政治理論修養、組織紀律修養、思想作風修養、文化知識修養等。對于今天的出版人而言,就是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錘煉過硬本領,從選題策劃環節開始提升出版物的品質,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承擔起傳播先進文化的使命。
2.堅持人民至上,樹立用戶思維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延安時期的出版人在服務知識分子的同時,也想方設法推出農業生產、醫藥衛生等方面的書籍,并克服一切困難把書送到群眾手里,體現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今天,推動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同樣也需要堅持人民至上。
一是緊隨數字化時代,樹立用戶思維。媒體融合時代,閱讀的內容、渠道、載體等都出現了線上與線下融合的特征,讀者也轉變成“用戶”。因而,傳統出版機構應向知識服務提供商轉型,探索融合出版,滿足數字化時代用戶的知識消費需求。二是創新公共文化服務方式,讓全民共享文化權益。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曾說:“出版業要服務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的要求。文化建設第一個要求,就是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10]從農家書屋、職工書屋、社區書屋、軍營書屋,到流動圖書館、新型公共文化空間,都是出版業發揚為人民服務精神、滿足人民多樣化需求的體現。
3.統籌國內國際,講好中國發展故事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與世界其他國家人民的精神溝通與交流,而出版物自古以來就是溝通各國文化和讀者心靈的橋梁。延安時期黨的革命主張能夠傳至全國、達至海外,同樣有賴于出版物的流通。因此,促進出版業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尤其要加強“走出去”,這既是傳播中國聲音、改變“西強我弱”國際輿論格局的需要,也是講好中國發展故事、服務文化強國等國家戰略的需要。
例如,近年來我國新聞出版業陸續實施的“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絲路書香出版工程”“中國當代作品翻譯工程”等項目,對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又如,“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系列圖書等中國主題圖書在海外的暢銷,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形象,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4.深耕出版品牌,強化改革創新
延安時期誕生的新華書店等出版發行機構,成為新中國出版業的“國字號”品牌,承載了幾代中國人的閱讀記憶,其發展史“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宣傳黨的先進理論和正確主張的傳播史,又是一部鮮活生動的現當代中國文化社會發展的歷史”[11]。除了黨的領導這一管理體制的因素外,其卓越的出版品質和為人民服務的出版文化才是品牌長青的根基。出版品牌,外觀上體現為出版標識,內在上體現為一種口碑與榮譽,反映著出版物或者出版機構在讀者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代表著其優秀的出版品質與廣泛的出版號召力,也是今天出版機構實現高質量發展所要追求的目標。因此,面對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出版機構不能再像過去一樣粗放式發展,必須與時俱進,以品牌求發展。
深耕出版品牌,需要像延安時期的出版人一樣強化改革創新、持續進行業務探索。延安時期的出版業也正是在改革創新中實現了從無到有、從零到一的突破。隨著信息技術的迭代變化,媒體融合深入發展,傳統出版業的生態格局被打破,轉型發展成為新時期出版人和出版機構面臨的時代命題。只有像中央印刷廠等延安出版機構一樣加強體制機制改革,鼓勵技術創新,釋放人才活力,才能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攻堅克難、屢創奇跡,實現高質量發展。
五、結語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時期出版業在我國現代出版史上書寫了光輝的一頁。出版人的職業精神和出版機構的事業精神,是這一時期出版業取得光輝成就的精神密碼。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個結合”的視域探究延安時期出版精神的內涵,既有助于了解延安時期出版業的歷史貢獻、動力源泉,又可為當下出版業破解改革難題、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是出版業積極踐行“兩個結合”的必由之路,也是出版業傳承和弘揚延安精神的應然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