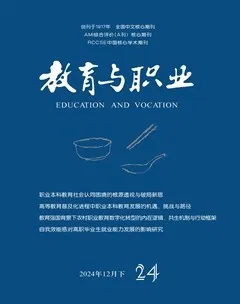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在邏輯、共生機制與行動框架
[摘要]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以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為價值愿景,以共享包容理念為目標追尋,以教育空間生產為可能形態,以滋養數智文明為實踐準則。從共生理論的視角看,其共生機制涵蓋多元主體參與的共生單元、連續互惠的共生模式、要素流通的共生場域與開放協同的共生界面。相應地,可以從以下四個維度入手,即釋放共生單元內生力、激發主體互惠協作意識,發揮共生模式調配力、提升新型農民數字素養,增強共生場域拓展力、打造數字化教育新基建,疏通共生界面傳導力、完善優質資源保障體系,為當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行動框架與可行路徑。
[關鍵詞]教育強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理論邏輯;行動框架
[作者簡介]趙書琪(1992- ),女,山東濟南人,山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講師,碩士生導師。(山東 "濟南 "250014)
[基金項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項目“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國職業教育與鄉村振興協調的時空演化與長效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3YJC880154)和2023年度山東省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項目“共同富裕背景下山東省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成效測度與長效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23QY030,項目主持人:趙書琪)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725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985(2024)24-0022-09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推進教育數字化,賦能學習型社會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全國教育大會上對新時代新征程加快建設教育強國作出系統部署,強調“深入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農為邦本,本固邦寧。農村職業教育作為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聯系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其數字化轉型能夠創生與鄉村全面振興相適應的新型教育文化,厚植數字意識,培育農民數字素養,促進鄉土文化資本再生產,為數字鄉村建設提供智力與技術保障。
近年來,數智時代農村職業教育的轉型發展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已有研究認為,數字鄉村戰略背景下的農村職業教育以實現城鄉共同富裕為愿景[1],以“技術進場—組織導入—社會驅動”為視角[2]、培育新型農民為切入點[3],構筑起農村職業教育助力數字鄉村建設空間[4],教育精準扶貧讓鄉村教育的辦學條件及環境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實現鄉村教育的高質量發展,信息化教學成為重要手段[5]。農村教育數字化轉型通過重塑鄉村性、重建教育性及重現文化性,凸顯了其在鄉村教育現代化中的社會、生命及文化價值[6]。在因應之策上,以公平負責、融合共生、自主包容、倫理規約[7]作為價值導向,開發兼具“普適性與差異性”的優質數字教育資源[8];推動農村教育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共享[9],改變農戶家庭的傳統觀念,助推智能化教育理念廣受接納[10];提升價值鏈,深化技術創新[11],構建智能化教學、管理、服務平臺[12],通過數字化教育云平臺聯結城鄉學校,形成“協同化”發展新格局[13]。
當下,“技術下鄉”正深刻影響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形態,數字技術賦能業已成為農村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并非“數字技術+農村職業教育”的機械疊加,在理論層面仍需深入探討如下議題: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緣何可能?數字技術重構農村職業教育的動力何在?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何以實現?職業是人的一種“自在”生存方式,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是一次以人為中心的教育系統創變。對此,本文以“人—技”共生理論為視角,試圖闡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在邏輯,探討其動力機制,描繪其行動框架,以期提供些許鏡鑒。
二、轉型之基: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在邏輯
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邏輯起點是探索科學技術理性與教育價值理性統一的共生域,秉持“人是目的,人是主體”的認知觀,促進農村職業教育主體生命與客觀數字技術的統整性交互。從“人—技”關系視角思考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問題,從應然性、必然性、實然性維度深挖轉型的內在邏輯,以轉變技術主義主導的教育觀,促進農村職業教育與數字技術應用的深度融合。
(一)邁向共同富裕愿景:數字化轉型的應然旨歸
對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行理據分析,探討其發生發展的應然旨歸,是詮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何以轉型”的前提性問題。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首要任務是打造“人—技術—自然”和諧共生的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高地。其應然旨歸體現在: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促進農民物質生活邁向共同富裕。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通過助力“三農”(扎根農村、緊貼農業、服務農民),為實現城鄉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質基礎。農村職業教育以培養農民職業技能與管理能力為目的,開展知識傳授與技能培訓,支撐其投入現代農業發展,并實現個體自由、全面發展。職業教育數字化可為農村場域積累豐富的人力資本,傳遞經過實踐檢驗并歷經數代累積的涵蓋農作物生產規律、生態農業基本原則、農業價值觀等的農業生產寶貴經驗,促進鄉土性人力資本再生產。此教育進程將衍生一系列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在直接影響農村勞動力市場結構變化的同時,助推農村職業教育精準扶貧,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另一方面,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助力農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本質要求。鄉土性是農村教育發展之根基,重塑農村職業教育鄉土特色是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文化價值的集中體現。綜上所述,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在提升農民數字技能的同時,也極大地助力精神共富,為實現共同富裕夯實了財富基座。
(二)促進教育共享包容:數字化轉型的普惠價值
對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行意蘊澄明,深究其發生發展的普惠價值,是闡述“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何以轉型”的基礎性問題。在互惠、共享、和美的農村組織化發展進程中,讓個體都平等地享受制度紅利,符合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內涵要求。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以技術工具支撐涉農主體平等融入職業教育建設,不斷彰顯其普惠價值。截至2023年6月,我國農村在線教育用戶規模達6787萬人,普及率為22.5%;農村在線醫療用戶規模達6875萬人,普及率為22.8%[14]。作為職業教育共同體聯結的紐帶,數字技術以智能疊加的方式打破時空限制,將離散“不在場”的農村教育資源吸納至數字網絡共同體。
其一,數字化轉型推動職業教育普惠“共享”。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加速實現數據共享和教育協同,助推信息與數據傳輸由單向、扁平的垂直機制拓展為多向、交互的平行機制。通過建設專遞課堂、名師課堂和名校網絡課堂,打通教育信息壁壘,共享優質教育資源,有助于解決相對短缺的教育資源與農民日益增長的知識技能需求之間的供需矛盾。其二,數字化轉型加快區域職業教育“共建”。數字技術利用大數據實時性、多維度、分布廣的屬性,賦能農村地區教育資源精細化配置,發揮城鄉的資源統籌功能,激發教育主體協作意愿,提升農民運用數字技術的自我效能感,使城鄉職業教育在交相映照、互為支撐、彼此滋養中邁向高質量發展。其三,數字化轉型賦能城鄉職業教育“共治”。數字化轉型為農村職業教育更好地聯通政府、企業、學校創生了新渠道,職業院校、涉農企業投入其治理與發展,持續激發社會各界參與職業教育的意愿,使農村職業教育真正成為全社會的“公共利益”。
(三)助力教育空間生產:數字化轉型的溢出效應
對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行樣態描畫,明晰其發生發展的溢出效應,是理解“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何以轉型”的現實性問題。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塑造了新的農村職業教育結構與形態,并呈現出獨具特色的空間特性。法國城市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認為,空間“既是具體的又是抽象的……這種具體的抽象性既是社會活動的中介(抽象),因為它構成它們,也是這些活動的一個成果(具體)”[15]。愛德華·蘇賈(Edward Soja)繼承發揚了列斐伏爾的觀點,認為“空間性是社會產物,并且同社會一樣,空間性既以實體形式(具體的空間性)存在,也作為個人與全體的一組關系存在”[16]。扼要地說,空間生產理論強調基于社會空間邏輯分析教育發展,為本文從更廣闊和更具生產性的空間向度理解和推進農村職業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結合空間生產力理論,本文認為農村職業教育場域具有豐富的“空間元素”。詳述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的空間分為物理空間、知識空間、人際空間和體驗空間四維。物理空間是學校教育空間最基礎的構成元素。技術賦能下的學校邊界已悄然發生改變,教學過程對接行業產業需求決定了課堂與企業車間、工位及實訓基地等空間相互融合。知識空間是由知識與技能內容、物質載體建構形塑的空間。農村職業院校以培育新型農民為目標,著力打造以涉農學科為主體的專業與課程群,通過教育元宇宙、智能陪伴機器人、分布式學習系統等支撐學生開展深度學習,最大程度地助力學生智慧生成。人際空間作為學校教育空間的動態生成系統,彰顯學校教育空間的社會性、動態性與生成性。通過升級農村地區教育專網,推動數字映像、動態呈現、全域感知、全程交互、移動計算等技術在農村職業教育教學場域的實現,鞏固了學徒關系,延展了農村職業教育的人際空間。體驗空間是學習主體在教學空間中具身感受到的空間。數字技術將優質教育資源推送至偏遠鄉村地區,讓學習者隨時隨地獲得具身學習體驗。
(四)滋養鄉村數智文明:數字化轉型的實踐原則
對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行路徑演繹,厘定其發生發展的實踐原則,是回應“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何以轉型”的關鍵性問題。農村不僅是集聚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也是特殊的文化單元。技術哲學家唐·伊德(Don Ihde)認為,技術是被歷史和文化所嵌入的[17]。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人類進入新的社會階段并催生出新的人類文明形態——數智文明[18]。 智能終端交互新范式旨在將算法流程及應用倫理融入新型農民培訓體系,以達到向農民傳授數字知識進而積累文化資本的目的。這一范式轉換驅動農村職業教育組織樣態的變革。數字技術賦能的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將融入鄉村經濟、嵌入鄉村科技、融入鄉村文化、滲入鄉村人心、匯入鄉村生活、納入鄉村議程,并通過傳授技術知識、培養數字技能、滲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鄉村技能文化。
文化決定了數字化轉型的挑戰和潛力,但倘若未生成必要的“文化意識”,即使是再美好的數字戰略也將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陷入困境。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滋養了鄉村數智文明。鄉村生活與鄉土文化既彼此獨立,又相互浸潤。其中有兩種實踐路向:一是“守正”。鄉村生活是鄉村文化生成的背景,鄉村文化承載著鄉村生活的意義。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文化價值通過培育新時代所需的職業新人得以實現。農村教育數字化轉型使農民在數字人文方法論引領下全面認識農村教育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型數字鄉村文化,重現具有鄉土特色的數字教育人文景觀。二是“創新”。教育技術需在特定的人文環境下加以理解,方能透過表層數據獲取其內在的教育價值。數字技術與鄉土文化的深度融合,輔助實現鄉村文化資源的數字化保存。職業院校利用全息影像開辦“鄉村技藝數字展”,重塑鄉村文化傳播新渠道,培育鄉村工匠,創生出與數字化社會相協調、與現代化精神需求相適應的特色“農產品”。
三、轉型之理: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共生機制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改造”“推進教育數字化”。數字化賦能已經成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選項。若要真正實現農村職業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提升新型農民綜合素質,須將農村職業教育與數字鄉村戰略置于同一時空與境域,找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之道。農村職業教育與數字技術深層互嵌將經歷局部失序至協同共生的演進過程,這符合共生理論所倡導的事物之間協調耦合的理念。共生(Symbiosis)概念起源于生物學,由德國學者德貝里(Anton de Bary)于1878年首次提出。他認為,共生是不同種屬的生物體和諧共存的現象[19]。共生理論強調共生要素之間的功能互補與進化,旨在通過均衡的利益配置與能量交換,達成一體化共生的發展形態。共生機制包括“共生環境、共生單元、共生模式”[20]三種內容性要素,以及“共生界面”[21]這一連接性要素。以共生理論視角觀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這一“超系統”由“單元(參與主體)—模式(要素形態)—場域(施教環境)—界面(聯結系統)”構成。農村職業教育是農村社會系統中最為開放、最為活躍、最為復雜的全息性教育類型。其數字化轉型能夠加速農村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延伸與轉換,數字技術賦能職業教育則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持續推送必要的資金、設備、人才支持。換言之,農村職業教育通過“自系統”與數字技術“他系統”的跨界融合,聯動生成了一種基于共建共享理念的“超系統”共生發展模式。對此,基于對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內在邏輯的深入探討,筆者以共生理論為分析框架,以共生環境、共生單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為切入點,力圖擘畫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共生機制。
(一)共生單元
共生單元是共生系統的基礎要素,其為共生程序的演化發展提供物質基礎與直接動力。以共生單元內容觀之,農村職業教育將在“政—校—企—村”多方主體聯動的生態鏈上實現技術化轉型。在數字化轉型進程中,農村職業教育各共生單元之間并非零散的組織合作,而是形成基于共同育人目標的緊密伙伴關系。由政府、職業院校、企業、農民(農戶)等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共生單元之間彼此融合、相互協作,筑牢數字農村職業教育共生系統的“地基”。
政府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共生系統的主導者與兜底者,承擔了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與義務,其工作重心是農村職業教育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問題,通過規劃、列支數字技術賦能農村職業教育建設專項資金,引導社會多元教育行動者形成自發、利益耦合的緊密協同育人網絡,借助利益協調機制和監督管理機制,確保農村職業教育網絡高效運行。職業院校與涉農企業是共生系統的推動者,其立足鄉情,識別與考量農村數字群體的使用特征與應用需求,提升技術賦能產品和服務農村職業教育的適用性與精準度,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均衡發展。通過教育智能化、平臺一體化、教學網格化、治理數據化、應用規模化,解決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覆蓋窄、程度低、落地難”等問題。農民(農戶)是共生系統的直接參與者與受益者。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聚焦以小農戶為代表的新型經營主體開展職業教育培訓,開設流動課堂、云端課堂、田間課堂,支持職業教育培訓利用“云上智農”等線上平臺,與農技推廣人員進行實時交流、成果速遞和服務對接,以培養更多具有較高學歷層次的新農人。
(二)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共生單元的實踐形式與互動方式,它反映共生主體間信息交流與能量互換的關系。以利益分配維度觀之,共生模式可細分為“點寄生共生、間歇偏利共生以及連續互惠共生,其中連續互惠共生是最理想化的共生模式”[22]。在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進程中,政府部門、職業院校、企業、農民(農戶)基于互惠共生關系組成“命運共同體”,形塑融合發展的一體化共生模式。
詳述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各共生單元在跨越寄生偏利、追求連續互惠共生的過程中呈現如下特征:其一,普惠性。承載著算法公平的數字技術工具在保障農民平等分享數字職業教育紅利、以數字包容推動區域和群體教育資源分配方面的功效顯著。弱勢群體機會平等獲得數字技術與技能培訓服務的現實,折射出互聯網絡無邊界普惠的功能。其二,包容性。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首先是共生單位包括意識、組織、能力在內的相互融合過程。作為數字化農村職業教育再造的聯結紐帶,數字技術橫跨時空的阻隔,將零散“不在場”的農村教育資源吸納至組織共同體,打造教育新生態。其三,開放性。區別于傳統農村教育形態,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將持續突破職業院校、涉農產業、新農人等共生單元間的價值壁壘、行業界限,與平臺打造數據聯結通道,使學校與企業、線上與線下、田間與車間緊密銜接。諸如此類,無不體現出鮮明的開放性特征。
(三)共生場域
共生場域是共生關系賴以產生與運行的外部環境。它囊括以數字基礎設施為主體的硬環境與以政策法規為主體的軟環境兩大要素。合宜的共生環境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共生系統運轉的前置條件,其通過健全高效協同、鏈接互通、開放共享的教育服務,以及資金保障、信息安全等制度體系,對農村職業教育數據進行靶向收集、智能分析與實時反饋。
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硬環境泛指數字農村職業教育基礎設施,軟環境則指相關制度環境及共生單元具有的數字素養。前者遵循“新經濟→新技術→新業態→新職業→新技能→新專業→新課程→新課堂”的基本思路,推進以全新智慧校園、智慧教室、智慧企業、智慧車間、智慧農場、智慧學伴等為主體的數字中樞建設,完善新的農村職業教育基礎設施,提升國家農村數字教育平臺能級。軟環境包括鄉村振興戰略和數字鄉村戰略背景下的職業教育政策。隨著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面向新發展格局打好農村產業鏈現代化“攻堅戰”成為新的歷史任務,而建設數字鄉村的首要工程就是推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農業的數字化離不開教育的反哺。近年來,《職業院校數字校園規范》《職業教育信息化標桿學校建設指南》等政策文件的出臺,為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硬件設施建設提供了政策依據。對職業院校的人才培養方案、師資隊伍、教學改革、教材建設等方面進行全方位改革,為教育強國建設創設了有利的人文環境。
(四)共生界面
共生界面指共生單元之間傳導信息與能量的機制,其功能的強弱與規則的好壞決定共生系統動力機制的水平與效用。在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算法驅動、產教融合、技術生態三個維度構筑了以協同開放為特征的共生界面。其一,算法驅動是基礎。算法設計的功能體現于消解傳統算法的偏利傾向,建制系統化職業技能培訓的信息推動模式,協助次級勞動力群體形成新的職業圖景,促進勞動者職業生命增值,激勵新農人在職業場域實現個體價值。農村職業教育系統設計需要將“算法正義設計”納入系統規劃,借此提升次級勞動力群體對數字化時代勞動者圖像的認同程度,并將其轉化為群體內部職業發展與個體成長的重要驅動力。其二,產教融合是核心。當前“數字下沉”“技術進鄉”行動日益轉變為助益農村產教融合迭代升級的革新力量。職業院校將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以涉農特色產業為基礎,創新農民常態化的培訓機制。通過對產業發展方向的研究和探索,職業院校打造示范田間課堂、移動課堂、遠程教育等多渠道教學模式,匯聚大量跨域沉積分散資源,因地制宜地構建特色職業教育模式,提升職業教育培訓服務水平。其三,技術生態是保障。技術生態論是一種橫斷性的思維范式,其深刻意蘊凸顯為數字技術賦能農村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技術“生態位”。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數字化轉型錨定技術研發,在政府、學校、企業、鄉村多方主體聯動的技術生態鏈上實現技術生態化。技術生態嵌入或可為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營造必要的機制保障,涉農職業院校運用數字生態系統實現各利益相關者間的跨界合作與資源交互,促使教學更加科學、高效、精準。
四、轉型之路: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行動框架
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是農村職業教育各主體為迎合數字化浪潮自主進行適應性改變的過程,是以數據為驅動的思維轉變、以技術為支撐的要素衍變、以人的數字化生存為要旨的系統創變過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在“為誰轉型”“轉型什么”“如何轉型”等問題上,均強調教育主體精神的輻射價值。以人工智能為軸心的數字技術為基礎,促進共生單元、場域、模式、界面的有機整合則是此次教育試驗的重心。從共生語境觀之,構建開放包容、互聯互通的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行動框架迫在眉睫。
(一)釋放共生單元內驅力,激發主體互惠協作意識
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所引發的農村職業教育系統性變革,要求各利益相關者從生產方式、思維模式、教育范式等維度均做出適應性改變,即它不僅依托教育系統內部的職業教育理念、教育組織形式、產教融合模式、課程目標內容、課堂教學方式等要素的創新,更需要教育主體凝聚互惠協作共識,匯聚各方資源,協同發力。如前所述,農村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轉型發展離不開多元利益主體的協同參與。其一,政府部門進行前瞻布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軌制”頂層設計構建模式,在不斷完善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政策規范的同時,瞄準發展中的難點、痛點、堵點問題精準施策。制定統一實施規劃、標準與框架,出臺教育數字化成熟度評估標準,數字平臺開放、資源共享、數據對接的評價標準,形成以國家與地方政府主導、職業院校為主體的聯動式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發展機制,構建智慧教育平臺及與之配套的公共服務體系。其二,職業院校應轉變辦學理念、價值主張、戰略方向及育人方式,涉農專業積極探索以“專業課程、實踐課堂、鄉村課題”為核心的人才培養體系。其三,涉農企業應主動立足農村職業教育實踐,對接數字鄉村發展需求,提供高質量的數字化教育產品和持續性的教育服務。聯合農村職業院校共建實習實訓場所、補齊數字化實訓設備,以創設學習者實習實訓的優質條件。其四,作為教育改革的直接參與者,農民(農戶)的參與意愿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內生發展的關鍵,其制約數字化轉型共同體的行動。通過相關職業教育培訓政策、信息的有效傳遞,使農民群體意識到數字技術賦能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價值,并依據其利益訴求,以“農民為本”進行價值塑造,推動其更便捷地掌握必備的職業知識與技能,實現農業農村發展。
(二)發揮共生模式調配力,提升新型農民數字素養
彰顯鄉村人文價值是數智時代農村職業教育的重要向度。扎根鄉村、服務鄉村、面向農村勞動者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義。人的生存是技術性生存,技術的本質與人的本質有一致性,技術應回歸人性、承載人文、以人為本[23]。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應兼顧經濟價值和人文價值,促進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個體可持續發展。在此理念下,共生機制需關照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共生關系的穩定。連續性互惠共生模式則有助于實現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資源的合理分配,以應用“新農具”與培育“新農人”為目標的數字應用技能培訓被視為提升新型農民數字素養的先導行動。一方面,開展數字化“新農具”應用能力提升行動。近年來,隨著電商直播經營形式普及至鄉村,數字技術與傳統農業日益結合,數據化作“新農資”,隨時傳播“新農技”,以移動手機代表的智能終端已演變為數字時代的鄉村“新農具”。對此,農村職業教育需加強數字鄉村應用場景的教育普及和擴散效應,以“主導+主體”為理念、“線上+線下”為引擎、“網絡+網格”為模式、“制度+技術”為保障,推進課程資源開發。孵化面向真實生產經營的活動場景,以拓寬數字化“新農活”場景,靶向農民數字化“新農具”運用能力,使數字農業的溢出效應“內在化”,助力智慧農業發展。另一方面,實施“新農人”數字應用技能培訓行動。培育“新農人”是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職業教育提出的現實要求。職業院校與涉農企業需將“新農人”數字素養作為農民數字應用技能培訓的重要內容。激發農民信息化基礎設施學習興趣與使用意愿,進行量體裁衣式知識技能培訓;匯集整合新技術推廣,健全縣域數字鄉村科教云平臺,組建在線學習共同體與學習資源庫,使廣大農民能夠通過微課、直播課等形式在線接受教學與輔導,助推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業產業的深度融合,努力使數字鄉村建設有“智”更有“質”。
(三)增強共生場域拓展力,打造數字化教育新基建
長久以來,農村職業教育受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等外源依賴性困境及自身內部變革沖擊等內源發展性困境影響。這無疑需要加大職業教育資源調配力度,著力打造數字化農村教育新基建。打造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新基建的目的是拓展農村職業教育場域的時空邊界,為廣大農民提供場景更豐富、內容更多元、使用更便捷的體驗服務。具體而言,它包括新網絡、新平臺、新基地和新安全四項領域。在新網絡方面,職業院校可聯合網絡通信供應商和運營商,以云計算、大數據基礎設施等“云”,互聯網、物聯網等“網”及手機設備、學習終端等“端”的“云網端”融合為重點,對校園網絡基礎設施進行迭代升級,推動農村數字職業教育網絡建設。在新平臺方面,搭建農村職業教育數據分析平臺,支撐產教融合、課程設計、學生管理等領域的專項大數據分析與應用。通過采集學習者大數據,進行網絡抓取和解析、數據挖掘與可視化、視頻圖像集成開發等,繪制農村職業教育數據資源圖譜。在新基地方面,職業院校應廣泛應用AR、VR、HR、元宇宙等技術,圍繞企業生產經營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規范,對接“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生產經營環境、服務流程與設備設施。建設專業虛擬仿真實訓中心、體驗中心及研創中心,營造與實際職業情境、技術研發過程對接的虛擬仿真環境。在新安全方面,對數據搜集、整合、轉換、存儲、維護等活動進行規范,提高數據應用的安全性。要夯實風險識別、終端加密、網絡管理、遠程認證四大安全底座。職業院校要基于云計算、云渲染的理念,跟蹤調研用戶黏性和活躍度,利用“內容分發網絡”“算力網絡智能選路”“網絡智能調度”等在內的5G關鍵技術,筑牢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安全屏障。
(四)疏通共生界面傳導力,完善優質資源保障體系
如何消弭數字技術與資源嵌入農村職業教育過程中的“區域差”“代際差”“供需差”,全面釋放數字技術賦能農村職業教育的普惠效應,是未來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著力點。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并非僅關注技術的表層應用,更要關照應用背后的底層邏輯及制度保障。其一,構建資金保障體系。政府部門應明晰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意蘊,并出臺配套支持政策,緩解農村職業院校教育資金投入短缺問題。完善以數字化教育服務設施為主的現代化、標準化農村職業院校軟、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其二,完善跨界協同機制。各行動主體需深刻理解職業教育的內外部運行機制,探索數字化轉型情境中的農村職業教育新教學模式、治理方式和評價方法,為農村地區提供優質的在地化、校本化數字職業教育課程,加強教師數字能力培訓,在不同應用場景中形成數字化轉型的實踐經驗與典型案例。其三,健全風險保障機制。數智時代人類福祉的理想形態是技術增進社會福祉與福祉技術化的良性耦合[24]。風險保障機制建設致力于規范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中所產生的數據流動、整合與更新。健全新一代移動通信基礎網絡架構及通信網絡安全標準;加強數字認責,明確數據負責人的權利和義務,推動農村職業教育數據資源按需共享、安全使用、有序開放,有效規避風險。
五、結語
強國必強鄉村,教育強國只有實現農村教育的“強”才能完整。立足教育強國建設愿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這一議題現實地呈現在職教工作者和理論研究者面前。筆者從共生理論視角,細致分析了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場域、共生界面;相應地,從釋放共生單元內生力、發揮共生模式調配力、增強共生場域拓展力、疏通共生界面傳導力四個維度著手提供實踐的行動框架與可行路徑。本研究的作用可能在于:一是聚焦農村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賦能價值意涵,詮釋了其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增益效應;二是將共生理論四要素“耦合”于研究對象,相應地提出了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新形態。未來學界應致力于探討如下議題:一是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價值既已凸顯,那么如何在“三農空間”范疇激發轉型價值擴散的內生動力,有待進一步澄明;二是作為農村文化基因的鄉土價值,不應因現代化技術廣泛應用而式微,故如何以共同富裕為愿景、以鄉村資源為基石、以文化傳承為使命,細述鄉土文化的現代價值,因村施策地為其再生產持續注入新動能、培育新優勢就顯得尤為重要。概言之,同生共構于教育強國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議題,未來學界將持續從“共生—共享—共建”維度講好農村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與發展的“中國故事”。
[參考文獻]
[1]李鵬.益貧式增長:鄉村教育促進共同富裕的模式、困境與對策[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9(3):191-199.
[2]Machado A ,Secinaro S,Calandra D,et al.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Industry 4.0:a structured literature review[J].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amp;Practice,2022,20(2):320-338.
[3]李曉夏,趙秀鳳.數字賦能與鄉村人才振興——“數商興農”背景下新農人培育循環體建設研究[J].成人教育,2023,43(9):36-42.
[4]趙書琪.教育強國背景下職業教育文化空間建設的內在理據、應然樣態與實踐路徑[J].教育與職業,2024(8):100-106.
[5]李華.信息時代鄉村教育的數字化轉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22:前言.
[6]王天平,李珍.鄉村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取向與實踐路向[J].重慶高教研究,2023,11(4):14-22.
[7]王樹濤,鮑俊威.數字化轉型助推中國式教育現代化:內在邏輯與發展路徑[J].中國遠程教育,2023,43(11):1-10.
[8]楊智,楊文杰,王佩.數字教育賦能鄉村積極老齡化的行動邏輯與推進路徑[J].職教論壇,2023,38(5):73-82.
[9]劉惠燕.新一代信息技術賦能數字鄉村高質量發展研究[J].西南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3,7(3):9-14.
[10]邱利見,劉學智.人工智能時代的鄉村教育振興:機遇、挑戰及對策[J].教育學術月刊,2023(5):47-53.
[11]王斌,張霞.農村職業教育服務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研究[J].教育與職業,2023(19):99-105.
[12]陳紅娟,張婷,薛雅文.涉農高職院校面向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功能定位與實現策略[J].教育與職業,2024(12):46-52.
[13]陳塵.教育數字化轉型賦能城鄉教育協同發展現實路徑[J].河北能源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23,23(2):40-43.
[14]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OL].(2023-08-28)[2023-09-20].https://cnnic.cn/NMediaFile/2023/0908/MAIN1694151810549M3LV0UWOAV.pdf.
[15](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M].劉懷玉,王士盛,羅慧林,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41.
[16](加)德雷克·格利高里,約翰·厄里.社會關系與空間結構[M].謝禮圣,呂增奎,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92-93.
[17]IHDE D.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from garden to earth[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20.
[18]何哲.數智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基于技術、制度、文化、道德與治理視角[J].電子政務,2023(8):48-60.
[19]Oulhen, N., Schulz, B.,Carrier, 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einrich Anton de Bary's 1878 speech, 'Die Erscheinung der Symbiose'('De la symbiose')[J].Symbiosis,2016,69(3):1-9.
[20][21]袁純清.共生理論——兼論小型經濟[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7-8,67.
[22]胡海,莊天慧.共生理論視域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共生機制、現實困境與推進策略[J].農業經濟問題,2020(8):68-76.
[23]李政濤.現代信息技術的“教育責任”[J].開放教育研究,2020(4):13-26.
[24]趙書琪,于洪波.破解“科林格里奇困境”:教育數字化轉型風險治理的向度、原則與進路[J].中國電化教育,2024(3):5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