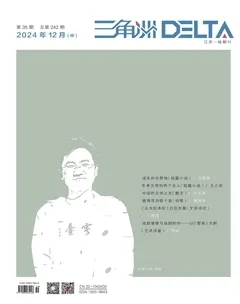從日常的閑談中捕獲寫作的靈感
2024-12-29 00:00:00馮祿添
三角洲 2024年35期

我平常比較留意觀察身邊的人和事,比較留心人們茶余飯后的話題,這些話題,有老舊的,也有新鮮的。我常常思考,為什么有些話題像一陣風一掠而過,為什么有些內容會被反復咀嚼。這些聽在耳朵里的話,還有生活中看得見的變化,往往在一瞬間能激發我創作的靈感。
近年來,常有一些關于某地民眾因為拆遷一夜暴富的故事,在小區里街坊們散步的閑談里,在辦公室里同事們口中津津樂道。前些日子和幾位在鄉鎮基層工作的朋友在小餐館里小聚,推杯換盞中他們談到在動遷工作中的一些親身經歷,引起我強烈的興趣。城鎮化進程產生了一系列的故事,當中也不可避免夾雜著一些不太和諧的小插曲,一個關于“釘子戶”的故事在我腦海里悄然萌芽。創作《消失的甘蔗地》,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基礎。
釘子戶劉鳳嬌和老侯,兩個行為一致的人,出發點卻不同,老侯的目的顯而易見,毫不遮掩,就是要囤貨居奇,坐地起價,謀取更加豐厚的政策紅利。劉鳳嬌的執拗,則表現為對過往的不舍,是對家園的無限眷戀。對于家園的推倒重建,無論建設得多好,總有一些東西無法復制,都意味著對前半生的徹底告別。生活中總有一些無法用物質去衡量的東西,值得人們去留戀,去堅守。然而再倔強的人,也倔強不過時代洪流,更有一些非物質的東西,令人無法招架,哪怕像劉鳳嬌這樣一手締造出甘蔗地村的女強人,在堅守曾經的王國時無比強悍,卻在與兒女的角力中黯然敗陣,在親情面前低頭。這原本也正常不過,人世間最美不過親情,值得我們讓步。然而當親情淪為一些人牟取更大利益的工具時,是多么讓人可悲可嘆。
在創作中我也自我反思,有些人,有些事,和我們看到的和想象中的不一樣,透過表象探尋其中的奧秘,這是我樂于寫作的原動力。愿以生澀的文字,書寫心靈的脆弱和倔強,在社會大潮與個體之間尋求和解,在復雜人性里尋找光。
猜你喜歡
英語文摘(2022年9期)2022-10-26 06:58:32
音樂教育與創作(2022年6期)2022-10-11 01:15:22
少兒美術(2021年4期)2021-04-26 13:45:40
創作(2020年3期)2020-06-28 05:52:44
讀友·少年文學(清雅版)(2020年2期)2020-06-15 11:16:34
讀友·少年文學(清雅版)(2018年3期)2018-09-10 06:04:54
百科探秘·航空航天(2017年3期)2017-07-12 14:13:44
文藝論壇(2016年23期)2016-02-28 09:24:07
中國火炬(2014年3期)2014-07-24 14:44:45
小說月刊(2014年1期)2014-04-23 09: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