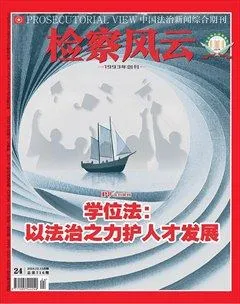氣候變化風險與金融穩定

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商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市法學會常務理事、金融法研究會副會長、案例法研究會副會長,綠色技術銀行總部首席法律顧問、研究院院長。
盡管當前綠色金融、氣候金融等新概念不斷涌現,但對于氣候變化、環境惡化等因素如何影響金融市場,關注者相對較少。氣候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機制非常值得關注,氣候變化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上海作為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必然會對全球金融穩定與氣候變化議題高度關切。
當前,金融在解決氣候危機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的作用被高度重視。各國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逐步認識到,如果不能建立氣候變化與金融穩定的監管法機制、各類金融機構若不能將氣候變化風險納入金融風險管理框架,則可能對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造成威脅。筆者注意到,2024年10月1日起在滬上實施的《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新增了發展綠色金融的專門條款,對上述議題也有所回應。本文將通過分析氣候變化與金融穩定的傳導機制,提出相關的監管應對措施。
氣候變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及其傳導機制
2015年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首次提出,應將氣候相關風險分為三種:即物理風險、轉型風險和責任風險。后來,學者們將責任風險歸入物理風險類別,理由是氣候變化導致實體經濟的物理損失,可能進一步惡化自身并無物理損失的其他資產價值。
物理風險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物理風險指異常天氣事件嚴重損害企業、家庭、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導致金融和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風險:
其一,由于氣候災害可能導致受災主體和金融機構的資產遭受物理損失,從而影響單個金融機構進而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諸如,由于資產的物理損失,那些投保的資產的損失多數由保險公司予以承擔,因此氣候災害對保險公司的影響最為突出。如果氣候災害發生頻次多且災害的嚴重程度高,則會直接導致保險公司沒有資本支持對全部投保資產的巨額理賠,從而影響保險公司的持續經營能力,甚至可能導致保險公司破產。在此過程中,保險公司為自救,可能會拋售其大量資產以補充資本金,這可能對二級市場的穩定造成直接沖擊。
其二,由于氣候災害直接導致資產物理受損,如果這些資產是給銀行的抵押資產,將導致抵押物價值受損。因為受災居民和企業的資產減少,可能增加貸款違約率,而抵押物又不足以彌補貸款違約損失,從而使氣候風險傳導至銀行體系。
其三,氣候災害導致受災地區的銀行服務網點運營暫停以及短期融資的困難增加,從而觸發金融機構、居民和企業的謹慎性資金需求增加,進而使流動性需求增加。如果央行不能及時提供流動性,市場“錢荒”極易威脅金融穩定。
轉型風險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轉型風險是指社會在向低碳經濟轉型過程中,氣候政策、技術、市場情緒等發生變化,導致資產價格變動或廣義的經濟危機(IMF,2019),即公共或私人部門為控制氣候變化采取的有效政策及行動帶來的金融風險,這種風險是成功應對氣候變化的代價。
轉型風險主要圍繞“擱淺資產”。國際能源署定義擱淺資產為:在其正常使用壽命前結束使用、不再產生經濟效益的投資,包括礦產開采權、化石燃料儲備或可能導致高碳排放的基礎設施等。換句話說,因為低碳轉型,加快了那些大量高碳資產的折舊速度,或在使用周期中提前沖銷。由于擱淺資產的價值受損,很可能導致高碳企業的資產損失,增加了其信用風險和貸款違約率。高碳企業將擱淺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中提前沖銷,不僅造成了經濟損失,還會影響這些高碳企業從金融體系繼續獲得融資的能力。這是典型的因為氣候變化導致實體資產受損,從而造成整個金融體系出現風險的情況。
此外,氣候政策變化與轉型風險也密不可分。如果在低碳轉型期間,政策導向不明朗,具體執行出現反復,則無法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很難形成公眾和投資者對低碳轉型的充分信心,難以正確引導投資者的資金流向,增加低碳轉型的經濟成本并可能加劇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
助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經驗及建議
從全球金融領域來看,金融加快綠色轉型,包括資產管理機構、商業銀行、保險機構在內,都在經歷新的監管和合規轉型。近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批準了一項新規則,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該規則名為“投資者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加強和標準化”。此外,公司必須解釋風險以及他們如何管理這些風險,例如對收入和支出的影響。而歐盟作為國際綠色金融領域最為積極推動和實踐的經濟體之一,早在2019年6月,歐盟委員會技術專家組就連續發布了《歐盟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歐盟綠色債券標準》以及《自愿性低碳基準》三份報告。其中長達400多頁的《歐盟可持續金融分類方案》將成為歐盟可持續金融發展的重要基礎。
在全球氣候治理的背景下,中國也加快了低碳轉型的步伐:中國人民銀行2023年發布的《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已與之前的《綠色信貸統計》《綠色信貸指引》形成制度協調。202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生態環境部、金融監管總局和中國證監會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綠色低碳發展的指導意見》。202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在建設國際綠色金融樞紐方面,政策體系框架日漸完備、基礎設施齊全、要素資源集聚。早在2021年上海市政府在其發布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中,就首次提出了建設“國際綠色金融樞紐”的定位和目標。2021年10月,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印發了《上海加快打造國際綠色金融樞紐 服務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實施意見》。2022年6月22日,上海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通過《上海市浦東新區綠色金融發展若干規定》,使得上海綠色金融的建設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并納入法律保障促進范圍。2024年《上海市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促進條例》《上海市轉型金融目錄(試行)》的密集發布與實施,更是將具體產業、項目納入了綠色金融支持范疇。從基礎設施來看,上海能源與環境交易所作為全球最大的碳現貨交易場所,日益發揮著碳資產定價和引導企業減碳增效的作用。此外,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綠色技術銀行等一批機構總部落戶上海,為上海綠色金融國家樞紐的建設提供了獨特的條件。最近,《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得以通過,新增了發展綠色金融的專門條款。此次新修訂的《條例》更是以地方人大立法的方式進一步推動著上海成為國際綠色金融樞紐。此外,上海成為國際綠色金融樞紐具有充分的要素資源,國際主要銀行、資產管理機構和保險機構在滬展業,必然會帶來豐富的國際綠色金融合規監管、綠色轉型經驗。
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積極順應全球金融綠色轉型的要求,將綠色金融中心城市建設目標納入其中,這包括本土金融機構治理和資產的綠色轉型,國內的金融基礎設施積極參與全球綠色金融組織和國際規則的制定工作。在關于氣候風險與金融穩定方面,上海應利用全球加強上海亞太臺風研究中心在全球熱帶氣旋綜合數據中心建設、基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熱帶氣旋災害數據深度應用和服務等方面研究對“氣象×金融”的數據和科技支撐,促進金融與氣象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動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再上一個新臺階。
(作者江瑛系同濟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