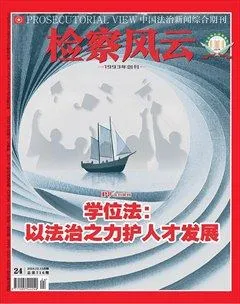古人的“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這個事,往好里說,是警惕性高,思維敏銳,見微知著,善于聯想,因小見大;往不好里說,則是神經過敏,小題大做,疑神疑鬼,無事生非,借題發揮。東漢時,大儒孔融只不過說了幾句對父母不恭的玩笑話,發了點牢騷,就被人舉報到曹操那里。曹操原本就對他懷恨在心,這回可抓到把柄了,立刻就上升到破壞以孝治天下國策的路線高度,把孔融全家殺害。西晉時,學者嵇康無心仕途,寫了一封信給勸他做官的朋友山巨源,表示拒絕做官。被與他有過節的顯貴鐘會構陷說是用心險惡,或有他圖,留著會后患無窮:“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挑唆司馬昭將其處死,《廣陵散》從此絕唱。
北宋蘇軾的烏臺詩案,更是典型的上綱上線冤獄。蘇軾的詩里面說到了龍、太陽、松柏,被無恥小人上綱上線說他是影射朝政,攻擊新法,詆毀君上,十惡不赦,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也多虧了王安石仗義執言,才救了東坡的命。而盛行于清朝的文字獄,則幾乎樁樁件件都是上綱上線的杰作。“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被上升到諷刺清朝統治者沒文化的高度。
當然,上綱上線也有說對的時候。大臣箕子看到紂王開始用象牙筷子,就認識到這是個原則問題,并立刻聯想到奢靡亡國的高度。他說,既然紂王改用象牙筷,下一步就會改使犀玉杯,改吃山珍海味,改住宏大宮殿,一味追求享受,無心理政,國家離垮臺就不遠了。他這話還真不算夸張,后來果然應驗了。
還有一回,劉備的上綱上線成了喜劇。蜀國遇到災荒,糧食緊張,劉備下令禁酒,家中凡藏有釀酒器具者,均以破壞軍國大計論罪,要重罰重判。謀士覺得有點太過,就想勸勸他,一直未得其便。一次陪劉備逛街,指著一男一女說二人宣淫,趕緊抓起來。劉備說,何以見得?謀士說:因其身上攜帶淫器。劉備大笑而悟,遂將此罪取消。
平心而論,上綱上線也是一種獨特的思想方法、話語方式,有時還有必要,可起到振聾發聵作用。但絕不能把上綱上線當成慣性與愛好,雞毛蒜皮的事也往綱上線上扯,動不動就搬出來嚇人也嚇自己,危言聳聽,夸大其詞,鬧得人人自危,氣氛緊張。畢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上綱上線,也不必把所有問題都拿來“透過現象看本質”,還是有事說事,該啥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