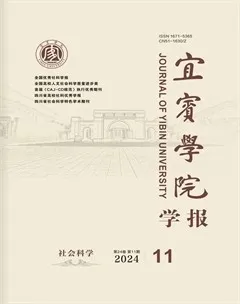區塊鏈技術背景下NFT作品權利窮竭原則的適用
關鍵詞:NFT數字藏品:權利窮竭原則:發行權:區塊鏈技術:智能合約
據CryptoSlate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NFT市場交易總量僅為8 200萬美元,而2021年則飆升到170 億美元,相較2020 年增長了21 000%[1],NFT數字藏品受到資本市場的狂熱追捧。但我國現行的著作權法尚未對發行權的權利用盡原則進行較為明確的規制。面對數字作品乃至NFT數字藏品的發行與轉售行為的規制則更為缺乏。“權利窮竭原則”是各國《版權法》關于權利窮竭的一條原則。在美國,立法者將發行權的權利窮竭原則表述為“首銷原則”,而在歐盟法域內則將其表述為“發行權用盡”。發行權用盡即在著作權人將作品原件或復制件首次出售后,受讓方的后續發行不再受該作品原始發行權的約束[2]。之所以規定該原則,主要是為了鼓勵作品自由流通,防止因版權專有性而對作品自由流通造成阻礙[3]。該原則最早由美國的Bobbs-Merrill Co.訴RIsidor StarusandNathan Straus 案①確立。首次銷售原則實際決定了二級市場上作品轉售的合法性,并可作為侵權的抗辯理由。據此,權利窮竭原則能否在NFT作品交易中適用,值得進一步探討。
關于數字作品作為商品的轉售行為中,權利窮竭原則能否適用的問題,部分學者持“肯定說”,認為應類推適用首次銷售原則,即把數字化的作品納入發行權規制的對象范疇[4]。“否定說”則認為,網絡環境下不可適用該原則,因為此時“發行權”與“所有權”的處分權能會因沖突失去存在的基礎,從而喪失發行權用盡原則存在的條件[5]。此外“折中說”主張發行權“有限用盡”,權利人可規定使用者在受讓數字作品時限定使用次數和范圍[6],以及利用數字技術特征建立信息網絡傳播權有限用盡規則,允許消費者附條件轉售[7]。但上述觀點均基于一般數字環境對數字作品交易是否適用權利窮竭原則進行考量,未探討在最新區塊鏈技術的賦能下,突破權利窮竭原則適用的“有形載體”前提與“合法復制”的限制,以實現數字作品特別是NFT作品適用權利窮竭原則的突破性探索。
就國外已有判例來看,美國國會唱片公司訴雷迪吉案否認了發行權耗盡原則在數字市場的適用②。美國雷迪吉公司在2009年設計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即通過“刪除-轉移技術”將數字化的音樂文件進行轉售。它可以讓新用戶在購買和下載指定的音樂文件后,在原用戶設備中使用特定的技術手段刪除原本的文件。然而美國法院卻認為權利窮竭原則不能直接適用于該種行為,因為“拷貝”行為實質上是將作品在另一種新的載體上進行再復制、再創造。法院認為,在生成新副本時,原稿是否被完全刪除,作品拷貝數量是否增加,都與拷貝行為沒有任何關系。即便轉售后將復制品徹底刪除,其行為實質也構成復制行為,也侵犯了復制權。但2012年,在歐盟審理的用軟公司案中,歐盟法院認為權利人是否通過“有形載體”來銷售軟件并不重要,而根據歐盟的《計算機程序保護指令》“軟件開發商對軟件的銷售控制權,在開發商收到交易資金時終止”認定數字軟件轉售適用首次銷售原則抗辯③。然而2019年,歐盟法院的態度再次發生了轉變。在Tom Kabinet案中④,電子書轉售行為被認定為“向社會公眾的傳播權”所控制的范圍,從而判定權利窮竭原則不能適用。
制定首次銷售原則所期待達到的法律效果,應是使得有用的知識成果能夠在社會中得到持續傳播并持續創造價值。面對NFT數字藏品版權交易的新形式,更需要探討權利窮竭原則能否適用于基于NFT這一新技術環境下的數字作品交易。首次發售后取得NFT藏品的合法持有人是否可對NFT 數碼收藏品進行轉賣,再次轉售該NFT數字藏品的行為其法律性質又當如何界定?
一、權利窮竭原則的法理及適用前提
(一)歐美現行法對“權利窮竭”原則的適用均強調“首次銷售合法性”
從立法現狀來看,歐盟2001年發布的《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規定:“對于作品的原件或復制品,在共同體內不得用盡發行權,除非該物品在共同體內首次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轉讓該物品的所有權是由權利持有人或其同意進行的。”而在《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重述”中,其第33條又規定:應當限制復制的專有權,允許對某些臨時性的復制行為作出例外規定。當復制行為非基于經濟目的且屬于進行其他合法行為的合理、必要前提時,這種復制行為便具備合理性及合法性。而《美國法典》則規定:“盡管有第106(3)條的規定,根據本章合法制作特定副本的所有權人,或享有授權的人,有權將該副本所有權出售,而不需要經過著作權人的授權”。由此可見,歐美現行法對權利窮竭原則的規制均強調“首次銷售的合法性”,即避免轉售行為侵犯作者的復制權。
(二)從權利窮竭原則的法理與規制目的突破“不得侵犯復制權”的限制
從著作權的產生起源與發展歷程來看,作品的產生以及作品著作權的存續需要依靠于有形物質載體。基于著作權與有形物質載體的高度依附性,且作品的發行與傳播都要依賴于有形載體的復制,作品的印制權和重印權便成為核心保護內容,復制權也在傳統著作權法中處于核心地位,由此呈現出復制權中心主義。《伯爾尼公約》亦未對發行權進行明確規定和界定。各國的立法也常用“出版”一詞概括發行與復制行為,這是因為在傳統的發行條件下,著作權人要進行發行,需要先對作品進行基于有形物質載體的復制,而復制行為本身也是為發行做準備。
因此,當作者授權出版某作品時,實際上便同時表達了同意發行該作品復制件的意思。可是,法律并非總能囊括社會生活的各種情形,各種復雜性會導致例外情況的發生。例如,著作權人可能只授權他人對作品進行復制,而沒有授權允許他人發行該作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人未經授權便發行了作品的復制件,作者的復制權并未受損,但其“發行”的權利則顯然受到了侵害。這種未取得作者同意便將作品的復制件投入流通進行發行的行為,毫無疑問損害了作者的著作財產權。為了解決這種情形下的利益沖突,“發行權”應運而生。通過設立發行權,一方面對作者行使復制權進行了補充,另一方面也為作者基于復制權而產生的“發行權利”提供更為有效的保護。
但是,發行權作為著作權人對其復制權的補充,其行使不能是無限的。比如在得到著作權人授權復制并發行后,著作權人如果對復制件后續的轉賣行為再次主張“發行權”,則會造成原著作權人對合法取得復制件有形財產所有權的買受人行使其所有權和處分權的妨礙,這將引發發行權和所有權的沖突。為了解決這一沖突,立法者又創設了權利窮竭原則。由此可見,權利窮竭原則的適用只針對作品的原件及其復制品的發行行為或轉售行為,其實質是對發行權與買受者所有權(流通處分權)的調整,要以發行行為為前提,并且只是對發行權的窮竭,不包括對復制權的窮竭,復制權仍屬于著作權人。
(三)歐美現行法適用權利窮竭原則以界定“發行權”為前提
《美國法典》第十七部分知識產權專章中規定:“所謂‘出版’是指將作品通過出售或其他所有權轉讓的方式,將其復制品分發給公眾的行為。為進一步分發、公開表演或公開展示目的向一群人分發副本或錄音制品的提議構成出版。作品的公演或陳列本身不構成發表。”《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將發行權規定為:“作者對其作品或復制品擁有禁止以銷售或其他方式向公眾發行的專有權”。而《伯爾尼公約》第3條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第6條均體現復制權中心主義:《伯爾尼公約》規定“出版指以復制件將作品傳播公眾,復制件發行須滿足數量和方式上的合理需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規定“作者享有通過銷售或其他所有權轉讓形式向公眾提供作品原件或復制品的專有權”。
何謂“單純的復制行為”?《美國法典》規定:“‘復制品’是錄音制品以外的物質對象,其中作品是通過任何已知的方法固定下來的,可復制或以其他方式傳播。‘復制品’包括除錄音制品以外的物質對象,作品首先被固定”。復制行為的實質,是把作品固定在物質載體上,從而構成作品復制件的一種行為。固定復制件的具體方式和手段并不重要,只要實現了復制件固定這一效果,即可認為復制行為已經完成。如在使用互聯網過程中,將作品的數據傳輸固定到網絡存儲介質中,實際上其行為已經形成新的作品拷貝件。這一“上傳——固定”行為實質上已構成法律意義上的復制行為。
據此可以得出:發行行為實質上是一種向不特定的公眾提供特定作品的原件或復制件、以使該作品原件或復制件在法律上實現所有權轉移效果的行為;首次銷售屬于發行行為,無論其是否通過網絡傳輸,但不包括單純的復制行為;而基于發行行為的發行權,是著作權人的專有權利。
(四)我國現行法未將“依托有形載體”作為界定發行權的前提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6項對“發行權”的界定是“將作品原件或復制件以出售、贈與等方式向社會公眾提供的權利。”但到了數字作品領域,學界卻對該規定產生了不同觀點。部分學者認為銷售作品的行為如果要構成“發行”需要以該作品具備原件或復制件的有形物質載體為前提。如果作品在數字環境中的流通,則不屬于發行權的規制范疇,而應當適用“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相關條款進行規制。實際我國現行的規定,并未明確將發行權的客體是限定為“具備有形物質載體”。其實與發行傳統作品相比,數字作品的發行主要是載體形式略有不同,而這是由數字作品的技術特性所決定的,其對著作權效果的實現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只要滿足將作品以所有權轉移的形式首次提供給公眾這一本質特征,即可認定其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發行行為。
發行行為和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主要區別并非“是否通過網絡形式”進行發行和傳播,而在于其對于作品流轉的效果究竟是“所有權的轉移”還是“經許可的使用權”。如果該首次流轉行為導致了作品“所有權轉移”的法律效果,無論其是否通過網絡進行流轉,均應認定其為“發行行為”;如果該首次流轉行為不涉及作品所有權的轉移,而僅為通過網絡進行授權的“許可使用行為”,則應界定為“網絡傳播行為”。
此外,發行行為所包括的對象應當包含無形載體。對于已經在網絡空間上架進行交易和流通的數字作品來說,作者在網站面向公眾提供鏈接以下載數字作品的行為,其實質是作者利用網絡技術手段實現將其作品的復制件公開提供給不特定公眾的行為。數字作品交易顯然符合發行權“將作品提供給公眾,以實現原件或復制件所有權轉移”的理論定義。況且,當初各國理論界之所以將“以有形載體為媒介”作為定義發行行為的前提,其主要是受限于當時的歷史和技術條件。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作品常以“書籍”等依托有形載體的方式存在,作品的產生、復制與傳播與“有形載體”具有高度的牽連關系和相互依存性。而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興起,數字作品特別是NFT數字藏品的網絡交易早就不再依托有形載體。我國著作權法,將發行權較為明確地界定為“將作品的原件或復制件以出售、贈予等方式提供給社會公眾的權利。”該條款并未明確數字發行是否包含在發行方式中,如果僅以字面意思將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的原件和復制件”理解為“有形件”,并且一定要固定在有形的實物載體之上,未免失之偏頗。
三、NFT 作品交易的法律實質與權利窮竭原則的適用
(一)NFT 作品交易的實質
數字作品按其產生的初始形態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數字形式經計算機技術輔助創作的作品,另一類是在傳統作品的物理載體上經數字化處理產生的復制件[8]。數字作品產生和儲存形式的特殊性,使其原件與復制件的內容在技術手段上的呈現是一致的。并且傳統作品皆需依靠有形物質載體來呈現,而數字作品由于其技術特性,可以脫離物質載體,所以其“物質載體”本身便不會像圖書、CD光盤等具備“載體”物權的稀缺性。但如果將數字作品鑄造成NFT,就可以讓數字作品的每一份復制件都與一組唯一的元數據相綁定,基于這種獨特的綁定關系,可以讓原本不具備載體物權稀缺性的數字作品,產生其權利憑證即NFT 與之進行唯一綁定和對應關系的“稀缺”效果。無論該數字作品本身是原件還是復制件,唯一的NFT僅與唯一的數字作品相對應。
在數字藏品市場交易中,雙方未必需要“交付”數字藏品本身,而僅需在區塊鏈上對NFT進行“所有權變更登記”即可。可見其區別于一般買賣合同的實物交付流程,但就其交易性質而言,仍成立買賣合同之債。并且一個NFT對應一個特定的數字作品,無論該數字作品本身是原件還是復制件,都不會影響NFT作品交易的法律性質,僅僅會影響該筆交易的價值。購買者基于對NFT的購買,將獲得與該NFT唯一對應的數字作品的所有權。作為一種物權權能,購買人將享有排他性占有、使用、收益及處分等物權權益。因此本質上來講,NFT數字藏品是將“NFT”與之唯一對應的“數字作品”進行唯一綁定的特殊數字作品,“NFT”是其所指代的“數字作品”的權利憑證,是“發票”,而“數字作品”則是該“發票”所指代的唯一“商品”。所以NFT數字藏品的交易,本質上就是通過買賣數字作品所唯一對應的NFT權利憑證,來實現與該NFT唯一對應的數字作品所有權移轉的買賣行為。
(二)NFT 作品的首次銷售行為應界定為發行行為
目前學界對數字作品乃至NFT 數字藏品的發行及銷售行為能否適用權利窮竭原則的最大爭議在于兩點:其一,數字作品的交易不涉及原作品有形載體本身的轉移,而發行行為通常要以有形載體所有權的轉移為前提;其二,數字作品的銷售行為,實質上是先將原作品進行復制,再將復制件的所有權進行轉移,只是這兩個行為的過程通常被視為一個行為,由于這其中一定會先進行復制行為,因此未經授權的復制行為可能侵害作者的復制權。前述案例中,美國法院認定二手數字出版物經網絡形成新復制件,如未經作者許可則屬侵權行為,實際上否定了轉賣的正當性[9]。歐盟法院卻認為復制行為若是轉售的必要程序而非不當獲利,且屬于合法轉售合同的一部分(即轉售合同所必需的附隨義務行為),那么這種復制行為便是合法且正當的。因此歐盟法院基于復制行為的正當性認定數字作品轉售行為的合法性,從而可以適用權利窮竭原則。
從發行行為的實質效果來講,數字作品的發行與實體作品的發行行為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作者在網站面向公眾提供鏈接以下載數字作品的行為,其實質是作者利用網絡技術手段實現將其作品的復制件公開提供給不特定公眾的行為,如果該首次流轉行為導致了作品“所有權轉移”的法律效果,無論其是否通過網絡進行流轉,均應認定其為發行行為。NFT作品購買者在支付了相應費用后,通過購買數字作品所唯一對應的NFT權利憑證,實現了與該NFT相唯一對應的數字作品的所有權移轉,從而取得與NFT相對應的數字作品的所有權和處分權。按照著作權法對發行行為的定義,則NFT 作品的首次銷售行為仍屬于發行行為,從而應當探討在區塊鏈技術環境下,權利窮竭原則在NFT數字藏品交易中的適用情景。
(三)權利窮竭原則在NFT 作品交易中的適用條件
權利窮竭原則要在數字作品特別是NFT 數字藏品交易中適用,除了需要滿足傳統作品適用該原則的基本條件外,還應滿足至少兩個要件:其一,發行行為的界定可突破“有形載體”的限制,即NFT作品非基于“有形載體”的首次銷售行為可界定為著作權法上的發行行為;其二,著作權人或者經其授權的主體對交易標的物明確是“出售”的意思表示,而非單純的許可行為,否則應適用信息網絡傳播權進行規制。
首先,需要界定NFT數字藏品的首次銷售行為即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發行行為。對于已經在網絡空間上架交易的數字作品而言,其交易實質是作者利用網絡技術手段實現將其作品的復制件公開提供給不特定公眾的行為,如果該首次流轉行為導致了作品“所有權轉移”的法律效果,無論其是否通過網絡進行流轉,均應認定其為發行行為,除非交易雙方明確其處分意思為“授權許可使用”。在“許可”而非“所有權轉移”的交易場景下,許可行為當然不是發行行為,不適用發行權用盡原則,而應適用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規定進行規制。
其次,關于NFT作品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的非法復制件的問題,權利窮竭原則的適用只針對作品的原件及其復制品的發行行為或轉售行為,其實質是對作者發行權與買受者所有權的調整,并且只是對發行權的窮竭,不包括對復制權的窮竭。NFT作品轉售過程中如侵犯作者復制權,應另尋其他路徑救濟,不能當然地直接類推“權利窮竭”原則不適用。
四、區塊鏈技術賦能下權利窮竭原則在NFT交易中的適用
(一)區塊鏈技術在數字作品交易中適用的前提
NFT作品的交易如滿足所有權移轉的法律效果,在突破“有形載體限制”的條件下,區塊鏈技術可以適用于數字環境下的作品交易。并且,權利窮竭原則的實質是對作者發行權與買受者所有權的調整,只是對發行權的窮竭,不包括對復制權的窮竭。
但是,學界主流觀點仍對“不得產生違法復制件”存有執念,即便遵守“不得產生違法復制件”這一前提,借助區塊鏈技術(包括NFT技術和智能合約)的賦能,能否對復制件的交易流通數量進行有效控制,能否足以保障交易安全,能否使權利窮竭原則在NFT數字藏品中的交易中的適用免去后顧之憂。在NFT作品交易中,當滿足所有權移轉的法律效果且突破“有形載體限制”的條件時,基于區塊鏈技術,無論其是否滿足“不得產生違法復制件”的條件,都可使權利窮竭原則在NFT數字藏品交易中適用,以促進NFT市場交易的發展與繁榮。
其實即便基于“發行權”是“復制權”的補充這一傳統理論的考量,依托于區塊鏈技術的NFT交易方式也可突破以往數字網絡銷售模式無法避開的復制權侵權障礙,而區塊鏈類似于不動產交易登記機構的角色,起著確權止紛的效果。只要NFT 數字藏品的受讓人對于該作品是合法取得的,其無需再次上傳該數字作品,便能夠在各大交易平臺上將NFT轉售。在智能合約將購買者記錄為新的擁有者后,交易即告完成。無論是首次交易還是后續交易,都不以生成新的復制件和實施新的交互式傳播為前提[10]。同時“二手”NFT作品的買受者,其實亦無需下載該數字作品便已獲得該NFT憑證所對應的數字作品的所有權,實質上成為該NFT所對應的數字作品的產權所有人。至此,基于區塊鏈技術,在數字藏品交易中適用發行權權利窮竭原則,已具備初步的基礎。
(二)區塊鏈技術背景下權利窮竭原則的具體適用
1. 區塊鏈技術可規避NFT 作品交易中的復制行為
著作權人通過區塊鏈技術讓每一份數字作品與區塊鏈上特定的哈希碼相互綁定,從而形成唯一確定的指向關系,以此實現數字作品的唯一確定性,并基于此產生稀缺性和可轉讓性。
法律之所以規定未經權利人同意,禁止復制其作品,以達到控制作品流通數量的效果,主要是為了營造一種“人為稀缺性”。在區塊鏈技術的賦能下,NFT數字作品的交易亦能產生這種稀缺性。比如使復制件的數量得到控制,在區塊鏈技術中就是使數字作品的復制件特定化。利用區塊鏈技術的獨特優勢,可使數字作品在買賣時實現所有權“一對一”轉移的效果,從而避免對復制權的侵害。在區塊鏈技術中,數據信息和原始交易記錄并不通過普通的計算機代碼進行保存,而是通過將原始數據編碼為具有特定長度的字符串,即轉化為相應哈希值后再記入區塊鏈,不同長度的輸入值會產生顯著不同的輸出值[11]。即便數字作品存在復制件,每一個復制件在區塊鏈上也只具備唯一對應的哈希值,NFT數字藏品亦具有稀缺性。
2. 智能合約技術可實現對復制權侵權的規避
發行人對同一作品鑄造不同的NFT 作品反復發行,以及在NFT數字藏品的交易流轉中,無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先由買家對NFT作品進行復制再將復制件傳輸轉移的過程,而區塊鏈技術并不能主動刪除數字作品復制件。如何確保區塊鏈場景下NFT作品在交易中的唯一性以及規避買家的復制權侵權風險呢?
“智能合約”的概念產生于1995年,由密碼學家Szabo首次提出[12]。通過智能合約執行這些“承諾”,也可歸于區塊鏈技術的范疇。智能合約可人為地在交易前制定交易規則。利用智能合約數字化和代碼化的特征,針對不同的NFT數字藏品制定個性化的交易條款。而后通過指令觸發合約,使其自動生成與執行,改變區塊鏈中數字對象的狀態和數值[13]。在制定智能合約時,可對交易達成設置特定的前提觸發條件,如限制作品的轉售行為以實現減少復制品的效果。將區塊鏈技術與智能合約的交易載體相結合,亦可保障數字作品及其復制品的唯一性。因此,在尊重著作權人自由的意思表示及交易各方意思自治的前提下,通過區塊鏈智能合約技術創設交易條件,以不明確拒絕即視為同意轉售為原則,同時建立統一的交易平臺和基于區塊鏈和智能合約技術的集合管理系統。
此外,區塊鏈智能合約技術以其分布式特性,在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方面展現出獨特優勢。它通過去中心化的方式,構建了一個多方參與的可信任機制。但在數據安全領域,智能合約中的缺陷設計可能帶來嚴重風險,因此語義分析是否嚴謹對安全驗證十分重要。進而對智能合約準確性和可靠性的驗證,特別是基于形式化方法的驗證,也不容忽視。而在隱私保護方面,智能合約的交易信息公開可能會導致安全與隱私的顧慮,因此,建立一個基于區塊鏈的匿名激勵機制亦具有必要性,該機制能夠通過節點驗證來保護用戶隱私,并同時確保激勵機制本身的安全性和實用性。
結語
NFT數字藏品交易本質上是利用區塊鏈等技術,將對應作品所有權轉移的買賣數字作品行為。因而通過網絡數據傳輸,轉賣軟件作品復制件的行為構成發行行為,而結合權利窮竭原則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其實質是如何實現對著作權人數字版權保護與促進NFT數字藏品自由流通之間的價值平衡。雖然目前權利窮竭原則適用的“有體性”限制已存在被突破的可能性且即便侵犯復制權亦不能直接否認權利窮竭原則的適用,但歐美各國仍對“不得產生違法復制件”存有執念。由于傳統數字作品的轉售過程中,必然先進行復制行為,進而借助智能合約等區塊鏈技術創設有關交易條件。當借助區塊鏈技術的賦能,對作品的復制件數量進行嚴格控制而足以保護發行者利益時,NFT作品的交易亦可適用權利窮竭原則,以實現利益平衡。
總之,在區塊鏈技術賦能下,即便遵守歐美各國“不得產生違法復制件”的傳統觀點,也可實現交易過程中必要的復制安全并確保NFT數字藏品的唯一性,使權利窮竭原則在我國NFT數字藏品交易中的適用免去后顧之憂。從而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賦能,無論基于何種觀點的考量,都可使權利窮竭原則在NFT數字藏品交易中適用,以促進NFT市場交易的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