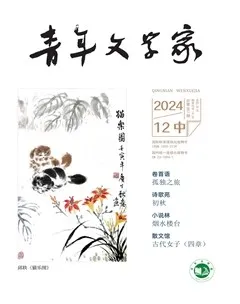舊日的老者在棲身的新土

長篇小說是時間的藝術,是對現實世界更廣闊、更深入的呈現。林森在長篇小說《島》與中篇小說《海里岸上》中,圍繞著當下的社會現實問題,書寫著舊時代的老人在新時代下逐漸變化的土地上的故事。清醒而浪漫的人文關懷,讓他的小說有別于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他用其在平淡中見溫情、寂寞中見怡然、圓滿中見悲愴的筆調,書寫著海島數十年發展步伐之下的眾生的悲歡。這一點在他的《島》和《海里岸上》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一、獨特的現實主義與家園挽歌
源于對社會生活的敏銳觀察與獨特體驗,現實主義是林森小說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島》與《海里岸上》兩部小說中,這種現實主義凝視具體體現為,將舊時代的老者安置于新時代的大潮之中,以其或無所適從,或向后追尋的生存狀態,來展示新老交替這一“火炬傳遞”過程中屬于個體與時代的陣痛。
在《島》中,林森直面當代中國具有普遍性的社會議題,敘寫了一個家園被拆毀的故事,并以“我”的視角,見證了守島老人吳志山的滄桑命運。環境的典型性帶來了人物精神力量的蓬勃,林森以開篇即高潮的方式,展露著他直面時代的決心:面對即將拆遷的老村,村民們的低沉,與伴隨著一聲聲驚叫的擲圣杯問神意的儀式交相輝映,呈現著彼時眾生面對“城市發展到農村”這股洪流時的無措。村民最終選擇妥協,在兵荒馬亂的拆遷中各奔東西。在此,林森設置了沉穩而目光長遠的伯父這一角色,來安排新與舊的過渡;設置了伯母這樣一位無助的哀慟者,成為更多普通人的寫照;也設置了堂哥這樣不堪于家園拆毀的悲痛,葬身大海的“逆流者”。在對“拆遷”這一社會問題的正面書寫中,林森以三位典型人物,呈現著海島發展中的陣痛與疑問。而在守島老人吳志山身上,我們能夠看到的,是獨屬于林森的回答:在清醒透視著海島變遷之時,他也渴望著現實的軌跡會有另一條走向。而這個變數,就寄托于吳志山身上。林森的現實主義落腳到吳志山身上,成了一種象征化的投射、心靈化的真實。
同樣的對比與寄托,也體現在創作更早的《海里岸上》中。年邁的船長老蘇與年邁的水手阿黃同樣帶有往日不再的落寞,死死把守著舊時代的遺物—《更路經》和羅盤,試圖延續這些古老傳承的溫熱,卻根本無力阻止它們以各種方式退隱,成為舊時代的陪葬品,同時也是新時代的紀念品。彼時,林森同樣以平淡的敘事筆調講述著挽歌悠揚的故事。懷舊者的命運也如出一轍地相似:出逃—返回—不被接納或無法適應—再度出逃—回歸—最終在遺憾中自我滿足。這樣的書寫,看似傳奇性大于真實性,實則是由外部的典型環境向人物內心精神力量蓬勃性的延展:當林森放眼于海島的幾十年,他看到了如潮汐般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規律,也看到了潮退潮漲之時,在沙灘上尋求一個洞穴的生靈。
事實上,就現實主義題材文學而言,遍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歷史文脈而言并不罕見。但林森的獨創性在于,其現實主義觀照的對象擁有獨特的內生矛盾。中國鄉土文學的傳統常常扎根于陸地,但海南島的特殊地理位置打破了鄉土中國的傳統想象。海南島是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同屬一個大陸架,但它同時是被大海環繞的島嶼,它是大陸島;對于海南人而言,大海與陸地一樣,都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文明的根基。而在陸地日新月異與被逐漸祛魅的同時,大海卻一如既往保持著那股神秘與危險。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憑借科學技術發展構筑起了現代文明,但在真正的海洋災難面前,這種文明依然難言具有優勢。即便吸取了歷史上威馬遜的經驗教訓,現實中的摩羯臺風依然能夠讓嚴陣以待的海南島停擺數日、損失慘重。而在《海里岸上》中,即便曾經多次帶領船員們安全返回,蘇父和老蘇卻在每次出海時都需戰戰兢兢—“海上找吃的,不靠賭氣,不靠膽子肥,得小心啊”,否則便是船毀人亡的下場:大噸位漁船葬身鯊魚腹的漁民以及因喝米酒下海而身死的曾椰子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
然而,即便海洋已經吞噬了無數島民的生命,帶來了許多災難,可海南島的人們還是需要大海。這種愛恨交織之下的鄉土情懷無疑具有了更加復雜的背景意味,甚至作為海洋文學的延伸途徑在傳統的瓦解過程中加入了自然偉力的影響,從而使得海南島的自然恒常性與社會變革性之間的沖突更加明顯。這也正是林森現實主義的特色所在。
因此,林森的現實主義具有一種冷酷的客觀與超然的悲憫:無論是《島》中的二堂哥,還是《海里岸上》中的阿黃,都可以稱得上是歷史傳統的維護者。可是,這些傳統的守護者固然悲壯可敬,但人終究無法抗衡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也無法改變社會發展的規律與趨勢。與托馬斯·哈代對冥冥之中神與命運的敬畏不同,吳志山與老蘇兩位主人公代表著林森對人類社會底層運行機制的尊重,以及對這份現實的追問與抉擇。林森并不是在呼吁回歸自然、回歸鄉村,而是如果舊家園不可避免地蹣跚著走向終末,如果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在次次陣痛中感激片刻的舒適,那么總要有人選擇出走和奔逃,選擇再造半生于化外。林森回應的,是“五四”前后興起又中斷的,在新時期得以再現的,屬于夾縫人、零余者的個體生存焦慮問題,是一個有限個體如何鼓起勇氣為絕不完美卻珍貴的往昔唱起挽歌的問題。這首挽歌并不一定好聽,這份勇氣并不一定合乎時宜,這種生活方式不一定能得到好的結果,但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經足夠有意義了。
二、懷舊者與他的洞穴
前文已經提到,《島》與《海里岸上》的眾生,對應著社會現實中的種種選擇。新時代的推動者,如主導老村拆遷與鬼島開發的政府、宋記者、收購硨磲的書法家等;過渡者,如伯父;抗拒者,如二堂哥與阿黃;懷舊者,如吳志山與老蘇。
從具體的文本實踐來看,林森在洞察到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并未選擇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入手書寫現實,而是向前的發展與向后的懷舊雙線并行,發展影響著懷舊的步伐,將其帶回大不同于舊日的面貌中,一波三折地完成融合,最終再給予懷舊者以另一種方式回歸往昔的機會。林森并未以更傳統的宏大敘事策略來呈現時代變幻發展的歷程,而是以肌理化的書寫,聚焦于兩大作為縮影的主人公,去回答新的時代環境下的社會問題。廣闊的海洋與精巧的小島在他的小說中得到了默契的結合。當老蘇的兒子與四堂哥在洪流中尋找著立錐之地,最終卻焦頭爛額時,林森給予了懷舊者更多的生存空間。我們不難看出林森的愿景:書寫時代是當代長篇小說不可或缺的使命,但作家幽秘的神思,恰在時代之外。小說畢竟是現實性與文學性共鼎的虛構世界,吳志山與老蘇也確然回應著現實的另一種可能。
那么,我們究竟從這兩位懷舊者身上看到了什么?其中一方面便是遺世獨立。這二人皆無法適應往日不再的生活,但選取的方式比二堂哥的悲壯與阿黃的痛楚來得溫和許多。林森給予了他們伴身的信物,以其傳承至今而不朽滅的珍貴性,與獨自過活的寂寞達成了公平的交易:老蘇因老伴兒去世失去了敞開心扉,講述數十年航海生活的機會,便以《更路經》與老式羅盤為至寶,日復一日用木麻黃的老根雕琢著象征遺憾與回憶的海船;吳志山度過冤屈的十年牢獄生活,歸鄉時面對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現實,孤身定居于無人島,壘起魚塘,挖好洞穴,以魚與酒寂寞度日,等待死亡帶走他與海沙。老蘇的懷舊者身份,本質上出于不可抗拒的歲月磨蝕;而吳志山,則出于過往的痛苦與現實的陌生。兩位幾乎脫離了時代前進步伐的老人,安于舊窩之中。林森試圖將其呈現為一種在寂寞中怡然自得的生存狀態。“有誰見過夜色蒼茫中,從海上飄浮而起的鬼火嗎?咸濕凜冽的海風之中,它們好像在水面上燃燒,又像要朝你飄過來,當你準備細看,它一閃而逝。”對于鬼火的書寫,恰是林森要在兩位老人身上表達的“島性”,朦朧至極而又確實存在于他的心中。
當我們閑游于海南島,立于山崖,望向大海,會有那么一瞬覺得:生活不該只是這樣。當每個人試圖和光同塵的瞬間,屬于心理的斥力就會發出警示。現實越是帶給普通人焦灼之感,人就越是需要這種遺世的奔逃。生命的意義不在于周旋于水流中,奮力抓取每一根稻草,而在于有選擇地離開。“這是他的島,是他的地盤,即使要死,也得回到這座島上。”平塔島象龜“孤獨的喬治”依偎著它的水坑,于連將他躲藏的山洞視為隔絕世界之地,老蘇與吳志山亦需要自己的寄托之所。
但需要注意的是,老蘇和吳志山的獨立具有必然的現實的妥協性,同時也是一種被動的獨立。前者不得不將老船出售,為自己的兒子忍痛出賣《更路經》和羅盤;后者也必須不定時回到漁村售賣海產、購買物資以維持孤島生存。這種不徹底的獨立蘊藏著某種暗示:現代人,哪怕只是生活在現代的,保有傳統精神態度的人,無論逃得多遠,也不得不為了保證自己的人之本質而短暫地回歸社會,以確認自己的存在。
另一個方面則是前進與融合。老蘇與吳志山,在懷舊者的身份之外,亦有些魯迅筆下過客的色彩:遠離布施,無謂于墳與百合花,而是不斷努力地平復自己的內心。二人奔逃的終點,是從神游中回歸于現實生活,并于現實中完成被接納的過程,從退休老人變成傳奇老船長,從“鬼島怪人”變成吳氏叔公,再尋此心安處。他們誠然在撕扯著舊己,但同樣也在融合著新己。
這種撕扯伴隨著一種心理上的死亡傾向。老蘇和吳志山都不約而同展現出了弗洛伊德所說的“求死欲”。弗洛伊德把求生的本能命名為“厄洛斯”(Eros,即愛欲),把求死的本能稱之為“桑納托斯”(Thanatos,即死欲)。前者表現為人們追求繁衍生存、愛與建設的創造,后者表現為人們向內自毀自虐、向外侵略征服的破壞。“老蘇很清楚,繼續往下,就會永遠留在海里了。他明明知道后果會怎樣,可海水更深處,還是對他有著強烈的吸引力。”這份吸引力一方面來自海洋,來自他不愿回歸現實妥協的一種抗爭的映射,同時也來自死亡。死亡與海洋一樣未知,那些死去之人的面孔在老蘇眼前浮現,死亡不再成為引發恐懼的存在,而是讓人目眩神迷,讓人感到安詳,如若不是有人相救,老蘇可能就真的回歸海洋了。而吳志山也面對著同樣的情況:“海里有著一股巨大的磁性,吸引著吳志山前往。”此時此地,沒有人能攔住他,所以“巨浪卷來,吳志山如愿以償”。
林森的“島性”,以離開為符號,但決然不是與現實世界的對立,反而是以離開的方式完成融合。在現實的世界里,東風并不知誰要向山而行,檐間的聲聲積雨亦不能憑空吹斷。這是屬于林森的,既浪漫又清醒的人文關懷。
三、林森與他的“島性”
那么,林森心中的“島性”究竟為何物呢?他并未批判在現實生活里焦頭爛額的人,并未過多傾訴對于無力反抗家園拆毀者的同情,也未曾給予在海浪上運籌帷幄、在孤島上獨守數十年的兩位懷舊者以宏大的歌頌敘事,而只是以一種扎實的敘述節奏,四平八穩地在縱向上開拓著空間,講述著眾生在數十年間的故事。
有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地方,那就是林森其實并不常用海南本土的方言參與他的相關創作。哪怕故事背景就是海南,故事主人公亦是海南人,但他們的話語卻常常以更加通行的現代普通話為主,即便是老一輩也不例外。可見,林森并沒有選擇以一種更具地方色彩的語言模式去構建他筆下的瓊崖人物,而是通過更加通行的語言去表明:無論新老、無論身份,這些角色都是具有現代性的“新”角色;這個故事也絕不局限于海南這一島之地,而是具有普世意義的作品。
林森的“島性”,在筆者看來是“尊重徒然的必然”。海南島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千年安于中國的南海之上,它的一切都刻印著屬于“老”的痕跡,老到仿佛天成。但它并沒有以此脫離于時代的發展與前進,反而成了排頭兵。當老村轟然倒塌之時,當老船成為海邊餐廳的包廂時,當老蘇的兒子變賣著硨磲時,許多人心中的“島性”,也就隨之消散了。但林森想要表達的“島性”,是讓荒謬和無奈擁有存在和認識的空間。于必然之中找到偶然,從偶然中發掘徒然,在徒然中和解自然。給予徒然空間,也是尊重必然的表現。
當代作家無法回避他們的時代使命,海島的孩子也無法拋卻他們對初始地的熱愛,林森正以老蘇與吳志山,謹慎地尋找著平衡。當他們漫游到生命的邊界,停滯在過往的一瞬時,林森將他們送還這個時代。沒有人屬于過往,但每個人最終都要成為過往。恰如吳志山家門前的對聯:“半生心事秋涼春暖愁歲月,永世恩情林秀風清憶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