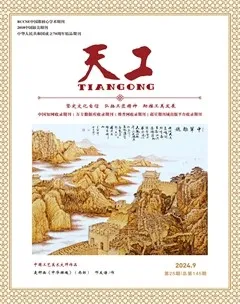麥積山石窟與巴中石窟造像比較
[摘 要]石窟造像源于古印度,中國藝術家對印度佛教文化及石窟樣式不斷吸收、融合、改造,并與本土精神相融合,以中國特有的藝術表現手法,使其更加符合中國文化傳統,逐漸契合國人的審美習慣和精神需求。麥積山石窟和巴中石窟都是佛教石窟發展鏈條上的重要一環,對其進行比較研究,有利于更加了解二者之間的聯系,同時體會到其產生差異的原因,理解和體會我國佛教石窟造像發展的歷程。
[關 鍵 詞]麥積山石窟;巴中石窟;石窟造像
[中圖分類號]K87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7556(2024)25-0094-03
文獻著錄格式:羅惠.麥積山石窟與巴中石窟造像比較[J].天工,2024(25):94-96.
一、開鑿背景方面的差異
麥積山石窟和巴中石窟的開鑿年代不同,麥積山石窟的開鑿始于后秦,而巴中石窟的開鑿始于隋代。麥積山石窟的開鑿在北魏時期達到高峰,在西魏、北周、隋朝時期持續有洞窟被開鑿出來,到唐代由于地震的影響跌入低谷,宋、元、明、清時期并無新開鑿的窟龕,主要是對原來的塑像進行重塑。巴中石窟的開鑿始于隋,興盛于唐,到兩宋時期造像逐漸減少甚至停滯,元朝并無開鑿,明清時期僅開鑿出一窟,民國時期也有少數窟龕被開鑿。從石窟開鑿的時間來看,巴中石窟很可能受到了麥積山石窟的影響,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交通的便利。巴中地處入川的重要交通道路米倉道南端,北接長安(今西安)南。同時,著名的絲綢之路,從河西走廊南下,通過甘肅東南部的秦州(今天水)至南鄭、巴中的交通也很發達。因此,巴中不僅可以到達唐代的二京地區,還可以由漢中經河西至西域,又可南下至成都。因此,巴中石窟造像深受當時經濟文化中心二京地區的影響,又因為從河西走廊南下經過秦州,所以也會受到敦煌莫高窟和麥積山石窟的影響。
二、材質和形制方面的差異
(一)造像材質的差異
麥積山石窟的塑像以泥塑為主。麥積山崖體屬第三紀紅砂巖,巖石的結構松散、粗糙,不易精雕細刻,歷代藝術家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礎上,以泥塑傳統的制作技藝,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基巖、木樁、蘆葦草、麻、雞蛋清、糯米汁等材料,結合石胎泥塑、木胎泥塑、浮雕等多種技法,利用黏土材料可塑性強和細膩的藝術表現力的特性,創作出一組組造型傳承有序、時代特征鮮明、歷經千年不朽的泥塑作品。巴中石窟大多為開鑿于崖壁上的淺龕,為摩崖石刻龕像。造像材質的差異主要源于兩座石窟群所處地區的石質不同。麥積山的石質是砂礫巖,比較疏松,不容易雕刻成型,因此麥積山石窟的雕塑多為泥塑。巴中盛產花崗巖、大理石、白花石等石材,都是石刻、石雕的天然材質,正是兩地石質的不同造就了麥積山石窟和巴中石窟造像的不同風貌。
(二)洞窟形制差異
佛教石窟中傳統的龕形是圓拱形,在我國出現最多的小龕就是圓拱形龕。麥積山石窟中多見平頂窟、圓拱形龕,這種龕形來源于印度,到唐代,北方石窟都一直在沿用這種傳統龕形。四川早期摩崖龕像也沿襲這一傳統使用圓拱形龕。巴中石窟突出的特點就是佛帳形龕極為發達,到目前為止,只在國內可見,巴中佛帳源自北方,西龕第21號龕中層的佛帳還保留了北方佛帳的許多特點,如:帳紋直條形下垂,三角形錘紋細密,龕眉上裝飾異獸、樂伎等,這些都是北方佛帳裝飾的特點。但是巴中石窟中的雙層龕是四川特有的,它實際上是雙口龕,外層方形,采用的是四川崖墓口部的做法,主要是因為南方雨水多,雙層口可以避免內龕直接被雨淋,其中外方內佛帳的雙層龕在巴中最突出,佛帳形內龕頂上多飾重檐,檐下懸帳、鈴等物形成龕楣,帳柱即為兩側龕柱,雕刻精美的龕楣和龕柱極具魅力,為巴中獨有。這是將北方佛帳形龕或圓拱形龕與巴中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也是巴中石窟本土化特征的顯現。
三、形象特征方面的異同
(一)面貌特征的異同
在巴中石窟中開鑿得比較早的北龕中可以看到隋代佛龕,這時的造像和同時期的麥積山石窟一樣,正處于風格轉變的過渡階段,頗有“面短而艷”的特點。例如,西龕寺第18龕主尊佛像肉髻低平,方圓形臉,雙眼下方內凹,頸上有蠶紋,雙耳肥大,戴圓形耳環,環上有耳墜。這與麥積山石窟第13窟中的主佛相似,主佛頭梳螺紋髻,前額有肉髻珠,方圓臉型,雙眼下方內凹,頸部有三道曲紋,雙耳肥大。他們都具有當時“面短而艷”的造像特征。
從晚唐開始,巴中石窟和麥積山石窟造像有了當時追求的豐腴、健美的審美趣味,體現出“曲眉豐頰”的特征,并且也增添了許多生活氣息。例如,麥積山石窟第5窟中,右龕主佛頭頂作螺紋肉髻,面部飽滿而偏方,雙目下視,眉彎如細月,頸項粗短,有三道曲紋,正是唐初典型的“曲眉豐頰”。在巴中石窟的南龕第68號龕雕刻了一組“鬼子母佛”,形象是一位體態豐腴的婦女,頭頂梳著圓髻,面部圓潤,眉彎如細月,身著長裙,戴著項圈、手鐲,身邊圍繞著許多胖小孩,所有人都盤腿而坐,顯得其樂融融。“鬼子母佛”造像衣著樸素,形態樸實,臉型已經完全具有漢人的特征,完全就是一位普通漢族母親的模樣。可見,這時的工匠已經是以普通老百姓為原型,借用佛經故事來反映世俗生活的情趣或教化人心。
麥積山石窟與巴中石窟在佛像形象特征上都體現了當時所處時代流行的審美趣味,如唐代盛行“曲眉豐頰”的豐腴之美。但是它們也存在差異,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麥積山石窟特有的“微笑之風”。麥積山石窟的“微笑”特征是有繼承和延續的,在最早的第78窟中,正壁主佛像的嘴角就已經洋溢著一絲微笑了,在此以前的“嚴謹之風”就消失了,具有趨于世俗化的特征,漢文化的融入表現在佛教造像上開始注重人性的表達,將佛像擬人化;到北魏時期,佛教造像漢化更加明顯,并引入南朝畫家陸探微創立的“瘦骨清像”圖式,佛教造像除了表現以瘦為美的氣質,其面部表情的“微笑之風”盛行,同時也運用了顧愷之“以形寫神”的藝術理論,增添了一些瀟灑脫俗、似文人墨客形象的風格。第121窟中竊竊私語的弟子和菩薩,以及第133窟中的小沙彌就是最好的體現。
(二)造像服飾的異同
隋代初期,當朝皇帝楊堅崇尚簡樸、杜絕奢華的習性使得這時的塑像去除了華麗之風,變得簡潔單純,麥積山石窟第37窟右側的菩薩佩戴花冠,秀發披于雙肩,頭部束有素雅的束帶,束帶自然下垂于雙肩,雙手自然、柔順地交疊在胸前,整體采用了直線式,束帶和衣物紋飾均為簡潔的直線。巴中石窟的佛教造像與同一時期的麥積山石窟一樣,造像風格簡潔而單純,這時的菩薩造像多袒露上身,配飾多為項圈、手鐲等。例如,水寧寺第1號龕的藥師菩薩,主尊身形挺拔、健碩,雙耳垂至肩部,身披袈裟,裙長至腳背,寶帶束腰,衣紋線條簡潔而流暢,簡單樸素的裝飾具有初唐的韻味。
到了唐代,麥積山石窟所塑的佛像數量較少,風格單一,由于唐朝的鼎盛,這一時期的塑像遵循了珠圓玉潤的審美風格,人物形象“曲眉豐頰”,服飾非常華麗。同時期的巴中石窟造像正處于鼎盛時期,這一時期的巴中石窟造像的服飾深受兩京地區的影響,也有著非常華麗繁復的服飾,例如,水寧寺第1號窟中的兩座脅侍菩薩立像,頭戴花蔓冠,身著華衣,手戴鐲,臂飾釧,披帛著地,瓔珞滿身。
最特別的是巴中石窟南龕第116龕中的天王,穿著一雙草鞋,這樣的天王塑像在全國僅此一例。由于川北地區的氣候濕熱,雨水較多,所以路面泥濘,工匠給天王穿著一雙草鞋,使得天王的形象被本土化,具有強烈的川北風味,體現出濃厚的世俗化特征。麥積山石窟第5窟中的“踏牛天王”頭束拳形髻帶三瓣式高冠,面相方圓,高鼻大耳,凝眉突目,赤須蚘髯,頭略左扭,雙手前伸至腹前,呈握拳狀,上穿緊身袍服,下著束口分襠褲,外面罩著明光鎧,腰束戰裙,腳蹬圓頭靴,踏在一牛犢背上,整體比其他石窟的天王像服飾簡單,沒有過多運用唐代士兵的鎧甲元素,具有當時西域少數民族武士形象的韻味。這兩個天王形象存在明顯的差異,體現了鮮明的本土化和民族化特色。
四、造像題材的異同
中國佛教造像受到印度小乘佛教的影響,初期內容多為彌勒佛、交腳彌勒菩薩、釋迦牟尼等單一題材,北魏中期后,結合歷史現狀及中國文化精髓,開始呈現出異質融匯和題材變異的現象,無量壽佛、三世佛、十方佛、千佛、羅漢、力士等題材競相出現,雕刻內容所依憑的佛經越來越多,組合的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在北朝時以三世佛為主題的法華思想及信仰主導了麥積山石窟的實踐,一步步充實了麥積山大乘佛教的思想。到了隋唐時期,巴中石窟造像受到唐代長安、洛陽一帶的影響,以及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的影響,同樣以大乘佛教的思想為題材。從現在麥積山石窟的造像來看,題材主要有釋迦牟尼、三世佛、彌勒、千佛、釋迦多寶二佛對坐、文殊和維摩詰等。巴中石窟常見的題材有釋迦牟尼說法圖、阿彌陀佛、三世佛、七佛、菩提瑞像、觀音、地藏、毗沙門天王、藥師佛等,其次是釋迦與十大弟子、藥師佛與十二藥叉、雙頭瑞佛、說法場面中的天龍八部、各式各樣的道教造像等。
兩處石窟的許多題材都是石窟造像中所共有的,都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影響,除了這些相同的題材,麥積山石窟和巴中石窟還有許多獨特的題材。例如,巴中石窟南龕第83號龕的主尊是一尊雙頭佛像,是全國唯一一例摩崖石刻造像,這是很少見的佛像題材。同樣的題材在我國最西部的7世紀后的新疆克孜爾石窟第58號窟內曾出土過,其是一尊木板彩繪的雙頭瑞佛像,在中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也有這個題材,以及西夏時期的黑水城“輝煌”舍利塔中的黏土彩塑雙頭佛,這些雙頭瑞像都是“雙頭四臂”,主要分布在絲綢之路沿線。巴中石窟南龕第83龕中的坐像與新疆克孜爾和敦煌莫高窟的雙頭瑞像是同一時期的產物,但卻是“雙頭一身兩臂”的形制。
五、存在差異的原因
引起兩地石窟造像產生差異的原因不止一點,其中最主要是地理位置的差異。麥積山位于甘肅天水,是古蜀道與絲綢之路交匯之處,是南來北往、東西交通的樞紐,佛教傳入后,得到了迅速發展,由于地理條件的優越,天水較早出現了見寺禮佛和開窟造像的活動,所以麥積山石窟造像的開鑿遠比巴中石窟要早,并且廣受各個地域文化的影響。巴中位于川北地區,與絲綢之路相距較遠,地理環境并不適合石窟的開鑿,加之潮濕的氣候不利于造像的保存,這也是南方地區鮮有石窟的重要原因。但是入川重要通道米倉道的逐漸興盛使得位于此道必經之處的巴中受兩京地區影響,在隋朝開始了佛教石窟的開鑿工作,這是開鑿時間產生差異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從河西走廊南下,通過甘肅南部的秦州(今天水)至南鄭、巴中的交通也非常發達,這是巴中石窟與麥積山石窟之間存在聯系的重要原因。
二者產生差異的另一個原因是麥積山石窟與巴中石窟的開鑿群體不同。麥積山石窟是在分裂政權時期由地方貴族或在統治者參與下興建的,所以對造像性質的要求沒有那么嚴格,這便造就了麥積山石窟獨有的“東方微笑”。而巴中石窟經歷了由傳統上以皇室為首的統治階級帶頭造像,發展到中小地主或工商業者、地方官員,且較多在城市附近,最后發展到鄉村,并且最底層人都可能參與。這一形式使得巴中石窟擁有極具特色的本土化特征,如“草鞋天王”的出現。
最后,人口的組成結構也是造成差異的重要原因,天水地區古代主要為羌、氐、胡等民族雜居地,也曾被眾多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權管屬,從麥積山石窟早期的供養人造像和題記中可以發現,麥積山石窟的造像得到了多民族人民的供養,這些民族的特征出現在麥積山石窟眾多的造像中。正是天水較多民族的長期雜居,決定了麥積山石窟佛像面貌和服飾呈現出明顯的北方游牧民族特點,而巴中其他民族人口少,決定了巴中石窟造像呈現出明顯的漢人特征。
六、總結
通過麥積山石窟與巴中石窟造像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到遍布中國的石窟之間都存在著聯系,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還深刻了解到我國石窟佛教造像的發展趨勢,以及北方石窟與南方石窟之間的差異和造成差異的原因,希望對相關研究者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雷玉華.巴中石窟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2]巴中市巴州區文物管理所,馬元浩.巴中石窟:唐代彩雕藝術[M].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8.
[3]花平寧,魏文斌.中國石窟藝術:麥積山[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4]冷維娟.中國佛教石窟造像的本土化特征探析[J].雕塑,2015(5):46-47.
[5]雷玉華.米倉道與巴中石窟[J].敦煌研究,2005(1):67-69.
[6]趙奎林.巴中石窟佛帳龕飾藝術探析[J].大眾文藝,2018(18):87-88.
[7]王松寒.從“秀骨清像”到“面短而艷”:南朝對佛教造像藝術中國化的影響[J].中國宗教,2023(2):74-75.
[8]劉曉毅,項一峰.麥積山石窟北方少數民族因素之探析[J].敦煌學輯刊,2018(1):83-92.
[9]魏文斌.麥積山石窟的分期、造像題材與佛教思想[J].中國文化遺產,2016(1):30-42.
(編輯:王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