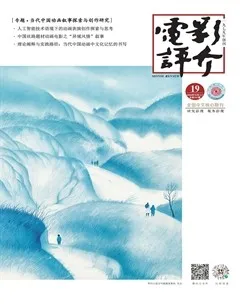理論闡釋與實踐路徑:當代中國動畫中文化記憶的書寫

【摘 要】" 當代中國動畫與中華民族文化記憶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這種契合性不僅體現在故事文本與視覺符號上,更深層次地在敘事情境上承載、傳播民族文化記憶。層級式互文激活、富有東方色彩的敘事修辭以及認同式審美移情是文化意義生成與文化記憶書寫的內在機制。實際上,當代中國動畫以物質記憶為核心內容,激活文化記憶的復蘇;以社會記憶為框架,厚植敘事的情境;以認知記憶為導向,推進觀眾對真理的受容。在后現代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文化記憶的現實化對于培養民族認同感與凝聚民族共同體意識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闡釋了文化記憶理論,并分析其與當代中國動畫之間的契合邏輯,在此基礎上歸納當代中國動畫文化記憶書寫的內在機制,并據此分析中國動畫書寫文化記憶的現實路徑。
【關鍵詞】 中國動畫; 文化記憶; 物質記憶; 社會記憶; 認知記憶
近年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底蘊和美學本質逐漸成為中國動畫生產實踐中關鍵的要素。一方面,全球文化同質化現象促使人們回望自身傳統文化,這不僅是民眾對自身文化遺產的珍視,更是對民族文化認同的自覺體現;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中國動畫注入深刻雋永的哲學意味和美學韻味。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1]因此,當代中國動畫對中華傳統文化元素和民族歷史的探討變得至關重要。
如何定位與落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動畫理論建構中占據的核心地位。目前學界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首先是宏觀視角,主要聚焦中國動畫的中華文化傳承與創新的路徑、策略,如中國動畫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構需要“立足于現代的生活”[2]、邏輯思路包括“以中國文化內容為創作基石,將中國文化與現代動畫技術進行融合創新”[3];其次是跨學科視角,涉及敘事學、社會學、符號學、傳播學、政治學等學科,考察中國動畫中傳統文化的表意方式。然而,隨著現代媒介技術的發展,作為視聽媒介的動畫,它的書寫與闡釋維度實現了拓寬,動畫的虛構技術可以為觀眾提供更加豐富的“過去”體驗。“人類的記憶都在被新生的機器記憶技術定制,記憶工業化已經成為事實。”[4]這也為當代中國動畫傳統文化的生產實踐與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創作與研究視角。近年來,一批講述“民間傳說”“古代神話”“民族歷史”的中國動畫,如《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田曉鵬,2015)、《大魚海棠》(梁旋/張春,2016)、《哪吒之魔童降世》(楊宇,2019)、《白蛇:緣起》(黃家康/趙霽,2019)、《姜子牙》(程騰/李煒,2019)、《新神榜:楊戩》(趙霽,2022)、《長安三萬里》(謝君/偉鄒靖,2023)等,這些作品的獨特景觀構造和深刻文化內涵,繼承與再造歷史記憶與文化心理,在業界受到好評。當前中國動畫如何表達文化記憶?其內在機制和實踐路徑是什么?
一、文化記憶與當代中國動畫的契合性
近代以來,記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體內部機制,涉及心理學、生物學、神經學等自然學科領域。然而,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從社會學角度深入探討記憶的外部維度,并首次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他認為“集體記憶是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之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是社會交往”[5]。集體記憶理論強調記憶內容受到社會框架的制約,社會對記憶選擇、潤飾和塑造影響著社會成員記憶的形成、保存以及情感歸屬。
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德國學者揚·阿斯曼(Jan Assmann)進一步提出了文化記憶理論。他從更宏觀的社會文化角度,深入剖析了集體記憶的形成、傳遞和演變。阿斯曼描述文化記憶為“包含某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所特有的、可以反復使用的文本系統、意象系統、儀式系統,其‘教化’作用服務于穩定和傳達那個社會的自我形象”[6]。這說明,文化記憶不僅是一個集體特定時期所特有的知識系統,而且還在重復實踐中傳承了文化的精髓。
在對文化記憶的研究過程中,學者們不同程度地強調了媒介的核心功能和價值。正如阿斯特利特·埃爾(Astrid Erll)明確指出:“若無媒介在個體和集體記憶這兩個層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記憶則不可能存在,記憶的方式影響著過去事物的形狀和意義的變化。”[7]文化記憶以客觀外化物為媒介,如文本、圖像、儀式、地點等載體。這些媒介物象征著集體共享的關于過去的知識,在機構化的交流(實踐、觀察)中得到延續,從而鞏固群體的文化歸屬感和認同感。
隨著技術的變革,承載文化記憶的媒介,從早期的壁畫、碑刻、文字、儀式等古老媒介物,延伸到如動態影像、新媒體等現代數字化的媒介。其中,影像的文化記憶價值和功能越發凸顯。“影像敘事具有強大的話語生產力,許多民族文化記憶往往以形象符號通過藝術表達、審美敘事、影像闡釋等方式進行呈現。”[8]從這一視角出發,動畫作為一種標志性的影像藝術,毫無疑問已成為傳遞文化記憶的關鍵媒介,它承擔著喚醒文化記憶的獨特功能。當前,旨在繼承和創新民族文化的中國動畫,不但在價值取向上與文化記憶高度契合,而且其在文化記憶理論框架下的生產實踐還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打開了新的視野。
當代中國動畫不僅是一種藝術表現,更是文化記憶的核心載體。從文化角度審視,歷史與神話構成了文化記憶中至關重要的“文本系統”,它們承載了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民族記憶與文化,捕捉并保存了民族智慧與經驗積累。這些歷史和神話文本,在時間沉淀中,展現了其深厚而豐富的內涵,是人們可深入探索的精神瑰寶。自中國動畫誕生之時起,其創作便深受傳統神話與歷史的啟發。當代中國動畫繼續承載這一使命,它借鑒傳統神話和歷史故事來構筑自身敘事,使得當代動畫不僅延續了傳統,更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精髓的重要媒介。例如,動畫《大魚海棠》靈感來源于《莊子·逍遙游》中的神話,這一經典的“逍遙游”哲學通過影片得以再次詮釋,成為傳達中華民族生活智慧和人生觀的有力載體。
從表現形式角度審視,當下大眾媒介技術使動畫、電影等影像媒介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直接橋梁。正如艾莉森·蘭茲伯格(Alison Landsberg)所描述的“假肢記憶”,“像電影這樣書寫不同的媒體讓人們到達另一個人的記憶體驗中”[9]。當代動畫運用人物、畫面、音響等要素,塑造感染力強的視聽情境,使觀眾在這個虛擬的時空中重新體驗和解碼記憶。并且,不同于實拍影像的“機械復制”,動畫擁有獨特的靈活性與變革能力,“可以拒絕形式上的束縛,安排上的固定。擺脫僵化的思維,追求永恒的運動與形變,具備展現任何形態的能力”[10]。這種特質賦予中國動畫孕育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民族知識相互關聯的視覺符號的能力。簡言之,當代中國動畫通過對記憶情境的構筑與民族符號的孕育,實現對文化記憶相關的“意向系統”的表達。在儀式化的觀影中讓觀眾的身體感覺和情感認同達到關于民族歷史的深度“記憶”體驗。
二、當代中國動畫文化記憶書寫的內在機制
當代中國動畫對歷史與神話文本的精妙演繹、記憶情境的精心營造與民族符號的創新孕育,已日益成為文化記憶的關鍵載體。然而,當代中國動畫所表達的文化記憶想要被群體“富有感情”接納,更需要依賴一套有效的內在機制來展現動畫文本、視覺符號、敘事語言所包含的記憶元素。這一機制成為連接民族文化與群體認同的價值紐帶,具體表現為層級式互文激活、東方式敘事修辭和認同式審美移情。其中,層級式互文激活是文化記憶書寫的外在表現,認同式審美移情是文化記憶書寫的內在動力。在“內生外化”機制中傳達中華文化的知識體系和視覺經驗,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層級式互文激活
互文是文本與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義、主體以及社會歷史之間的相互聯系與轉化之關系和過程。[11]在文化記憶術中,互文是基本的原則。通過互文,中華文化中那些鞏固身份認同的知識重新被激活并再次進入循環與再生產。在當代中國動畫中,激活民族文化記憶的互文機制體現在敘事文本、藝術語言及社會文化三個層面。
一是動畫敘事文本的互文性。當代中國動畫并非對神話或歷史的機械重復,互文性強調在不同文本之間尋求相似性與異質性的平衡,神話或歷史文本的一部分在新的敘事語境中被賦予了新的意義。盡管原文本經歷了變化,但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觀者接觸到改編后的新文本時,仍會將其與文化原型產生聯想和比照;二是藝術語言的互文。在動畫的藝術媒介中納入其他藝術語言,當下中國動畫較為常見的藝術語言互文是將水墨、工筆、壁畫等民族傳統藝術語言融通和化用。民族傳統藝術語言在當下動畫中的巧妙運用能夠實現動畫的審美突圍,拓寬藝術的表現領域,還能夠使民族記憶的觸點不斷被激活,民族文化得以延續;三是社會文化的互文。民族特有的價值觀念、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知識內容,以文化符號的形態走入動畫虛構的世界。在當代中國動畫中這些社會文化知識的再現,保證了鞏固認同的知識的傳達和繼承,由此實現了文化意義上的認同再生產,也增加了群體的凝聚性。
(二)東方式敘事修辭
“文化記憶以文字、圖像、舞蹈等進行的傳統的、象征性的編碼及展演。”[12]這里的編碼是文化信息系統的、形象的、邏輯的符號化過程,而這些編碼符號在展演中傳遞深層意義。換言之,當代中國動畫是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上的一種“編碼”藝術。其在文本中的敘事修辭,實際上是對這些文化編碼符號潛在信息的展演。為了完整展現其文化內涵,中國動畫自然采用東方色彩的視覺修辭。
文化符號的隱性敘述。中國藝術常常表現為一種謙和內斂的特質,敘事上傾向于含蓄與雋永的表達。這種敘事風格通常借助民族文化符號的意指間接表達深層的情感和思想。當代中國動畫的文化符號敘述延續了中國藝術的這一特征。如《白蛇:緣起》中白蛇修煉場所的桃花意象。桃花在中國文化中是愛情的象征,而在這則隱晦地指向主人公的情感糾葛。當代中國動畫民族文化符號的隱性表達,引導觀眾在熟悉與震驚間解鎖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
視覺奇觀的意境呈現。蘇軾曾說:“作藝如意造華嚴,造一片高嚴境界。”[13]長久以來對意境的追求都是中國藝術的核心美學理念。當代中國動畫嘗試將寫意造境融入動畫敘事修辭中,在影像奇觀表達時復現了這一藝術風格。如《新神榜:楊戩》中展現的仙界蓬萊、瀛洲、方壺三大仙島以及在云間穿梭的古代飛船等視覺奇觀,這些視覺奇觀在動畫影像所營造的東方色彩的意境氛圍中被呈現。藝術修辭的同一性突破了視覺奇觀帶來的陌生感,拉近觀眾與奇觀的距離。
在中國美學思想中,意境營造也是重要的情感表達形式之一。宗白華曾指出:“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貢獻的一方面——研尋其意境的特構,以窺探中國心靈的幽情壯彩。”[14]當代中國動畫歷來重視用意境來表情達意,如《白蛇:緣起》中小白與阿宣在云霧繚繞的湖面上同舟共濟、結伴撐著油紙傘在漫天飛舞的蒲公英中御風而行的畫面,導演以景寄情暗示主人公之間愛情的升溫。這里借助意境間接實現情感的表達,當代中國動畫成功地傳承了傳統藝術中那種不言自明的情感溝通方式,使得其所承載的文化記憶以跨越時空的方式得以釋放。
(三)認同式審美移情
在研究移情的過程中,美學家朱光潛認為審美主體的主動性是推動移情的引擎,主張心理印象帶來的美學意味。[15]審美移情是記憶內部的機制,同時也是回憶的穩定劑。當代中國動畫是積淀社會內容的意味,還具有獨特的形式美,藝術的光暈觸發觀眾的審美認同情感。這種審美移情與情感共鳴,結合記憶元素,強化了動畫的文化記憶功能,“影像的移情功能可以讓觀眾跟隨主人公一起回憶往事或分享‘想象力中的幻想’”[16]。
一方面,生動的視覺形象與深刻的意味美是移情機制中文化記憶構建的著力點。“思維雖然很抽象,但回憶的過程卻很具體。”[17]當代中國動畫通過具體的人物形象、空間風貌、話語言說方式、社會內容、生活模式、思想觀念等作為喚醒文化記憶的獨特符碼,被內嵌到生成故事之中。這些先驗性視聽符碼激發觀眾移情的產生,觀眾在視覺沉浸中自然地圍繞感知對象展開聯想,激活存儲在當代中國動畫中的民族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審美移情的內模仿活動能夠在情感共鳴中加深對感知信息認知與記憶。當代中國動畫中的畫面、音響、情節設定、敘事方式等要素營造了情景化的感知體驗。觀眾在審美體驗中調動自我的內模仿心理機制,把自我投射到動畫情境中,實現情感、認知與身體的完全共鳴。這種情感共鳴使得個人記憶變得更容易被集體所接受,并使觀眾的感受與情感完美地融入動畫所塑造的文化記憶環境中,從而達到主體與客體完美合一的境界。總之,當代中國動畫側重審美移情,突出動畫藝術的形式美、意味美的體悟,這是情感聯結進而鞏固文化認同的重要內在機制。
三、當代中國動畫文化記憶書寫的現實路徑
根據人類學和符號學的研究框架,文化可以被視為三維的結構,由物質、社會和認知三個維度構成。如阿斯特里特·埃爾(Astrid Erll)所言:“文化記憶可以說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涵蓋了物質記憶、社會記憶和認知記憶。在現實當中,這三個維度共同參與文化記憶的制作。”[18]當代中國動畫借助細膩的藝術演繹,生動地將文化遺產、民俗及傳統藝術等展現給觀眾,從而在物質層面激活文化記憶。此外,動畫中的人物行為、互動和交流賦予了豐富的社會情境,反映社會記憶的脈絡。當代中國動畫核心在于以精心構筑的敘事結構和情節深度來傳達特定的主題,引發觀眾對傳統哲學思想和民族價值觀的深思。依循當代中國動畫文化記憶書寫的內在機制,探尋基于物質、社會與認知三個維度下的文化記憶實踐途徑。在這“多元統一”的框架內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深刻地嵌入群體的集體意識中,促成一種更為持久和深入人心的文化記憶。
(一)以物質記憶為內容,激活文化記憶的復蘇
當代中國動畫中的物質具有承載、傳達與構筑記憶的作用。在文化記憶理論中,“物質擁有時間索引,這個時間索引和當下一起指向過去的各個層面”[19]。物質背后所承載的意義,遠超其直觀的形態,它既包含人們的個體和集體回憶,也融合了先祖的智慧以及民族歷史的底蘊。當代中國動畫對傳統神話和歷史的創新闡釋,其敘事背景通常架構在歷史的某個階段,融入各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質元素,從自然景觀、日常物品,到具有民族特色的村落場景,再到融合了傳統文化的虛構元素。這些物質在動畫中呈現,一般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文化記憶的傳達:一是“原創性重現”,當代中國動畫將物質還原至原初的意向,以重現民族符碼;二是“現代化再解讀”,將歷史和傳統物質元素進行現代化的再闡釋,經過融合、拼貼呈現現代審美意味的物質符號,同時又不失其傳統特色。這兩者共同構成文化記憶的豐富圖景,傳承文化意義。正如學者龍迪勇所指出:“各種表達空間的方式都包含著一切符號和含義、代碼和知識,它們使得這些物質實踐能被談論和理解。”[20]
民族符碼的視覺重現。數字動畫技術結合現代動畫語言對物質的原初形象進行細致還原。盡管這些形象脫離了它們原初出現并得以保存的時空,但精準、豐富地呈現物質的形態、質感、紋理等特征,指向了物質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確保了文化的連續性。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山河社稷圖的景觀深受中國傳統盆景藝術的影響。哪吒的標志性武器裝備,“火尖槍”和“風火輪”在動畫中被真實地還原,火尖槍的金屬光澤、銳利的尖端,以及風火輪的細致紋理和飽滿色彩,都生動地展示了這些文化符號的歷史和文化層次。
傳統物質元素的現代化再闡釋。動畫藝術家在遵照原初物質元素的意向、當下社會審美風格以及動畫敘事需求的基礎上,利用變形、融合等動畫造型技巧以及光影、構圖、鏡頭變化等動畫表現手法,打造了兼具現代風格和象征意味的文化符號,這不僅維系了民族文化和審美價值的連續性,也展現了現代感。例如《新神榜:楊戩》中婉羅所跳飛天舞,在融合敦煌壁畫風格的同時,利用現代三維數字動畫技術為其賦予新的生命;《白蛇:緣起》中的寶青坊,該場景基于傳統中藥鋪的設計,但又巧妙地融入了現代科幻風格,展現了一種后現代工業的美學風格。
當代中國動畫的民族符碼重現與傳統物質元素的現代化再闡釋,不僅加深了文化的記憶輪廓,同時也實現了文化一致性與遞進性的延續。“影像作品敘事過程中某些器物的反復出現,往往能夠得到視覺上的強調,不僅可以產生超越物質形式層面的文化表意功能,并能在敘事層面產生結構性意義。”[21]對經典韻味的物質再現,當代中國動畫將其固有的規范和定型的價值延續,在動畫實踐中傳遞深層的文化信息,從而確立了文化的一致性。同時,將這些元素與現代文化有機結合,實現了文化遞進性的表現。
(二)以社會記憶為框架,厚植敘事的情境
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在《社會如何記憶》提出“在人類社會中,記憶不僅屬于人的個體官能,而且還存在叫作社會記憶的現象。”[22]這種記憶源于社會成員對過往事件的共同回憶和共享,是在社會互動和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當代中國動畫的社會記憶存在于角色群體的日常生活、交流與互動等多層面的社會實踐之中。這是記憶內容的重要來源,也是動畫影像特有的話語表達方式。在動畫劇集《中國奇譚》之《小妖怪的夏天》(於水,2023)中,回家的小豬妖與母親的對話和關心備至的叮囑,如“不要太拼”“好好干”等話語,觸動了觀眾與父母溫馨時光的深刻回憶。
在文化記憶的構建中,社會記憶提供了一個關鍵的框架。文化記憶生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現存的社會秩序制約,這些秩序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集體的相互關系。這種“社會框架”不僅限定了被納入文化記憶的內容,同時也為敘事提供了背景情境。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也認為,社會可以記住是處于參考框架內的東西,被忘卻的就恰好是不在參考框架之中。[23]以神話“哪吒”為例,經典故事中的哪吒在鬧海沖突后,被其父親李靖強迫自盡,其中的削骨還父、削肉還母情節體現了封建社會的宗法禮制。但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李靖寧愿自我犧牲也不希望哪吒遭受天劫。盡管他在日常里管教嚴格,但他背后的無私付出與當今社會中默默奉獻的父母形象相吻合。此外,李靖慈父的形象為哪吒從一個叛逆少年向一個拯救眾生的英雄的轉變奠定了情節基礎。
社會記憶的傳遞依賴身體。保羅·康納頓將其描述為“身體實踐”,也被稱為“體化實踐”。[24]當代中國動畫通常將視角聚焦于普通的小人物,通過小人物的身體實踐,來體現和傳遞深藏在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中的社會集體記憶。福柯也強調,日常生活是鏈接過去與現在、形成記憶的重要領域。“日常生活是記憶、行為和身體的集散地,涵括著歷史和記憶的點點滴滴,從生活習俗、方言到口音、動作,體現著歷史的拓殖和記憶的延展。”[25]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叛逆、貪玩、缺少父母陪伴的哪吒,仿佛映照當下很多年輕一代對童年的集體記憶。再如,《小妖怪的夏天》中的小豬妖,盡管它勤勞而毫無怨言,但常被忽視和誤解,其遭遇恰似部分觀眾職場的一個縮影。
(三)以認知記憶為導向,推進真理的受容
觀眾對影像的認知是基于其外部的視聽感知與內部的記憶經驗之間的緊密交互而形成的。當影像刺激觀眾的感知系統時,會引發身體反應,使觀眾身體回溯并描繪出某種形狀或輪廓。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記憶會傾向于接受與“記憶-形象”相似的知覺。正如克里斯蒂安·麥茨(Christian Metz)所描述的電影狀態:“在觀眾的視網膜上放映、聽覺器官中接受和大腦中分析的電影狀態。”[26]當觀眾的記憶通過其感知來展現“記憶-形象”時,動畫中的感知與記憶交融,引發深層的認知反應。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指出,“記憶的實際功能,因而也是通常的功能,就是當前行為對過去經驗的利用,簡言之,就是認知。”[27]動畫影像與觀眾記憶相互交織時,其中喚醒的是群體共有的、具有延續性的認知,正是“認知記憶”現象。
在這個豐富多元的文化背景下,當代中國動畫在營造富有創意的視聽體驗中,深入挖掘和解析植根于集體潛意識的認知記憶,特別是對中華傳統哲學思想的多維注解。中國的文化歷史悠久并且吸納了多元的哲學觀點,逐漸形成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同時兼容道家、禪宗等多種哲學觀念的綜合體系。當代中國動畫將這些傳統哲學思想巧妙地納入敘事結構,讓觀眾在享受視聽樂趣的同時,也能體驗到濃郁的文化韻味。如《大魚海棠》中描述的鯤與魚群在浩渺大海中的嬉戲場景、椿于五光十色的星河中的孤獨身影,這些畫面都在構圖、鏡頭、視角等方面精心設計,展現了天、地、人三者和諧統一的觀念,而其故事也向觀眾傳達了人與神之間都應遵循自然法則生存的理念,從多個維度呈現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再如,《姜子牙》中,姜子牙決心拯救眾生,即便面對無盡的挑戰與困境,他依然堅定自己的初心和信仰,生動地展現了“身心合一”及“修身克己”的哲學觀念。
然而,從對真理的探求角度而言,認知記憶并不總是全面或絕對的,正如真理本身帶有內在的不確定性。當代中國動畫中,角色們在敘事情境中歷經一系列矛盾和沖突,當矛盾化解后,角色們實現了自我成長,也催生了觀眾與自我認知記憶間的深刻對話。這一過程既重新闡釋了真理,也有組織地引導觀眾對真理的再認知。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在遭遇挫折后勇敢地高呼“我命由我不由天”,這一觀念和精神特質也被傳達給觀眾。這與中國傳統哲學中強調的“順應天命”的命運觀,特別是儒家的“樂天知命”觀念,存在明顯差異。然而,“我命在我不在天”這一觀點,起初出自道家典籍《龜甲文》,在道教修煉“成仙得道”語境下,才能理解命的最初意義,這與哪吒表達的內涵并不相同。事實上,哪吒所表達命運觀和抗爭精神,它強調堅毅與進取的精神特質,這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因此,當代動畫電影引導觀眾與傳統哲學思想對話時,必須緊扣時代脈搏,結構與現代社會和文化進步一致的觀念,從而確保所傳達的價值觀符合時代需求。
結語
當代社會的快速發展與多元化趨勢為文化身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隨著時間和空間的持續變遷,個體與集體的身份認同變得愈發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代中國動畫顯得尤為特殊,它不僅是娛樂的載體,更深層的它還成為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的橋梁。動畫影像的編碼為觀眾傳遞了豐富的文化知識體系,既呈現了民族風格的自然景觀、歷史遺跡和物質文化,又反映了文化的規范、世界觀和人生觀。這種雙重呈現不僅有助于傳遞并維系記憶與知識系統,更在無形中加強了觀眾的文化身份認同。
需要指出的是,動畫電影并不僅僅是過去文化的簡單再現,它在后現代背景下與外來文化、新文化發生互動,形成一種“對立-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既強調本民族文化的特質,又不拘泥于傳統,反映了現代社會中文化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總的來說,當代中國動畫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在弘揚民族文化、強化文化認同、促進文化交流與融合上均有其獨特的價值。在未來,隨著科技和藝術的進一步融合,中國動畫將為文化身份的表達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和推動。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 J ].求是,2023(17):4-11.
[2]于苗,高慶占.國產動畫電影中傳統文化的“基模”化重構[ J ].電影新作,2019(03):38-41.
[3]彭國斌,熊艷,王竹君.傳承與開拓:當代動畫電影的時代嬗變[ J ].電影文學,2023(07):87-91.
[4][法]貝爾納·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M].趙和平,印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277.
[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0.
[6][德]簡·奧斯曼.集體記憶與文化身份[C]//.陶東風,周憲,譯.文化研究(第11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7.
[7]Erll A.Re-writing as Re-visioning:Modes of Representing the\"Indian Mutiny\"in British Novels,1857 to 2000[ J ].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06:163.
[8]劉慧梅,姚源源.書寫、場域與認同:我國近二十年文化記憶研究綜述[ J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04):185-203.
[9]Landsberg A.Prosthetic Memo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Remembrance in the Age of Mass Cultur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120.
[10]Jay Leyda.Eisenstein on Disney[M].Calcutta:Seagull Books,1986:21.
[11]李玉平.互文性:文學理論研究的新視野[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5.
[12][17][19][23][德]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51,30,11,16.
[13]朱良志.中國美學15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271.
[14]林同華.宗白華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56.
[15]王玨.試論數字動畫應用創造的美學新空間[ J ].當代動畫,2019(03):20-25.
[16]李恒基,楊遠嬰.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19.
[18][德]阿斯特里特·埃爾.文化記憶研究指南[M].李恭忠,李霞,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4-5.
[20]龍迪勇.空間問題的凸顯與空間敘事學的興起[ J ].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06):64-71.
[21]陳曉云,李之怡.影像創作的器物迷戀與文化研究的物質轉向[ J ].現代傳播,2022(09):97-103.
[22]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
[24][英]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3.
[25]安捷.福柯如何看電影[ J ].文藝研究,2018(08):88-98.
[26][法]克里斯蒂安·麥茨.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與電影[M].王志敏,趙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10.
[27][法]亨利·伯格森.物質與記憶[M].姚晶晶,譯.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74.
【作者簡介】" "鄭其寶,男,江蘇南京人,南京藝術學院傳媒學院博士生,南京傳媒學院動畫與數字藝術學院
副教授,主要從事動畫藝術理論與實踐研究;
葉佑天,男,湖北孝感人,湖北美術學院影視動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詩意動畫
實踐與影視美學理論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1年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專題項目“課程思政與動畫教學創新研究”
(編號:2021SJB1249)、2022年江蘇高校“青藍工程”優秀教學團隊“動畫專業教學團隊”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