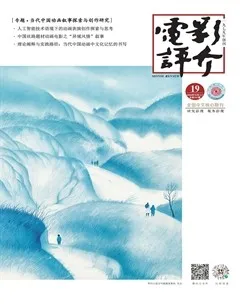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音樂的多維創新表達

【摘 要】 電影音樂作為現代電影創作中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對于增強電影的情感深度和藝術表現力起著重要的作用。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在類型機制、敘事風格及審美表現等多個維度上呈現出創新發展景觀,而音樂在其中亦起著頗為重要的造型、表意、主題塑造等功能作用。在文本敘述上,它以深刻的社會觀照意識和時代精神激發觀眾情感共鳴,兼收并蓄各種文化元素,創造出獨特的聽覺體驗;在制作流程上,它實現了創作效率和藝術表現力的雙重提升;在傳播路徑上,它以數字化、新媒體等網絡傳播途徑實現了審美功能的效益延伸。
【關鍵詞】 新時代; 國產現實主義電影; 電影音樂; 創新表達; 嵌合構型
“現實主義手法是現實題材電影的核心。”[1]審慎觀察不難發現,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以一種更深刻、細膩且富有洞察力的方式展現了時代的脈搏律動與社會的多樣面貌;它們在主題表達上呈現出更廣泛和多元的態勢,涵蓋從個體命運到群體關懷、從社會問題到人文精神等諸多方面,并以濃烈的藝術感染力與思想穿透力影響著受眾的審美趣味及價值取向。在某種意義上,“現實主義仍是當下主流電影創作中的主要手法,也標志著中國現實題材電影依然占據電影市場的主導地位”[2]。其中,音樂作為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與影像文本合力共構時代樣貌時亦展現出蓬勃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風格層面,呈現出中西并舉、古今共存、豐富多元的審美態勢;在文本層面,以詞為媒,自然延伸影像空間、構建主體間性關系;在制作和傳播層面,借助現代制作技術和數智平臺實現自身藝術品質、審美魅力的升華及傳播范圍、傳播速度的擴大或提高。無疑,分析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的音樂多維運用與藝術表現,考究其歷史發展脈絡及其創新性表達的現代景觀,對國產電影音樂的未來實踐乃至于提升國產電影的藝術品質有所裨益。
一、現實主義電影的音樂與影像嵌合構型的語義脈絡
(一)音樂與影像本體的嵌合構型
電影音樂作為電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具有獨特的魅力與價值。理解電影音樂的內涵,一般有兩個維度。一是電影音樂乃音樂的一類,既有音樂本身的結構、形式和特性,又表現出一種與電影這一現代視聽媒介異形共構而別具一格的藝術特征。米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提出冷熱媒介的概念,二者差異在于接受者在解碼過程中的感官參與和認知難易程度:越不需要大腦認知參與的媒介越熱,反之對客體認知參與度較高的媒介則越冷。[3]相較于電影中富有畫面感的影像,作為聽覺媒介的音樂則要求更高的客體參與度:音樂具有多釋性,對其的理解與想象取決于客體的先在經驗;通過聽覺的在場,客體進入音樂構建想象空間,進而實現自我的情感投射和交互體驗。在此意義上,音樂和狹義上的語言類似,都是攜帶意義的感知形式,依賴接受者的主觀解讀和個體經驗的參與。二是電影音樂也是基于影像本體的音樂;其并非獨立于電影之外而存在,而是黏附于電影的語境與敘事,承載著獨特的意義表達和情感渲染功能。換言之,電影音樂應影像而生,合影像之拍,述影像之旨。它借由與影像的自然融合,延伸影像的敘事空間,喚起審美客體的主體意識和具身體驗,引發客體的情感共鳴和身份認同,繼而實現電影藝術價值的躍遷。
與一般音樂相比,電影音樂不僅是單純的旋律與節奏的組合,更是為了契合影片的特定情境與情感表達而創作,具有“明確目的與指向性”[4];其運用不可避免地受到電影整體風格及敘事情境的制約。在欣賞方式和審美理解上,電影音樂也非如一般音樂那般僅訴諸單一的聽覺體驗(僅從編曲、節奏、調性等方面即可對其展開鑒賞評判),亦要結合影像本身的某種規定性:過于重視音樂技巧的歌曲,可能會喧賓奪主,有損影片的藝術效果;相反,在單獨欣賞時顯得簡單甚至支離破碎的歌曲,在與影像結合時卻能凸顯影片意蘊,實現音樂對影像的賦能。可以說,電影音樂唯有在與影像的結合中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效用;也只有在特定的影像文本中,才能對電影音樂的好壞做出恰當公允的判斷。
據出現時間、自身特色及藝術功能等,電影音樂可分為主題歌、插曲、背景音樂等類型;而主題歌又可細分為片頭曲、片中曲、片尾曲(通常情況下,片尾曲較常見,而片頭曲、片中曲較少見;作為主題歌的片尾曲多起到凝練思想、深化主題的作用)等。比之電影音樂的其他形式,主題歌擁有更加完整和獨立的藝術品格,能承載深層情感意蘊并清晰傳達電影的題旨意涵;它“往往是對影視劇內容的一種高度概括,它可以以特定的風格和凝練的情感表現來充實劇中主要人物形象,可以展現特定的歷史氣氛,可以表現生活中的某種情懷等”[5]。電影中的插曲、背景音樂等多用來增強影像的情緒氛圍與修辭色彩,傳達在視覺敘事中未能直接展現或難以完全表達的情感及描摹電影角色的內心活動和心理狀態,進而激發觀眾想象,為影像構筑豐富的闡釋空間。不僅如此,在具體的敘事段落中,插曲、背景音樂還可承擔一定的敘事功能,既能預示情節發展,還能借音樂的連續性串聯分散的故事情節,構建跨越不同時空的敘事橋梁,增強電影敘事的連貫性,為觀眾提供超越視覺感受的敘事體驗。
在整體意義上,電影音樂與影像本體、情節敘事和主題意旨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它們交匯融合、相輔相成,共同構成電影藝術的有機整體。在本質層面上,嵌合于影像本體的電影音樂以其獨特的語言形式參與本文的話語建構,并渲染其情緒與氛圍,繼而使影像的感知延伸,進一步拓展電影藝術在人物塑造、情感傳遞、主題闡釋等方面的想象疆域。
(二)現實主義電影中音樂與影像有機結合的歷史語境
實際上,以多樣形式和風格存在于電影文本的電影音樂,無論是激揚壯闊還是細膩婉轉,都在為電影注入某種情感沖擊力或情緒感染力。藝術是時代氣質的表征,每一時代的藝術都會映射出那個一時代的精神風貌和文化特征。注目國產現實主義電影的發展歷程,電影音樂在創作語境、藝術特征等方面,也體現出貼合時代特色的表征及其與影像密切結合的趨向,也經歷了不同的歷史躍遷與審美嬗變。
國產現實主義電影最早可回溯至20世紀30年代,在全民族抗戰的時代背景下,《漁光曲》(蔡楚生,1934)、《風云兒女》(許幸之,1935)、《馬路天使》(袁牧之,1937)等現實主義電影及其音樂在精神氣質和文化取向上均折射出強烈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懷;《漁光曲》(電影《漁光曲》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電影《風云兒女》主題歌)、《四季歌》(電影《馬路天使》主題歌)等電影音樂以激昂澎湃的旋律和振奮人心的歌詞,激勵了無數中華兒女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義勇軍進行曲》后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至今仍發揮著凝聚人心與激發愛國情懷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電影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原則,《上甘嶺》(沙蒙/林杉,1953)、《紅色娘子軍》(謝晉,1960)、《小兵張嘎》(崔嵬/歐陽紅櫻,1963)等現實主義電影,以鮮明的民族風格、追求崇高的英雄書寫、單一的政治本位視角等塑造了國產現實主義電影的主流范式;片中音樂也呈現出鮮明的民族風格與強烈的時代氣息——在與影像世界緊密結合的前提下,以激揚的旋律和動人的樂章烘托、強化影片所表達的革命精神與愛國情感。《我的祖國》(電影《上甘嶺》插曲)、《紅色娘子軍連歌》(電影《紅色娘子軍》主題歌)、《參加八路軍》(電影《小兵張嘎》主題歌)等電影音樂將民族音樂元素與時代音樂取向相結合,體現出民族風格與時代特色有機交融的美學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受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尤其是巴贊的“段落鏡頭理論”與“真實美學”對第五代、第六代導演的影響),這一時期的現實主義電影既確立了民族性主體地位,也高揚了不無先鋒精神的現代性;片中音樂在繼承、發揚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創新,并開始以頗具現代意識的表達方式與審美風格助力影像敘事表意。《紅高粱》(張藝謀,1987)巧用民俗音樂元素(嗩吶聲、腰鼓聲等)串聯影片,主題歌《酒神曲》與插曲《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等不僅凸顯濃郁的陜北民俗韻味,也以高亢、快節奏的旋律與貼近俗世情懷的歌詞彰顯現代感。《霸王別姬》(陳凱歌,1993)選用戲曲音樂(融合了京劇、昆曲、豫劇等多種戲曲元素)作為影片的背景音樂,并將西方器樂融入其中——中式二胡與西式大提琴等的和諧并置使電影音樂頗有特色。
二、新時代現實主義電影音樂的多維運用及審美旨趣
電影是時代之鏡,通過藝術化手法映照、反射時代風貌與俗世精神。現實主義電影以其對社會現實的敏銳捕捉、對人性的深度挖掘及對生活本質的真實再現而頗具魅力;細膩的敘事、真實的人物刻畫等也讓觀眾感受到現實世界的冷暖色差和紛繁復雜。其間根植現實生活土壤的電影音樂運用也往往超越單純的背景氛圍烘托,而以真實、質樸的方式訴說蕓蕓眾生及其復雜情感,讓受眾更易沉浸于影像敘事,真切觸摸現實社會肌理并引發深度思考。隨著科技、經濟、思想、文化等諸方面的發展進步,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也不斷吸納、運用新的創作技法,在表現形式、敘事手法、藝術風格等方面推陳出新。與之相應,片中的電影音樂也在風格形式的融合性、文本語義的共鳴性、制作流程的數字化和傳播方式的網絡化等方面大膽探索、實驗,并在與影像的有機融合中表現出多維度的創新性突破。
(一)超越影像:音樂風格的融合性
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文中認為:意識形態借助各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宗教、教育、法律、工會、大眾傳播媒介等散漫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個體”詢喚為臣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主體”。[6]電影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用影像結構為一種想象性關系,從而使觀眾為其文本縫隙中的意識形態所詢喚。換言之,電影亦是“一種注定要獲得明確的意識形態效果的機器”[7]。也因如此,早期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的音樂多采用民族敘事、革命敘事形式,風格上也頗受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影響(廣泛吸納民族音樂的旋律、節奏和器樂等元素),功能上也指向政治理念與社會價值觀的傳揚:旋律常處于較高的音域范圍,節奏常采用2/4拍的進行曲風格,調式偏好使用明快而寬廣的大調音階,演唱多為男高音或女高音的獨唱(抑或雄壯的合唱),響度常保持在較強程度,整體上營造出一種剛勁猛烈、激昂澎湃的音樂氛圍和風格特征。[8]
實際上,電影音樂的雙重屬性——它既是投射于電影本體的音樂,需要服務于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電影的敘事,同時又是一種音樂類別,具備音樂自身所固有的結構特性(具有調性調式、節奏節拍、音域音區等要素)——使其在參與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影像建構的過程中呈現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創新態勢: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時代語境下,民族音樂與電子音樂的結合,民族樂器與西洋樂器的交融,古典音樂與流行音樂的并舉,建構了自身的主流表達及古典美學、民族特色、流行元素、現代電子音樂多元并存的融合態勢。
《我不是藥神》(文牧野,2018)的主題歌《只要平凡》融入異域民族音樂元素,呈現出較濃厚的俄羅斯民歌風格:旋律悠長婉轉,曲調自然優美,蘊含朦朧悠遠的哀傷和對生命的深刻體悟;伴奏樂器由吉他、提琴和風琴等組成,弦樂音色寬廣、深沉且充滿抒情性,給影像營造出溫柔、纏綿的情感氛圍,讓受眾深感音樂語言的內在韌性,繼而喚起其對生命的敬畏感;節奏上采用6/8拍,而三拍子的慢律動模式也讓受眾領略了一種優雅而流暢的聽覺感受,并引導其進入一種輕松的意識性體驗狀態,繼而在音樂搭建的想象空間中重構自我主體性。《懸崖之上》(張藝謀,2021)的同名主題歌將俄羅斯風情小調與現代音樂元素巧妙融合,既有歷史厚重感又不失現代氣息:以吉他分解和弦為骨架,鍵盤鋪底,弦樂緩緩流動,給人營建出深沉而悲傷的氛圍;片中其他配樂也借不同的音樂元素來體現影像的緊張氛圍與人物的內心情感,使音樂與畫面、情節形成較為完美的呼應:大量貼合諜戰氛圍的不無懸疑、緊張感的現代音樂元素給人帶來某種身臨其境的壓迫感、緊張感,而一些傳統器樂的加入又使自身具有本土韻味——豐富的視聽體驗深化了影片的主題思想,凸顯了對無名英雄的禮贊,對民族信仰、愛國情感的歌頌。《三大隊》(戴墨,2023)的配樂以弦樂為主,多采用弦樂重奏或重奏與電子樂相結合的形式,烘托敘事節奏、情感張力并使之協調統一:在程兵(張譯飾)追兇苦久想要放棄之際,管弦樂的配樂以干澀刺耳的顫音傳達出主人公的絕望感、無力感;片尾程兵說出“三大隊任務完成”后,背景音樂以后搖元素與管弦樂相結合,配以明亮的風笛聲和強烈的鼓點,給人營造出悲壯的襯托人物形象的英雄主義氛圍,而隨著程兵走出巷子,音樂中配器漸少,最后只剩下柔和明亮的小號聲,化繁為簡的旋律在“勝利”的情感氛圍中流溢出溫暖、抒情的一面——這種“勝利”后的釋然情緒增強了影像的敘事表現力,觀眾的情緒感染力也隨小號聲慢慢擴散開來。
(二)曲調之下:歌詞文本的共鳴性
有論者指出:“在藝術中,感性是至高目標”[9];達成感性則意味著觸及理性難以企及的層面,即人的內在情感層面。一如英國民族音樂學家約翰·布萊金(John Blacking)所說:音樂是一種“被組織成社會可接受模式的聲音”[10];作為寬泛意義上的語言,音樂所獨有的情感和語義傳遞能力可使人的心靈產生天然的接受感。其實,電影音樂的調性、調式、旋律、節奏、響度等基本元素潛藏了豐富的情感內涵和表達指向;它們共同作用并引導進入影像所創造的情感世界,繼而產生情感想象和共鳴,尤其是當歌詞以明確的詞義、隱喻性修辭等展示出創作者的主觀情感態度時,這種情感引導和想象激發作用則更加明顯:直接表述的文字與寓意性的語言相結合,無形間將接受者“詢喚至生存現實與社會關系之間的想象疆域中”[11],使受眾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情感投射和意識體驗。當然,這一內化過程也使受眾與音樂文本之間建立起深層的情感交互性和共鳴性。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的音樂,常以微言大義的敘事方式和樸素的個體生命視角,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關切,同時在歌詞中通過人稱代詞的使用,使自身與受眾建立起感知認同關系;頗具人文性的歌曲主題和巧妙的人稱敘述策略,詢喚出受眾的主體性意識,并使之自然而然地在審美欣賞中產生自我投射,在知覺體驗中產生情感共鳴,進而強化電影的藝術感染力。
誠然,電影音樂具有一定的藝術獨立性,但它與影像主題的密切聯系也使其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藝術形式;它常以情節內容為情感介質,借具象的影像世界來發散抽象意涵,進而增強影片的藝術表現力和審美感染力。歌詞文本作為電影音樂與觀眾之間的橋梁訴諸情感的直接表達;對一般觀眾而言,歌詞以直觀的文字表達提供了一種易于理解、感受的方式,使人能輕松跨越專業門檻,觸及歌曲的情感內核。《風云兒女》《紅色娘子軍》等早期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的音樂歌詞多較為質樸、直白,簡單但富有真情實感的語句直指現實,直抒胸臆。然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的音樂歌詞則更多地承載了深刻的寓意,多圍繞生命的意義、人性的復雜、道德的邊界、社會的正義等富有哲思性的問題展開;這些問題又因扣合新時代語境下人們共同關切的議題而能較易觸動受眾,并在與之發生深度情感交融之際重塑其主體性意識。《第二十條》(張藝謀,2024)片尾曲《你也》描寫了坎坷世事、悲喜人間的社會面貌,喚起觀眾對冷暖社會、人生意義的思索;《三大隊》主題歌《人間道》展現出人物對責任和信仰的執著追求,引發人們對人性、生命和存在意義的叩問;《八角籠中》(王寶強,2023)主題歌《生如野草》描繪了普通百姓在面對困境時的堅持和不屈不撓,體現出生命的韌性和不懼困難的精神,也引起受眾對社會現實的冷峻反思。概言之,歌詞因頗具人文性的主題使歌曲超越了單純的音樂伴奏而成為一種能夠激發受眾深層思考的藝術媒介:“受眾在聆聽電影音樂的過程中,以主體性自我的情感共鳴、身份認同與另一個主體產生間性關系,并且在互動交流中為電影音樂語言結構中蘊藏的時代意識形態所形塑。”[12]
在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的音樂歌詞文本里,創作者常采用人稱代詞的敘述策略,以內聚焦視角(電影敘事除內聚焦視角外,還有外聚焦視角)書寫“人物-觀眾”的情感體驗,從而強化歌曲的情感表達。“電影賦予敘事以有趣的、新的視點操作之可能性,因為它們不是僅僅擁有一條而是同時擁有兩條信息通道——視覺的與聽覺的(而且在聽覺方面,不僅有人聲,還有音樂和噪音)。”[13]一般情況下,創作者多借助不同的鏡頭調度來實現內聚焦敘事:或“通過演員置于畫面中的位置,增強我們與他的聯系”[14],抑或運用簡單的匹配剪輯方式假定觀眾的感知視點,從而使觀眾與鏡頭本身建立起一種“感知共鳴”[15]。在具體音樂表達中,歌曲與受眾“感知共鳴”的建立多依靠第一人稱“我”的運用;這使歌曲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和自我表述特質(仿佛創作者在直接袒露內心感受與情感經歷),容易讓接受者自覺進入歌詞構建的想象世界,并油然而生對客體的共鳴與共情:“我要走穿這條命去看雪蘭花/我要踏破這雙鞋光腳平風沙/我要白日見云霞夜里舉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事事有王法/我要出了門的人再晚也歸家/我要天上落的雨又回到天上/我要吃這一口飯守這一野荒/我要這人間所有道都在青天下”(歌曲《人間道》),便通過第一人稱和排比修辭的運用,直接而強烈地展現出主人公對公義信念的堅守和對不公命運的抗爭,給受眾傳遞出強烈的認同感和反向自身的主體意識;“我沒有蕩起的雙槳/野草靠風吹的方向……黎明沒得黑暗也沒得用/四季跟我扛過肩上的重”(歌曲《生如野草》),亦貼合平凡大眾的身份特質,讓受眾自動帶入“我”的視角,對影像世界與人物形象進行情感投射和想象拓展。同樣,第二人稱“你”的直接呼喚能創造出主體間對話式的互動間性關系,繼而拉近歌曲與受眾間的距離:“我知道你也會懂/你也會痛/命運會傷人……我知道你不躲藏/你不退讓”(歌曲《你也》),通過“你”的指代,使受眾自然沉浸于歌詞的敘述空間,并與之進行一場心靈對話;第三人稱“他/她”則提供一種客觀或全知的視角,為歌曲增添更多的敘事性和普適性:“他們說大城市/比家鄉要精彩/闖出去就沒失敗/只是暴雨襲來/在人生路徘徊/他還看不清未來”(《奇跡·笨小孩》宣傳主題曲《還是笨小孩》),通過第三人稱“他”很容易使受眾找到自己生活中的影子,從而對歌詞文本乃至影像世界產生強烈的身份認同與情感共振。
(三)技術賦能:制作流程的數字化
毋庸置疑,技術創新是推動電影音樂發展的重要力量。隨著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電影音樂的制作和錄音技術也在不斷更新換代。傳統的電影音樂創作經過多年的實踐和探索,已經形成一套相對成熟、完善的工業化流程,但為數智時代的數字技術浪潮所裹挾,這一流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
作為綜合性的多人密切協作過程,傳統的電影音樂創作流程涉及作曲家(詞作家)、導演、制片人、音樂家、錄音師、剪輯師等多個方面;它通常始于作曲家(詞作家)與導演、制片人等方面的溝通(旨在充分理解電影的主題、風格等),之后作曲家(詞作家)會觀看電影樣片(深入把握影片情感走向和視覺節奏),構思能體現電影核心精神的主題旋律和歌詞文本,并進行相應的旋律創作和配器編曲。在創作初步完成后,作曲家(詞作家)制作小樣并進行試聽,之后根據導演和制片人的反饋意見進行修改,然后進行正式錄制;錄制完成后,進入混音和制作環節,并最終將音樂與電影畫面進行調試混錄。
在當下,傳統的費時費力的電影音樂制作方式正逐漸被新的數字音樂制作方式所取代。數字技術的出現為電影音樂的制作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工具,使作曲家(詞作家)能夠更加自由地發揮創意,創作出更具個性、特色的音樂作品。MIDI(音樂器數字接口)技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曲和配器的成本,使得音樂創作變得更加高效、經濟;采樣技術通過高質量的音頻采樣實現了對傳統樂器聲音的精確模擬,為制作者提供了更為豐富的聲音選擇;音色合成技術打破傳統的音色限制并讓全新的音色制作成為可能,從而拓展了電影音樂的表現力和創意空間;AR、VR等技術的應用為電影音樂的呈現方式帶來新的可能性,受眾因之能領略到更為沉浸式的觀影體驗。能夠說,在數智音樂制作技術的加持下,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音樂創作的效率和效果已實現了雙重提升。當然,在音樂創作取得創新性突破的同時,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也需警惕音樂過度商業化和娛樂化的傾向。作為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音樂應始終堅持以藝術性和思想性為核心,避免因過于追求商業利益和表面效果而忽略了其內在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內涵。
(四)媒介脈動:傳播方式的網絡化
在數智時代,數字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改變了電影音樂的創作流程,也擴大了其傳播時間、范圍和速度,影響了其產業和文化生態。以往電影音樂的傳播多受限于傳統的放映機制,即只有在電影院里,受眾才能首次接觸到電影的原聲音樂,而隨后電影音樂被制成音像制品,才可能在市場流通;而這意味著電影音樂的傳播脫離不了碟片、磁帶等物質載體,從而限制了電影音樂的覆蓋范圍和產業效益,制約了其傳播時效和傳播速度。
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數智平臺的廣泛普及,電影音樂的傳播格局被創新性重塑。而今,電影音樂的首次亮相不再限定在電影上映之時;作為一種高效的配套商業宣傳工具,電影制作方常將片中部分音樂提前于網絡發布,利用微博等社交媒體、bilibili彈幕視頻網站、QQ音樂和網易云音樂等平臺進行創意推廣,從而盡可能地讓更廣泛的受眾得以接觸,并以此強化電影宣傳效果。《你也》作為《第二十條》的主題曲,在電影公映前五天便通過媒體平臺發布;這有效提升了電影在網絡上的曝光度和討論度。顯而易見,數字音樂格式也使音樂作品的復制和傳播變得更加便捷,受眾可以輕松地在各種設備上收聽和分享自己喜歡的電影音樂作品;這種跨媒介的互動性既增加了電影音樂的可見度,還增強了電影的傳播效果。實際上,為數字技術加持的全媒體時代也催生了新的電影音樂消費模式:受眾可以通過在線訂閱、數字下載等方式獲取電影音樂不再需要購買實體音像制品,這種消費模式不僅降低了受眾獲取電影音樂的門檻,也為電影音樂的傳播提供了更大的靈活性。
總而言之,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了新時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音樂的傳播和普及;它們不再受限于傳統的物質載體,而是借助數智平臺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即時傳播。無疑,這種不無創新意識的變革既促進了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音樂的商業價值和文化影響力,也為受眾提供了更豐富、更便捷的互動音樂體驗。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數智平臺的升級迭代,國產現實主義電影中音樂的影響力也將不斷擴大,進而成為全球化時代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結語
電影音樂作為現代電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與電影視覺語言一起承擔著敘述、造型、表意等的功能;它不僅豐富了電影的情感表達,還與影像融為一體形塑電影獨特的審美意境。在新時代現實主義電影文本中,音樂的創新性表達既強化了電影音樂對影像畫面的輔助性功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電影音樂自身的藝術表現范疇。創作者通過對音樂風格的多元探索、歌詞文本的共鳴性挖掘、制作流程的數字化革新及傳播方式的網絡化拓展,已使電影音樂成為影像世界連接受眾內心世界的重要紐帶;在實現音樂本體藝術價值提升的同時,亦為電影產業注入新的活力。《懸崖之上》《你也》《人間道》《生如野草》等較為成功的電影音樂制作,啟示國產現實主義電影創作務必立足影片本身,深入挖掘配樂內涵和主題,持續探索新的配樂風格與元素,使電影音樂能夠與不斷變化的社會文化精神和大眾審美需求相適應。與此同時,片中音樂還應在歌詞文本中折射出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觀照,對人類普適性議題的思考,對時代潮流的積極回應。只有這樣,音樂才能更好地為國產現實主義電影敘事服務,從而實現觸動受眾心靈,激發受眾主體性,與受眾產生共鳴、共情的審美效果。當然,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觀眾審美的多樣化,國產現實主義電影的音樂創新性表達也會面臨更多的機遇和挑戰。毋庸諱言,唯有立足影像本體、革新音樂符號表征和引領受眾接受三方面有機結合,國產現實主義電影音樂的創新性突破與發展才可持續,也才可能為受眾帶來更加豐富、深刻的審美體驗,并在整體意義上促進電影及電影音樂的全面繁榮。
參考文獻:
[1][2]周星,李昕婕.2023年度中國現實題材電影藝術報告[ J ].電影評介,2024(07):1-9.
[3][加拿大]米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8.
[4]劉暢.影視·人文·音樂[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4:26.
[5]曾田力.影視劇音樂藝術[M].北京:北京廣播電視學院出版社,2003:12.
[6][法]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M]//李訊,譯.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下編,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681-740.
[7][法]讓-路易·博德里.基本電影機器的意識形態效[M]//李訊,譯.李恒基,楊遠嬰主編.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下編,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64.
[8]劉曉飛.中國主旋律電影歌曲風格演變及發展探析[ J ].當代電影,2023(08):162-167.
[9]余秋雨.藝術創造論(序)[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2.
[10]王濼泉.新時期中國電影音樂文化研究[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19:2.
[11][12]陶婧,馬紹惠.審美認知、主體意識與“破圈”效應——新時代現象級主旋律電影中的音樂流變與藝術作用[ J ].四川戲劇,2022(10):138-142.
[13][14][15][美]西摩·查特曼.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M].徐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3:145,145,146.
【作者簡介】" "彭弋的,男,四川南充人,成都大學音樂與舞蹈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影視音樂、電子音樂
研究;
峻 冰,男,安徽蒙城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比較電影學研究所所長,四川省電影
家協會副主席,泰國理工大學、泰國皇家理工大學曼谷分校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影視理論與批評、比較電影學、影視傳播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