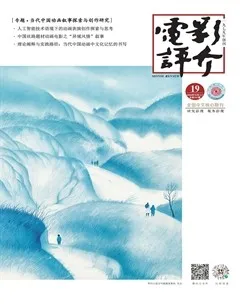人工智能時代的電影革命:人機交互、技術賦權與主體遷移
【摘 要】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對電影產業全鏈條的顛覆性重構,不僅體現在AI使內容生產范式從“線性預設”模式轉向基于流動性與生成性的“交互生產”模式,以及“人機協同共創”所帶來的人機關系變革,它更是直接推動了文化形態的迭代以及影像生產權力結構的變遷。通過新媒介的技術賦權,大眾從被動接受的觀看者轉變為“產銷合一”的“生產性觀眾”,決定文化產品審美意義和價值的“主體”亦從藝術家遷移至“生產性觀眾”,UGC成為未來影視創作的重要方式,加速著“創意民主化”與“影像生產泛平民化”時代的到來。本文透過對內容生產、人機關系、受眾角色轉型及藝術主體遷移等幾個面向的分析,試圖探討人工智能的技術交互如何在文化層面深刻影響電影創作與審美接受的交互實踐。
【關鍵詞】 人工智能; 人機交互; 技術賦權; 主體遷移
當前,在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創新的賦能下,影視生產的外延和邊界正不斷拓展。“人工智能+電影”革新電影生產模式,新質生產力成為電影產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驅動性力量之一,推動著科學與人文、技術與藝術、虛擬與現實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術迭代不僅使傳統的電影創意機制、生產邏輯發生了結構性改變,還帶來“人機關系”的變革及受眾角色與功能的轉型,并推動了影像生產權力結構與社會關系的變遷。
一、算法技術邏輯下的“人機關系”變革與人機交互實踐
(一)算法技術邏輯下“智能主體”的崛起
人工智能時代,以算法為代表的新興科技介入電影創意、制作與宣發全流程,促發傳統電影工業容納電影算法工業的新生態[1],這使當下電影生產思維發生了顛覆性變革,人的邏輯被弱化,不再居于中心位置,算法的邏輯加強。[2]AIGC以非人類要素的方式加入創意內容的生產環節,從技術工具轉變為可以和人類協同工作的“智能主體”,被賦予和人類對話、參與創作的平等地位。這帶來一種顛覆人本主義原創觀念的“后人類視角”,意味著非人類要素與人類要素在內容生產中開始占據平等地位。[3]
機器智能在內容生產中的能動作用不斷凸顯,AIGC在滿足人可操作性前提的基礎上,表現出某些等同或超越人類生產方面的進步性,形成類人般的“創造力”,成為新興的“智能主體”,釋放出巨大的創意價值。AIGC的底層基礎設施也確實在迭代出這樣的生產邏輯。大數據收集的全面性弱化了人類認識世界過程中來自主觀的目的性,保證對于世界認識的完整性與客觀性,注重數據的相關性而非因果性,實質也就降低了事件預測及相關決策的決定論色彩,這種遵循相關被量化的數字的演進方向,很可能獲得更為真實的對于世界的預測。[4]
面對算法超越性的數據收集分析和內容產出能力,人類創作的主體性面臨巨大的挑戰。然而,算法展露的智能性則進一步推動人機之間的交互對接,為開拓藝術創作的想象力、創造力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5]隨著ChatGPT、Midjourney、Sora等大語言模型的應用,人類社會進入一個“人工智能生成藝術”時代。在內容審美方面,“人工智能藝術”已然成為一種存在形態,AIGC創作的內容已經實現了普遍化的審美接受,人工智能或將創造新的審美范式。然而,從本質上說,人工智能仍然不能超越人類,因為人工智能的藝術生產不是“創造”,而是“生成”,它是根據自身算法對數據庫的學習,“生成”具有某種創新性的作品。[6]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將人的“直覺能力”理性化,推動了“機器理性”的發展。而機器理性則是以人類心靈為基礎的“馴化”,直覺與機器理性仍統一于人的心靈。[7]
(二)技術媒介化視角下的人機關系重構
人類藝術生產創意機制的演化,經歷了“手工創作——機械復制——數字創意——智能創意”的發展歷程。進入AIGC時代,不斷迭代的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動影視創作進入“智能創意”階段,“人-機協同”新生產模式正在成為影視業的主流生產模式。在物質生產和實踐層面,人機之間的交互關系已經由過去不具超越性的主仆關系轉變為逐漸融合、互相宰制、人機趨向一體的“賽博格”[8]。
從媒介融合視角看,從一種媒介到另一種媒介的過渡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種媒介消亡,另一種媒介取而代之,相反,它涉及一個越來越廣泛的不同媒介的復雜融合。由于AIGC具有“多模態生產”的跨媒介特性,能在基于數據、算力、算法賦能內容生產的基礎上,將原來以文本為核心的單模態創意生產升級到多模態形態。因此,多模態融合更徹底更輕易地消除了媒介間的壁壘,將藝術的跨媒介實踐從傳播和消費端前置到創意和生產部分。這一過程通過數據融合的途徑,實現了所有文化范疇和文化概念之間的跨碼。[9]生成式人工智能通過將文字、圖片、圖像等多模態媒介進行“再媒介化”的方式重組再造,以此創造出新的藝術內容。因此,從此種生成邏輯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一種融合多種媒介形態與功能的“超媒介”,它的迭代創新將現代技術發展推至一個新的高峰。
從媒介技術演進角度看,新媒介的出現及其運作是人類與技術總體性共同進化的一部分。隨著人類對新技術的開發,人類不斷地被驅使去接受和修正技術,從而與技術一起進化為更復雜的存在形式。[10]如果說“數字技術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個人與布滿技術界面的當代文化復雜環境之間的互動方式”[11],那么,人工智能技術則又將這種變革往前推動了一大步。生成式人工智能則是技術與人類共同進化進程中一個里程碑式的創造。智能媒介正拓展介入人類主體的重塑[12],創造出“人-機共生”的新型主體。這種準全息化的媒介有著與人類感官的同構性[13],而智能傳播時代媒介技術所呈現出的具身性特點,使其成為“人體的延伸”[14]。人工智能與人類協同進行藝術生產的合作模式,則進一步擴大與重塑了人類的感覺中樞。
從媒介演進史看,過去幾個世紀的媒介演變整體呈現出一種規律,即從以人類為中心的基于語言的交流形式轉向以機器為中心的基于代碼的交流形式[15],技術的持續迭代推動了傳播媒介從物質性媒介轉向“界面”。從文字到廣播、電影、電視,再到手機、互聯網、社交媒體,每一種新的媒介都在不同程度上迭代了人類的信息傳播與知識生產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則將這種迭代又向前推動了一步,它通過個體與智能媒介的實時交互,真正實現了知識的“個體化生產”。ChatGPT實現的個體化生成式應用——個體作為生產者與人工智能媒介展開的直接協同——極大地激發了個體化社會交往。[16]在個體與社會連接方面,生成性、全息化、全能型新型智能媒介的普及,釋放了個體的潛能,使普通個體作為分布式獨立節點,能夠跨越現代性以來專業分工的社會系統,直接接入社會網絡。[17]因此,就此種層面而言,“人-機協同”的新生產模式不僅顛覆了傳統的創意機制與內容生產的范式,更是涉及個人與社會連接方式的顛覆性變革。它創造出一種全新的普遍性的社會交往模式,使機器超越了工具層面躍遷至與人類平等的生產與交互主體,進而引發人類文明的變遷。
二、技術與人的互動:交互敘事與生產權力變遷
進入數智時代,“視覺文化”正以數字形式大規模生成,技術將呈現出更多復雜的面向。數字化革命的一個主要結果是,把先鋒美學策略納入計算機軟件的指令和交互界面隱喻中。[18]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標志著媒介技術新的突破,它不僅帶來內容生產層面的重構與人機關系的變革,更是直接推動了文化形態的迭代。人工智能技術正在催生出一種全新的視覺藝術形式。這種基于人機交互界面(human-computer interface)構建起的虛擬藝術語言,正在催生出“人機一體”的新技術美學——“后人類美學”。進入電影敘事的虛構世界的窗口已經成為進入數據場景(datascape)的窗口[19],曾經作為電影的東西如今成為人與計算機世界的界面。
伴隨分析式與生成式AI的規模性普及,新的數字內容生產規則和敘事邏輯發生了改變,衍生出另一條敘事路徑。人工智能電影敘事邏輯跳脫出預設的“線性敘事”,轉向基于“界面”與“生成”的“交互敘事”,敘事主體也由創作者轉向算法和觀眾,從原有的內容體驗局限逐漸走向開放包容的姿態。例如,最初作用于影視宣發而創造的“平行實境游戲”,即是一種驅動觀眾探索影視內容的敘事手段,“它常以橫跨不同大洲及多個線上媒介的游戲空間、長達幾月甚至幾年的游戲時間,囊括不同語言、專業的大規模玩家團隊共同協作完成多個游戲任務而成為全新跨媒體敘事體驗和影視業病毒式營銷計劃中的重要一環”[20]。在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電影A.I上映前,The Beast作為一款平行實境游戲率先在互聯網上發行,觀眾化身玩家,通過在電影海報、預告片、電子郵件中搜集到的細微信息,可提前進入電影敘事線索的挖掘之中,進行互動。
從本質上講,人工智能時代的電影敘事形態將更多地體現為人與技術之間的互動,受眾的參與性、人機交互性顯著提升。生成式AI基于其可供性重新配置數字內容的生產規則,由算力、算法驅動的深度學習作為一種支配性的敘事機制,構造出系統化的技術界面。這也是一套影像敘事的過程性的內容界面[21],它將敘事要素(影像資源)以數據的形式存儲于“庫”,并按標準分類(包括對簡單敘事段落的可能性歸因),組織起相應的內容讀取與對話界面,通過“交互”實現用戶指令對敘事的確認及修改。如徐冰導演的可交互AI實驗電影《人工智能無限電影》,用戶可通過某一平臺進入電影創作界面,根據界面設置選項(戰爭、愛情、科幻犯罪或前衛)進行選擇,通過輸入關鍵詞或句子指令,即可由AIGC生成類型化的電影片段,還可以對某一故事的情節與敘事轉向進行設計與修改,通過輸入關鍵詞來改變電影中的角色和情節走向。當情節發展不盡如人意時,用戶可重新輸入指令,訓練算法學習養成,實時調整內容。這一視覺藝術形態創新的背后實則存在一種隱喻,導演隱至看不見的“黑箱”,創作主導權已由導演轉移至“算法工程師”和觀眾,由程序對內容實現規制與處理。顯然,人工智能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的作用已提升,并由外而內對敘事結構產生根本性影響,由此,相應地構造出數字內容敘事的基礎邏輯。
當下,人工智能正以一種獨特的技術表達機制變革內容生產范式,數字內容的生成方式正發生著從“結果”向“過程”的轉變,從影視原創團隊制作向“影視從業者+粉絲生產+算法實現”的新型生產模式的轉變。AIGC技術打破了電影藝術領域長期以來由技術精英對影像生產的專業壟斷,將創作權力賦權給大眾,推動著影像生產權力的下沉。這種生產權力的下沉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影視觀眾從“想象力消費”的觀眾轉變為“想象力生產”的用戶。無論在技術呈現方式還是內容補充方面,AIGC都促使用戶在一定的許可范圍內實現創意生產,這實則打通了導演與觀眾之間的關系壁壘,優化了資源配置;另一方面,在想象力延伸的同時,影視內容也更加訴諸情感與現實,變得更加“接地氣”。生產性觀眾創造的內容往往源自個體經驗、群體規范以及時代隱喻,這也說明,相比導演中心制的原創團隊,用戶參與生產的方式,整體上往往更符合大眾喜好與市場需求。
總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迭代與應用,正在改變電影工業傳統的權力結構與社會關系,AIGC的“交互敘事”模式超越了傳統文化工業設定的敘事空間,以更大的自由度、信任度、價值度賦權給觀眾,使觀眾得以直接參與到內容生產中,影像生產權力正發生著“從內容生產機構向大眾”的遷移,加速著“創意民主化”與“影像生產泛平民化”時代的到來。
三、技術賦權與主體遷移:“生產性觀眾”的主體化
(一)受眾的角色轉型:從被動接受者到主動生產者
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從根本上改變了電影生產者與受眾之間的關系,大眾媒介時代內容生產機構中心論被消解。大眾媒介時代內容生產機構中心論將影視內容視為專業機構的社會生產,大眾的身份就是專業機構的用戶。[22]然而,步入數智時代,智媒技術賦權推動著受眾的角色與功能發生轉型。在AI這種新型個體化媒介的技術賦權下,大眾已經從被動觀看者轉變為文化內容的主動生產者,成為視頻生產及媒介內容創作的新興主體。
賴納·溫特(Rainer Winter)在《生產性觀眾:媒體接受作為文化與審美過程》一書中,提出過“生產性觀眾”這一概念。賴納·溫特認為,電視商品生產出來后被出售給電視臺,進入傳播領域,由此,電視商品轉變為“生產者”,這個“生產者”生產了新的商品,即觀眾,并把觀眾這個“商品”出售給廣告人。在接收過程中,媒體文本離開了財政經濟領域,進入文化經濟領域。但是,在文化經濟中,觀眾拒絕接受自己作為“商品”的角色,而是成為“生產者”——他們制造意義和愉悅,他們不再是“觀眾”,而是成為“觀看電視”這一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具體化所在[23]。
“生產性觀眾”這一概念伴隨著經濟系統的驅使,以及文化工業理論的崩塌、后現代文化理論的延展而出現。生產性觀眾會在各自的生活背景中解讀媒體文本的符號維度,利用文本的多義性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生產出意義。[24]他們在創造性地接受媒體文本的過程中,可以發掘自身文化與審美上的潛力,利用媒介賦權,為媒體文本的消費打上獨特的個性化印記——“個體并非被動吸收符號形式,而是積極創造它的意義,因此意義生產即接收的過程”。可見,每一個文化產品的消費者都可能從認知和情感上成為文化生產的一部分。此外,不僅消費者的個性與能力會影響接收過程,不同的規則、符碼和習俗也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媒體接受的過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被媒體產品同化的過程,而是一個積極和富有創造性的解讀和評價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媒體文本的意義被建構出來,它所提供的愉悅得以形成。[25]
隨著智能媒介系統成為影視制作的基礎設施,智能媒體技術釋放出驚人的潛力,創造出人與世界之間新的互動方式。智能媒介迭代的關注點在于人與外部世界連接方式的變革,涉及人、機、物等多個層面的新型交互狀態。[26]通過個體與智能媒介的實時交互,智能技術實現了人-機在影視藝術創作領域的協同生成。[27]人工智能電影的交互敘事模式能使觀眾得以繞過專業機構的中心化組織,直接參與影視劇情設計與內容創作中,從而實現與內容產品的個體化、生成性的應用與交互。由此可見,智媒技術的賦權使觀眾不再被動地接受文化內容,而是成為內容的主動創造者與交互生產者,由過去被動的信息接受者轉變為“產銷合一”的新型內容生產者——“生產性觀眾”[28]。
(二)主體遷移:“生產性觀眾”的主體建構
“生產性觀眾”概念的提出,更加突出“媒體接受”作為一個文化與審美的過程,凸顯受眾在文化審美過程中的主體性與能動性。AI介入影像生產,促使被動觀看的觀者轉變為產銷合一者的“生產性觀眾”。隨著人工智能的技術賦權與“生產性觀眾”的崛起,傳統藝術創作體系中的“主體”亦被顛覆,決定文化產品審美意義和價值的“主體”從藝術家遷移至“生產性觀眾”。在AI以媒介的形式輔助觀眾根據自身需求參與生產與改造文化內容的過程中,觀眾不再是大眾媒介時代那個被動接受的“客體”,而是成為具有創造性和意義生產性的“主體”,發揮著重要的文化建構功能。以《人工智能無限電影》為代表的一批AI電影的涌現,亦指明了未來影視創作發展的幾個趨勢:
一是由用戶選擇影響劇情走向的作品與更加注重受眾互動性、參與性的作品,將俘獲更多用戶群體,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將成為未來影視創作的重要方式。
在《黑鏡:潘達斯奈基》中,用戶通過運用鼠標、遙控器、觸屏的方式即可實現劇情設置,劇情設計因個人選擇的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每位用戶所經歷的故事情節、結局也因人而異。雖然這類互動劇在腳本選項上的設置還較為簡易,然而,借助AI腳本生成工具,用戶可以充分發揮想象力,進一步拓展文本敘事的可能性,完善作品的核心價值輸出。在影游融合電影《頭號玩家》游戲與電影的嵌套式敘事中,導演借助彩蛋、二維碼、鏈接等互動元素積極調動觀眾能動性,鼓勵觀眾參與到作品內容的深度挖掘中[29],這就好比在當前影像的后臺開啟了數個瀏覽“窗口”,而每一個“窗口”又將鏈接出新的未待發覺的內容[30],激發了觀眾的好奇心。
在未來的電影敘事設計中,通過觸摸“按鈕”“按鍵”“手柄”等物質性元素或內嵌于屏幕內真實有效的“二維碼”“鏈接”等虛擬元素與觀眾展開互動的作品,將會越來越多。相比傳統的視聽模式,這些以“界面”為互動媒介的作品更加注重觀眾的參與性,賦予觀眾類似于“玩游戲”的體驗,使觀眾能以具身參與的方式投入其中,更加真切地體驗劇情的起承轉合。
二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正在成為賦能影視與游戲的新質生產力,并為影游融合進一步創造條件。
從內容生產角度看,電影制作已經全面轉向數字化,比如場景大量由人工智能協助完成,角色的表演越來越依賴電腦后期……對于完全采用數字化生產的游戲而言,大量采用數字化生產的電影元素也提升了游戲轉換的效率。新技術的創新迭代,為“電影”與“游戲”二者在產品融合上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性,“游戲電影化”與“電影游戲化”(借鑒游戲的互動電影)將成為未來影視創作的發展趨勢。[31]
總之,在技術、從業者和用戶共同參與的維度下,“意義”的生成變得不再確定、不可把控。AI技術在將影像創作權力下放給用戶的過程中,也將敘事文本的定義權與詮釋權賦權給用戶,使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審美與消費需求,進行意義的再生產。由此,在用戶與技術交互的過程中,敘事文本的意義與價值不再由專業權威人士所定性,而是轉變為由用戶所定性。然而,由于受到人工智能自動化、自組織、自生成的技術特征的限定,生成式虛擬影像生產在最大限度地調動大眾參與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電影工業作為大眾媒介的組織功能。
結語
綜上所述,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對電影產業全鏈條的顛覆性重構,不僅體現在AI使內容生產范式從“線性預設”模式轉向基于流動性與生成性的“交互生產”模式,以及“人機協同共創”所帶來的人機關系變革。作為技術與文化雜合體(hybrid)[32]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更是直接推動了文化形態的迭代以及影像生產權力結構的變遷。人工智能所掀起的電影智能革命所帶給人們的重要啟示莫過于,技術不僅僅是一種工具,還是人造物與使用者的一個共生體。[33]而運用AI變革電影制作的一個開拓性革新在于,智能技術模糊了“虛擬”與“現實”的界限,并帶來強烈的群體互動性。未來,或將涌現出更多由人機交互創作出來的電影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將更多地呈現出多層雜糅、虛實共生的特征,這種新技術美學特征所呈現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將進一步超越人類想象和認知的邊界。然而,面對技術所創造出的烏托邦的想象與“人機共生”的未來社會圖景,個體也將面臨如何在虛實共生的世界中重新確立“存在”的意義這一新的哲學命題。
參考文獻:
[1]劉俊,賈奕星.人工智能時代電影算法工業的邏輯表征與批判反思[ J ].電影評介,2024(08):1-7.
[2]張立娜,陳旭光.“算法作者”的創作思維與美學原則——算法時代電影工業美學之倫理轉向[ J ].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03):65-75.
[3]孫蕾蕾.從本土到全球:紀錄片講好中國故事的話語轉變與敘事升級[ J ].當代電視,2023(06):10-15.
[4]閆奎銘.大數據時代的人機關系[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2016:11.
[5]張柏林.機遇或危機?算法時代ChatGPT對人機關系的重構研究[ J ].新聞研究導刊,2024(05):1-4.
[6][7]周豐.人工智能藝術的神經美學研究[ J ].東岳論叢,2023(10):67-72.
[8]虞鑫,李一諾.當ChatGPT“闖入”勞動場景:人機互動、空間爭奪與價值重塑[ 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02):126-132.
[9]趙宜.人機共創、數據融合與多模態模型:生成式AI的電影藝術與文化工業批判[ J ].當代電影,2023(08):15-21.
[10][11][15][美]羅杰·F.庫克.后電電影覺:運動影像媒介與觀眾的共同進化[M].韓曉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149,28,147.
[12][13][16][17][22][26][27]孫瑋.“視頻化社會”的來臨——從ChatGPT展望媒介通用性變革[ J ].探索與爭鳴,
2023(12):55-62,193.
[14]張珈瑜.“賽博”語境下“人機關系”的轉型變革與影響思考[ J ].秦智,2022(01):84-86.
[18][19][俄]列夫·馬諾維奇.新媒體的語言[M].車琳,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21:29,203.
[20]徐立虹.“無限游戲”的哲學隱喻:交替現實游戲(ARGs)研究[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0(05):17-22.
[21]何天平.從文本構造到界面連接: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數字新聞敘事的重塑[ J ].新聞界,2023(06):13-21,61.
[23][24][25][28][奧]賴納·溫特.生產性觀眾:媒體接受作為文化與審美過程[M].徐蕾,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2022:155,298,156-157,293.
[29]]彭新宇,張玉雪.技術游移、敘事想象與游戲轉向——影游融合賦能元宇宙發展之路徑研究[ J ].東南傳播,
2023(09):112-116.
[30]王虎,彭新宇.用戶賦能、協同生產與跨屏升維——5G時代影游融合產業新景觀[ J ].文化產業研究,2022(01):
142-153.
[31]大眾新聞.唐季禮聯手多牛:AIGC開創影游融合時代[EB/OL].(2023-12-20)[2024-10-11].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IMDO8QBN00259I71.html.
[32]張毓強,姬德強.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與我國國際傳播的新生態[ J ].對外傳播,2024(03):68-72.
[33]易顯飛.技術現象學、經驗轉向與技術文化——伊德的技術哲學評析[ J ].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06):82-85.
【作者簡介】" "孫蕾蕾,女,山東濟南人,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社教節目中心主任編輯、導演,中國民族學學會
影視人類學分會理事,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導師,河北省城市傳播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影視藝術、
紀錄片、國際傳播研究;
彭新宇,男,山東濟南人,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智能媒體傳播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電視媒體虛擬現實媒介敘事手段建設與創新研究”
(編號:22BXW076)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