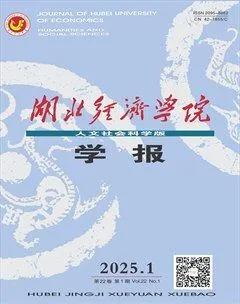“國潮快閃”在海外:跨文化語境下中國Z世代的微觀敘事與游戲化傳播
摘 要:“國潮快閃”作為青年亞文化、傳統藝術和民族與國家意識的共構,是近年來中國Z世代人群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創造認同空間的重要范式。本文以“國潮快閃”中Z世代參與跨文化傳播的微觀敘事為邏輯起點,歸納出其三重微觀敘事策略:形式上,打造空間聚合環境,立足本土化傳播語境;內容上,創造個體具身實踐,形構跨文化意義共同體;媒介上,利用數字交互媒介,驅動記憶個性化傳播,并引入斯蒂芬森的傳播游戲理論,進一步探索Z世代如何在傳播游戲觀的驅動下,通過海外“國潮快閃”驅散宏觀文化差異、開放中外文化邊界,實現跨文化語境下的中華文化賦魅。
關鍵詞:國潮快閃;跨文化傳播;微觀敘事;游戲理論
隨著全球化進程日趨深入,異質文化間的邊界漸趨模糊,文化間的交流、互鑒與融合持續進行,為全球語境下中華文化的跨文化傳播提供了許多契機。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1]。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在于區域國別間的宏大敘事、傳頌大國史詩,也在于從時空、情感、互動等多方位貼近受眾日常生活的微觀講述。微觀敘事追求通過對傳播活動的場景化、具象化、生活化,有助于消解文化接觸者對外來文化的排斥感,創造個體與“他文化”的情感聯結,進而將自身演繹為文化接納者的身份角色。
Z世代(Gen Z),通常指出生在1995—2009年間的人。“快閃”作為一種短暫性行為藝術,于2000年起源于美國紐約,并迅速成為西方社會流行的公共藝術形式,2011年傳入中國。我國Z世代在青少年階段受西方流行文化的影響,利用“快閃”形式創造性演繹中國民風民俗、傳統文化等元素,形成“國潮快閃”這一獨特的藝術傳播現象。近年來,展示民樂、民族舞蹈及中華傳統服飾的“國潮快閃”作為我國青年亞文化、傳統藝術和民族與國家意識的共同呈現,成為留學生等海外華人青年跨文化傳播、展示中華文化魅力的新范式。
一、傳播游戲觀視域下的“國潮快閃”
傳播的游戲觀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威廉·斯蒂芬森提出,他將傳播闡釋為一種體現受眾高度自主性和主觀性的“游戲”。其研究著眼點是站在受眾立場上的自我參與式主觀體驗,關注游戲中主體的自由、投入與愉悅,指出“傳播游戲并不強調規則,而強調人們在傳播中的主觀經驗,即傳播快樂”[2]。“快閃”活動的發起者比爾曾表示,“整個意念由嬉戲開始,有的是純為搞笑,有的被視為社會或政治活動。”學者認為,“游戲”的屬性可以概括為“自愿性”、“樂趣性”、“非功利性”、“特定時空性”與“規則制約性”,前三者側重游戲的主體性,后兩者側重游戲的結構性[3]。“國潮快閃”作為傳播者自主發起、具有特定的秩序、在特定時空節點進行的以“國潮展示”為主體的短暫狂歡,可以被定義為“傳播游戲”的一種呈現形式。
(一)創建游戲
1. 擺脫現實規則并建立游戲秩序
從物理空間層面,“國潮快閃”作為一種“非常規”的公共藝術展演,其組織和策劃往往局限于一個特定圈層,對于大眾而言不具有預設性,以達到更具戲劇性和震懾力的傳播效果。“快閃”的呈現形式打破了當地的時空常規,創造性地擺脫了現實規則對傳播環境的約束。從文化空間層面,海外“國潮快閃”在西方文化空間下以狂歡的呈現形式傳播中華文化元素,作為一種強勢的文化入侵,對本土原有的文化秩序和文化環境造成破壞。 又因其“短、平、快”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來文化符號與既有文化秩序產生的“對抗性”,消解了本土文化接觸者產生的不適應感。簡言之,海外“國潮快閃”不僅呈現于介入和擾動公共空間的創造性實踐,更表征于對西方文化及其藝術體制的挑戰。
“人們喜歡游戲,正是在于擺脫固定的社會結構對自由的限制,傳達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感受”[4]。“國潮快閃”在打破本土原有空間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基礎上,建立自身的游戲秩序。“快閃”活動的組織者通過對活動內容的創造性設計、對活動議程及形式的預先規劃和對活動參與人群的選擇性募集,建立了具有“自愿性”、“樂趣性”等游戲特征的活動秩序。
2. 荒誕行為邏輯下創造傳播快樂
斯蒂芬森的傳播游戲觀認為傳播的要義在于“傳播快樂”,與自我娛樂、自我體驗、自我提升和自我快樂相關聯,強調傳播主體的主觀感受。“快閃”所預先設置的行動計劃可以視作一種新聞腳本,發起者遵循這種腳本為受眾營造了一種脫離公共秩序的荒誕娛樂氛圍,受眾自愿出入于“國潮快閃”的文化空間和現實空間之中,且兩者的邊界非常模糊,近似于一種游戲參與。“國潮快閃”模擬偶發性表演的呈現形式,不具有政治目的、完全追求快樂體驗的動因共同構成了其荒誕的行為邏輯。
海外Z世代中國青年采用“快閃”這一荒誕、“無厘頭”的藝術形式作為跨文化傳播的載體,符合該人群注重傳播娛樂性和主觀感受的集體特質。以實現自我快樂為主要目的的傳播方式也更易于消解不同意識形態下異質文化接觸和交融所產生的排異反應,降低海外受眾在文化身份轉換時的防備和排斥情緒,從而短暫打破中外文化邊界,形成以中華文化融入西方本土文化的多元文化空間。
(二)參與游戲
1. 趣緣驅動下的選擇性匯聚
作為一種傳播游戲,“國潮快閃”強調個體的自我意識和精神層面的自我取悅,其組織和參與的過程是一個個體興趣驅動下的選擇性匯聚。相比于西方的一般“快閃”,“國潮快閃”一般發起于海外留學生校友會、同鄉會等同質聚集且以中華文化背景為深層鏈接的網絡共同體,具有更高的穩定性和可控性。
從受眾的角度,游戲觀下的傳播活動充分尊重個體的自我存在和個體在社會支配機制下的解放,海外受眾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時間安排選擇是否停留、觀看或切身參與“快閃”活動。“國潮快閃” 通過在海外本土環境的展演,聚集對中華文化富有興趣的趣緣群體,推動中華文化認同在海外文化環境中的建立。
2. 網絡二次傳播中的自我指涉
自我指涉作為斯蒂芬森傳播游戲理論下的一個研究視角,就其根源來看是對事物的一種“重新安排”,并以自己期望的方式表達出來[5]。“國潮快閃”的活動場景會被組織者以圖片、短視頻等形式生成多模態的影音資料,并在海外的社交媒體平臺上進行推廣。社媒平臺的二次傳播是“國潮快閃”在海外影響力提升的重要渠道。
對于“國潮快閃”相關內容的生產、轉發推廣、社媒互動、網絡趣緣圈層建立等行動體現出海外受眾在作為文化接觸者過程中自我指涉。從受眾角度出發,海外受眾不僅在偶遇或觀看“國潮快閃”展演時獲得傳播快樂,也能主動參與對“國潮快閃”的意見評論、內容衍生與推廣等環節。這體現了海外受眾基于自身興趣和期待加入“國潮快閃”的二次創作,甚至重新安排傳播內容。這種自主選擇感興趣的傳播話題,通過參與或干涉傳播環節獲得自身滿足感的行為,體現了一種純粹的“玩樂態度”。
從傳播的游戲觀視角來看,海外“國潮快閃”的流行一方面歸功于傳播主體即中國Z世代青年追求自我快樂和自我愉悅的游戲心理,是一種“我本位”的傳播范式;另一方面,“國潮快閃”作為一種傳播游戲,可以為海外受眾創造娛樂心態,模糊異質文化邊界、降低宏觀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沖擊感,與西方文化語境下我國Z世代跨文化傳播的需求相耦合。
二、海外“國潮快閃”的跨文化微觀敘事實踐
從傳播的游戲觀看海外“國潮快閃”,是一種基于個人意識、人格形塑、人際互動等微觀層面對其傳播心理的解構。本文基于敘事情境、敘事內容、講述媒介等敘事學角度,提出我國Z世代人群參與海外“國潮快閃”、展開跨文化微觀敘事的三重實踐策略。
(一)敘事情境:打造空間聚合環境,立足本土化傳播語境
“快閃”強調匿名參與、突發介入和即興表演,組織者基于電子郵件或網上社交平臺發出行動號召和主張,將彼此匿名的參與者集結到公共空間,進而把預先的行動主張表演出來,然后快速散去[6]。“國潮快閃”借助網絡媒介對參與者進行組織和號召,并在預先商定的公共空間進行民樂、雜技、戲曲、華服等組合多種中華文化元素的實體展演,為中華文化的實體呈現打造一種人、物、情感的空間聚合環境。
不同于戲劇、歌舞劇等傳統藝術展演,“國潮快閃”大多在紐約、馬德里、日內瓦等西方大型都市的街道、廣場等場所舉行,可以高效聚集海外華人、留學生等中華文化背景人群,并融入本地的時空環境。例如2024年2月,福建省歌舞劇院民樂團的8名演奏家以福建蟳蜅簪花造型在馬爾代夫首都馬累街頭開展快閃表演,吸引數百名當地居民圍觀并拍攝[7]。2024年2月15日,“春晚序曲 全球看春晚”歡樂春節快閃活動在全球登陸,包括南非第一大城市約翰內斯堡曼德拉廣場、柬埔寨暹粒吳哥機場等地,全球上千名外國友人駐足觀看[8]。
“國潮快閃”選取宏大西方文化背景下一個真實生活場景,開展一場具象的、短時的傳播活動。借助海外觀眾在西方媒介環境中對“國潮”元素的記錄、詮釋與共享,將中華文化話語置入本土傳播語境,給西方受眾傳遞真實、立體、具象的文化接觸感受。
作為高語境文化國家,西方國家的受眾喜愛顯性的文化符號和簡約直接的傳播方式。“國潮快閃”多運用中國紅、中國龍等帶有明顯中華文化特征的象征符號,以樂曲、吶喊、狂歡等情緒飽滿、原始的表述方式傳達話語,與西方傳播語境相契合。
(二)敘事內容:創造個體具身實踐,形構跨文化意義共同體
微觀敘事視角是相對于宏觀敘事視角而言的,指的是將敘事視角對準平凡的個人與群體,從其瑣碎的生活細節、豐富的場景變幻、中近景的景別選擇來呈現出國家層面甚至更高層面的宏大主題,如大國擔當、民族精神、命運共同體等[9]。宏觀敘事視角建構總體國家形象,形塑宏大且籠統的文化記憶;微觀敘事視角則側重微小事件對個體記憶的填充和修飾作用,以求為文化接觸者填補記憶細節亮點,為個體創造對“中國故事”的具身實踐。“國潮快閃”的傳播對象是廣大城市生活中的平凡個體,注重對個體的記憶進行加工展演,創造微觀文化體驗。
“國潮快閃”大多選擇在露天的戶外環境或是開闊的公共場所,開放的物理空間可以弱化異質文化空間之間的邊界感,受眾“退一步就能回歸日常生活”,從而可以開放內心對他者文化的防范機制。其內容的呈現往往富有高度感染力和互動性,受眾隨時可以轉換文化身份,從外來文化接觸者轉變為中華文化的親身演繹者。如2017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快閃紀錄片《海外華人華僑拜年》中,由海外華人在街巷中分發紅色氣球,數百人共同將氣球拴在預先制作好的“福”字框架上,合力拉起“福”字,并共同注目巨型紅色“福”字升入空中。
海外華人作為“快閃”的發起者、外國居民作為“快閃”的參與者,形成了在同一文化空間下的共同在場,同步、同時地對“快閃”中的符號呈現和實踐行為賦予意義。在對“國潮快閃”的共時性文化體驗中,“福”字、舞龍、歌舞等中華文化元素成了承載雙方情感、記憶、認知的“意義共同體”。這種相通的意義收獲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異質文化間的“交點”,為跨文化的民族認同與身份認同創造了可能。
(三)講述媒介:利用數字交互媒介,驅動記憶個性化傳播
“國潮快閃”中微觀敘事策略的選擇,與當下社會數字媒介、移動互聯興盛的新媒體環境不可分割。盡管公共空間中的展演模式大大提升了開放程度,但“國潮快閃”要突破既有的傳播范圍和時空局限,仍需依靠數字媒介的傳播效能。網絡社交媒體具有成熟的互動機制和算法推薦機制,能夠拓寬傳播邊界,創造網絡受眾在虛擬空間中的文化體驗,驅動個體記憶在網絡空間中的無限衍生。此外,微觀敘事通過與各類新興微媒體融合,實行以文字、圖畫、音頻、視頻聯合敘述宣傳的模式,還可借助場景再現、環境渲染、增強現實等附加手段提升“國潮快閃”微觀敘事的成效[10]。內容生產者可以利用數字媒體技術,通過對“國潮快閃”的個性化再創作以增強其魅力,追求中華文化在海外輻射范圍的不斷擴大。
2014年9月,一場名為《多倫多·中國心》、時長約10分鐘的公益快閃演唱會在多倫多市中心鄧達斯廣場舉行,其相關視頻在世界范圍內多個社交媒體平臺發布,獲得過億點擊量[11]。“國潮快閃”博主“碰碰彭碰彭”在YouTube、Instagram等海外社媒平臺發布自己在法國街頭演奏古箏的系列“快閃”視頻,截至目前已有96.1萬訂閱者,單個視頻播放量最高1758萬次。案例表明,“國潮快閃”作為一種具象的、展現大眾生活形態的藝術展演形式,能夠滿足新媒體環境下用戶對傳播題材小切口、接地氣的微觀視角需求。
數字媒介的再創作賦能“國潮快閃”的跨文化傳播力進一步提升。至此,我們發現“國潮快閃”通過網絡社交平臺發起行動號召;在本土文化空間開展實地展演,形構跨文化意義共同體,產生共通性文化體驗;借助社交媒體再一次推廣,驅動記憶無限傳播,為下一次活動的發起做群眾準備。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互為實踐基礎,形成傳播路徑閉環。
三、作為游戲的“國潮快閃”:中國Z世代傳播游戲觀背后的文化價值回歸
在全球化、泛娛樂化、消費主義并行的時代,以Z世代為主體的新媒體人基于“快樂至上”的傳播心理打造傳播游戲,將傳播重心從文化培養轉移為娛樂體驗,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對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去價值”。
“國潮快閃”是我國海外Z世代人群在以“快閃”為代表的現代流行文化底色上對中華文化符號的投射與創新,這體現了中國Z世代不僅具有注重自我娛樂、偏好“我本位”傳播的代際特征,也兼具與中華文化的情感鏈接與價值認同。
馬克思·韋伯在《學術與政治》一書中提出“世界除魅”,即“祛魅”的概念,意指對崇高、典范的消解,破除權威與神圣,揭開事物神秘的面紗[12]。所謂的文化之 “魅”可以從兩個層面解讀:一是神秘性,二是感召性[13]。面對現代語境下傳統文化神秘性、魅惑力的消解,重構文化的呈現形式來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新賦魅的必要性與日俱增。“國潮快閃”利用“快閃”在沒有預設的情況下快速展演又快速散去的活動特質,以及中華文化本身的多面性,在可見中創造“不可知”,以此重塑中華文化在海外文化語境中的神秘性。這種神秘性的復生又再次加強了中華文化對于一切接觸者的感召力,從而實現文化賦魅,為我國在海外的國家形象建構與國際傳播增加籌碼。
回歸至范式的反思層面,海外“國潮快閃”的創造和興起體現了一種文化價值的回歸,我國跨文化傳播不能放棄中華文化內核而空談創新,不能放棄微觀層面的異質文化接觸而空談國家敘事。在海外的中國Z世代于傳播游戲中柔性輸出中華文化,力求破除海外文化語境中的族裔偏見和政治歧見,轉向對中國國家形象及文化底蘊的認同。
參考文獻:
[1] 新華網.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EB/OL].[2021-01-06].http://www.moj.gov.cn/pub/sfbgw/gwxw/ttxw/202106
/t20210601_424961.
[2] 海龍.傳播游戲理論再思考.新聞學論集(第20輯)[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193.
[3] 宗益祥,陳潔雯.走向科學人本主義范式:傳播游戲理論的歷史溯源與現實觀照——與傳播“信息理論”的比較研究[J].傳媒觀察,2022(8):37-44.
[4] 宗益祥.游戲人、Q方法與傳播學[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120.
[5] 吳浩然,胡茂鈞.傳播游戲理論視域下“網紅記者”現象解析[J].新聞前哨,2023(8):12-14.
[6]楊光影.“國潮快閃”在海外:一種國際傳播的“藝術地理”范式[J].藝術傳播研究,2023(4):117-128.
[7] 人民日報.“福年福味”閃現馬爾代夫街頭[EB/OL].[2024-2-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1208994010365357amp;wfr=spideramp;for=pc.
[8] 新華網.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4年春節聯歡晚會與全球歡度中國年[EB/OL].[2024-02-10].http://www.news.cn/politics/20240210/07b6c94a769d4418a95eb4d7ef71b9f9/c.html.
[9] 李超楠.少數民族題材紀錄片微觀敘事表達及個體形象構建——以《石榴花開2》為例[J].喜劇世界(下半月),2024(4):55-58.
[10] 陳佳雨.傳遞記憶的微光:論檔案記憶再生產的微觀敘事[J].檔案與建設,2024(1):51-56.
[11] 中國政府門戶網站.多倫多華僑華人“歌唱祖國”迎接中國國慶[EB/OL].[2014-09-17].www.gov.cn.
[12] 王澤亞.現代文學藝術創作的“祛魅”與“復魅”[J].湖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6):52-57.
[13] 夏天成,武元婧.文化賦魅、祛魅與返魅對文化發展及矛盾化解的啟示[J].新疆社會科學,2015(4):1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