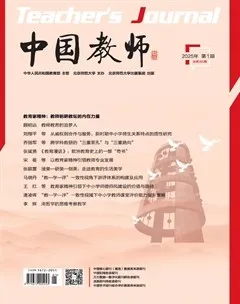用哲學(xué)的思維考察教學(xué)
最近研讀了孫杰教授的《為己之學(xué):中國(guó)教學(xué)哲學(xué)的歷史考察》,使筆者對(duì)中國(guó)古代的教學(xué)哲學(xué)有了新的認(rèn)識(shí)。孫杰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以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為研究對(duì)象,將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基本問(wèn)題的考察放置在哲學(xué)的思維下做歷史透視,采用歷時(shí)與共時(shí)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式,圍繞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相統(tǒng)一的邏輯體系,從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生成、變化、發(fā)展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中,探尋和詮釋了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精神實(shí)質(zhì)—仁智統(tǒng)一的為己之學(xué)。讀罷,筆者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四方面。
一、追尋一個(gè)新論題:教育學(xué)史的研究應(yīng)該成為教育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
與其他學(xué)者一般將教學(xué)思想史或教學(xué)論史作為教學(xué)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不同,作者將教學(xué)哲學(xué)史看作教學(xué)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循著這樣的思路,本書(shū)主要關(guān)注的就不再是中國(guó)古代教育史中的教學(xué)思想或教學(xué)論,而是基于教學(xué)思想或教學(xué)論的哲學(xué)反思—教學(xué)哲學(xué)。正如作者所言,教學(xué)哲學(xué)是研究和揭示“教和學(xué)關(guān)系及其發(fā)展的合理性”的哲學(xué),教學(xué)哲學(xué)的主要任務(wù)是研究“為何教和學(xué)”“教和學(xué)什么”“如何教和學(xué)”。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歷史考察就是研究中國(guó)古代教育史中的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方面的哲學(xué)問(wèn)題,就是思考中國(guó)古代教育史中的教學(xué)如何在教學(xué)觀(即關(guān)于學(xué)與教及其相互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的支配下圍繞教學(xué)操作思路(即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而展開(kāi)教學(xué)活動(dòng)的哲學(xué)問(wèn)題。作者之所以將教學(xué)哲學(xué)作為教學(xué)史研究的對(duì)象,是因?yàn)樽穼ぶ逃龑W(xué)家陳元暉的學(xué)術(shù)遺愿—“教育史應(yīng)該叫教育學(xué)史,是教育理論在各部門(mén)體現(xiàn)的歷史”“教育學(xué)史的研究應(yīng)該成為教育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既然教育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是教育學(xué)史研究,那么,教學(xué)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就應(yīng)該是教學(xué)哲學(xué)史研究。換句話說(shuō),作者追尋陳元暉先生的學(xué)術(shù)遺跡,通過(guò)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展開(kāi)歷史考察,尋求一種研究中國(guó)教育史的新范式,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教育學(xué)史研究成為教育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的研究主旨。
在筆者看來(lái),與其說(shuō)本書(shū)是一本教學(xué)史論著,毋寧說(shuō)是一本中國(guó)教育學(xué)史著作。本書(shū)既不是研究教學(xué)和哲學(xué)的關(guān)系,也不是用哲學(xué)研究范疇進(jìn)行教學(xué)研究,而是“用哲學(xué)的思維方式和反思的方法來(lái)思考教學(xué)的基本問(wèn)題”。作為陳元暉先生學(xué)術(shù)遺愿的追尋,本書(shū)集中反映出作者對(duì)中國(guó)教育學(xué)史的研究情結(jié)和秉承師門(mén)(注:陳元暉為作者導(dǎo)師的導(dǎo)師)一貫追求的學(xué)術(shù)志向,展現(xiàn)了作者作為一名中國(guó)教育史學(xué)者的使命自覺(jué)和責(zé)任擔(dān)當(dāng)。
二、踐行一個(gè)新邏輯: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的統(tǒng)一
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歷史考察就是研究和思考中國(guó)古代教育史中的教學(xué)如何在教學(xué)觀(即關(guān)于學(xué)與教及其相互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的支配下圍繞教學(xué)操作思路(即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展開(kāi)教學(xué)活動(dòng)的哲學(xué)問(wèn)題。也就是說(shuō),教學(xué)哲學(xué)包含兩個(gè)基本要素: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作者在書(shū)中依次考察了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中的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
1.教學(xué)觀
教學(xué)觀是“教學(xué)應(yīng)該是什么”的思維觀念。作者認(rèn)為,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是從論述學(xué)與教及其相互關(guān)系開(kāi)始的。作者通過(guò)分別考察“為己之學(xué)”中的學(xué)與教、修身中的學(xué)與教、教學(xué)相長(zhǎng)中的學(xué)與教,指出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是站在“學(xué)”的立場(chǎng)上看待學(xué)與教的關(guān)系問(wèn)題。在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中,學(xué)是貫穿教育者終身的行為,而教只是教育者另一種形式的學(xué),或者說(shuō)是學(xué)的另一種呈現(xiàn)方式。由此,在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教學(xué)觀中就形成了以學(xué)論教的整體性思維。
2.教學(xué)操作思路
教學(xué)操作思路是“教學(xué)應(yīng)該怎么做”的思維路徑。作者指出,教學(xué)操作思路包括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和教學(xué)方法。教學(xué)目的與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相互關(guān)聯(lián),有什么樣的教學(xué)目的就會(huì)相應(yīng)地選擇什么樣的教學(xué)內(nèi)容和教學(xué)方法,教學(xué)內(nèi)容和教學(xué)方法都為教學(xué)目的服務(wù)。作者在考察中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在教學(xué)操作思路上表現(xiàn)出仁智雙修的教學(xué)目的、文道合一的教學(xué)內(nèi)容和以道自得的教學(xué)方法。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德性和學(xué)問(wèn)并重,所以在教學(xué)目的上強(qiáng)調(diào)培養(yǎng)既有高尚品德之“仁”,又有豐富知識(shí)之“智”的德才兼?zhèn)渲恕閷?shí)現(xiàn)這一教學(xué)目的,古代將“六經(jīng)”等既包含豐富文化知識(shí),又蘊(yùn)含深刻道德理念的文本作為教學(xué)內(nèi)容。在教學(xué)方法上,古代教學(xué)強(qiáng)調(diào)學(xué)生通過(guò)對(duì)以“六經(jīng)”文本為中心的教學(xué)內(nèi)容的自我研讀和體悟,以一種類似“博學(xué)之,審問(wèn)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xué)習(xí)方法,實(shí)現(xiàn)文化知識(shí)上的自我發(fā)展和道德品質(zhì)上的自我完善。
誠(chéng)如作者所言,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相統(tǒng)一的邏輯體系受劉慶昌教授的教育思維理論的影響和啟發(fā)。劉慶昌教授在《教育思維論》中提出,教育思維是教育觀和教育操作思路的統(tǒng)一體,一定的教育觀就會(huì)形成相應(yīng)的教育操作思路。筆者認(rèn)為,本書(shū)可以說(shuō)是作者對(duì)劉慶昌教授的教育思維理論在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史研究中的一次學(xué)術(shù)踐行。透過(guò)本書(shū)的文本闡釋,一個(gè)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相統(tǒng)一的教學(xué)哲學(xué)研究框架呼之欲出。
三、勾勒一個(gè)新形象:學(xué)不厭、教不倦的“好教師”
作者在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史的討論中,還總結(jié)概括了教學(xué)哲學(xué)史上的教育者(師者)形象及境界追求,這為我們今天的教師教育和教育家培養(yǎng)提供了一定參考和借鑒。
1.師者之形象—學(xué)不厭、教不倦
在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史上,孔子作為“好教師”的代表、作為“至圣先師”而為后世取法,是師者形象的最真實(shí)體現(xiàn)。這種形象又具體表現(xiàn)為孔子本人所言說(shuō)和展現(xiàn)出的“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學(xué)而不厭”,表明教育者是個(gè)善學(xué)的人;“誨人不倦”,表明教育者也是個(gè)善教的人。這種“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形象體現(xiàn)出的正是教育者本人的善學(xué)善教,而善學(xué)善教正是一個(gè)“好教師”所應(yīng)具備的品行,是“教學(xué)哲學(xué)所期望達(dá)到的理想境界”。
2.師者之功夫—教學(xué)相長(zhǎng)
《學(xué)記》中這樣闡述教學(xué)相長(zhǎng):“學(xué)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qiáng)也。故曰:教學(xué)相長(zhǎng)也。”正是因?yàn)榻逃咴趯W(xué)與教的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不足”和“困”,才更促使其反求諸己、自強(qiáng)不息。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教學(xué)相長(zhǎng)就是一個(gè)具備“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精神的“好教師”在教學(xué)中不斷修煉自我的過(guò)程。
3.師者之追求—仁智統(tǒng)一
仁智統(tǒng)一就是一個(gè)“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好教師”在教學(xué)中經(jīng)由教學(xué)相長(zhǎng)的自我修養(yǎng),最終要達(dá)到和實(shí)現(xiàn)的理想人格和境界追求。正如《孟子》中提到的:“學(xué)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也。”也就是說(shuō),“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其實(shí)內(nèi)含著對(duì)一個(gè)“好教師”既“仁”且“智”的要求和期待。沒(méi)有“仁”的教育者無(wú)心教學(xué),沒(méi)有“智”的教育者無(wú)力教學(xué)。只有具備“仁”的教育者才會(huì)關(guān)愛(ài)他人,在教學(xué)中表現(xiàn)出對(duì)學(xué)生成長(zhǎng)的關(guān)懷以及對(duì)學(xué)生人格完善的期待;只有具備“智”的教育者才會(huì)學(xué)無(wú)止境,在教學(xué)中不斷改進(jìn)教學(xué)方法,積極引導(dǎo)學(xué)生發(fā)展。像孔子那樣成功的教育者正是兼具“仁”“智”,是“仁智統(tǒng)一”的師者理想人格和奮斗目標(biāo)。作者也提到,《荀子》從三個(gè)具體層面論述仁智統(tǒng)一的師者理想人格,其中“仁”的境界追求是從“使人愛(ài)”到“愛(ài)人”再到“自愛(ài)”的邏輯進(jìn)路;“智”的境界追求是從“使人知”到“知人”再到“自知”的邏輯進(jìn)路。
作者所勾勒的“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好教師”形象、教學(xué)相長(zhǎng)的“好教師”修養(yǎng)功夫、仁智統(tǒng)一的“好教師”理想人格和境界追求,一方面提供了關(guān)于教育者基本素養(yǎng)的新意解讀,另一方面也為教育者提供了一條以“仁”和“智”的培養(yǎng)為核心的發(fā)展路徑。教育者只有具備“學(xué)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師者形象、教學(xué)相長(zhǎng)的師者修養(yǎng)功夫、仁智統(tǒng)一的師者理想人格和境界追求,才能成為真正熱愛(ài)教育的“好教師”。教師教育應(yīng)該努力培養(yǎng)和造就這樣的師者。
四、提煉一個(gè)新范式:仁智統(tǒng)一的為己之學(xué)
通過(guò)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歷史考察,作者在本書(shū)最后總結(jié)得出: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本質(zhì)就是在踐行仁智統(tǒng)一的為己之學(xué)。也即,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無(wú)論是從教學(xué)觀來(lái)看,還是從教學(xué)操作思路來(lái)看,就是以“為己”為旨?xì)w的“仁智統(tǒng)一”之學(xué)。
先說(shuō)“為己之學(xué)”。作者認(rèn)為,“為己之學(xué)”是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教學(xué)宗旨。這是作者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中的教學(xué)觀的提煉概括。在學(xué)與教及其相互關(guān)系上,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認(rèn)為教學(xué)不僅是成就學(xué)生的“成人之學(xué)”,更是教育者完善自我的“為己之學(xué)”。教育者對(duì)學(xué)生的教學(xué),也是自身學(xué)的一種體現(xiàn)。更進(jìn)一步說(shuō),就是從“為己”的目的看待教學(xué)的過(guò)程,即不論是“獨(dú)學(xué)”“共學(xué)”,還是“教人以學(xué)”,都屬于教育者自我學(xué)習(xí)的組成部分。在學(xué)與教及其相互關(guān)系中,學(xué)是核心,教只是學(xué)的一個(gè)組成部分,教育者的學(xué)除了教以外,還有“獨(dú)學(xué)”與“共學(xué)”。由此,教育者的學(xué)與教的活動(dòng)就徹底融入“為己之學(xué)”之中。在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教學(xué)觀方面,“為己之學(xué)”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教育者在教學(xué)中應(yīng)有的學(xué)術(shù)堅(jiān)守和學(xué)術(shù)追求。
再說(shuō)“仁智統(tǒng)一”。作者認(rèn)為,“仁智統(tǒng)一”就是指在教學(xué)中同時(shí)追求道德情感—“仁”與道德理性—“智”的統(tǒng)一。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是圍繞仁智統(tǒng)一的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而展開(kāi),并最終由仁智統(tǒng)一的教育者引導(dǎo)學(xué)生達(dá)到理想的教學(xué)境界。這是作者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中的教學(xué)操作思路的提煉概括。這種以“仁智統(tǒng)一”為內(nèi)核的教學(xué)操作思路正是基于教育者“為己之學(xué)”的教學(xué)觀形成的。“仁智統(tǒng)一”的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和教學(xué)方法正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為己之學(xué)”的教學(xué)觀。
作者在這里提煉出一種教學(xué)哲學(xué)的新范式,即仁智統(tǒng)一的為己之學(xué)。作者把這種新范式看作一種基于自身優(yōu)秀教育遺產(chǎn)構(gòu)建的教學(xué)哲學(xué)新范式。這種新范式既是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中教和學(xué)關(guān)系的揭示,也是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中教學(xué)目的、教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方法中“仁智統(tǒng)一”教學(xué)精神的強(qiáng)調(diào)。隨著這一新范式的提出,本書(shū)也由此形成了一種屬于中國(guó)的“教學(xué)哲學(xué)的話語(yǔ)體系和概念系統(tǒng)”。
在筆者看來(lái),本書(shū)所彰顯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既體現(xiàn)了一種學(xué)術(shù)上的傳承,也展現(xiàn)出一種學(xué)問(wèn)上的繼續(xù)。作者通過(guò)將教學(xué)哲學(xué)史作為教學(xué)史研究的中心環(huán)節(jié),繼承了陳元暉先生以教育學(xué)史為教育史研究中心環(huán)節(jié)的學(xué)術(shù)追求;同時(shí),作者又對(duì)劉慶昌教授所提出的教育思維理論在教學(xué)哲學(xué)領(lǐng)域做了進(jìn)一步拓展和詮釋,從而構(gòu)建了一種全新的教學(xué)哲學(xué)史研究框架和研究邏輯;最后,作者用“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就是教學(xué)觀和教學(xué)操作思路的統(tǒng)一體并止于仁智統(tǒng)一的圣賢境界”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對(duì)中國(guó)古代教學(xué)哲學(xué)的歷史考察進(jìn)行了概括總結(jié),不啻于對(duì)中國(guó)教學(xué)哲學(xué)的話語(yǔ)體系和概念體系進(jìn)行的一次有益嘗試和探索。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本書(shū)無(wú)異于是一本教學(xué)哲學(xué)史“新論”。
(作者系全國(guó)青少年學(xué)生法治教育實(shí)踐示范基地研究助理)
責(zé)任編輯: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