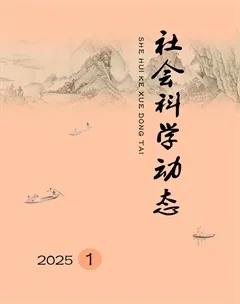學術研究為蒼生
摘要:文學、文化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經典作品是社會現實的折射與反映,也是作者家國情懷的體現。《開窗放入大江來——劉躍進講演錄》是劉躍進先生近30年來學術講座與大會致辭的精選本,它既是講演者對古代文學與文獻研究的結晶,對古代文學和當下學術研究的審視與反思,也是其治學方法、學術研究方向、孜孜不倦的學術追求,更體現了一位資深學者所擁有的人文精神、家國情懷與文化擔當。
關鍵詞:《開窗放入大江來》;學術創新;家國情懷;文化責任
中圖分類號:H1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5)01-0019-04
古往今來,文學、文化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經典作品是社會現實的折射與反映,是作者家國情懷的體現。劉躍進先生始終遵奉“文章須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1)的治學理念,其《開窗放入大江來——劉躍進講演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講演錄》)對“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的命題進行闡釋,認為文章應該有益于學術,有益于社會;前者涉及學術積累與創新的問題,后者指出學術研究貢獻社會、貢獻蒼生之目的。(2)筆者以為,“有益于學術”屬于專精的學術研究,“有益于社會”重在學術的普及工作。劉躍進先生將專精的學術研究作為“守其一而終生”的事業追求,將“有益于社會”作為自己治學的目標,這體現了一位資深人文學者的學術責任、家國情懷與文化擔當。
一、學問文章:守其一而終生
學術積累主要表現為文獻、史料的積累。文獻是學術積累的基礎,學術積累是學術創新必要條件。新的文獻資料考證可以推動學術的進步與發展,推動學術的變革與學術理念的更新,如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顧頡剛等人的“三重證據法”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新材料的基礎之上。(3)文獻學是《講演錄》的核心話題之一,劉躍進先生始終重視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重視文獻資料在學術變革與學術理念更新中的重要作用,將“有益于學術”作為終生的學術追求,并身體力行地服務于學術。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重視文獻整理與資料匯編、提出治學方法與學術理念、推動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的發展。
文獻學是從事傳統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學科研究的基本技能的訓練,是步入學術大門、登堂入室的路徑。老一輩學者均注重文獻資料的整理。如姜亮夫先生主張做研究之前,要先進行資料匯編、竭澤而漁式地收集資料。作為姜先生的弟子,劉躍進先生繼承老師的衣缽,十分重視文獻整理與資料匯編。如他輯存《文選》舊注時,“原原本本”地將“清人沒有見到的文獻,或者所見版本不同的文獻匯為一編”,進行集成性的文獻學研究。(4)由此,《文選舊注輯存》就成為收集版本齊全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集大成之作”(5)。文獻學是走進文獻、闡釋作品的最佳途徑與方法。在文獻整理的過程中,劉先生提出了治學方法與學術理念,進行學術創新。如界定《文選》“舊注”的五個方面的含義(6);歸納文獻學的現代意義——強化學術信念、推動學術轉型、建構學術體系;提出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歷史感”與文學地理學的命題,注重文學的時空屬性;指出“傳統文獻學是我們進入傳統文化領域的必由之路”(7),“誰繞開史料,學術界將來一定會繞開他”(8);剖析文學史的文學、歷史雙重屬性,認為理解文學屬性需要具備藝術感受、理論素養、文獻積累三個條件(9),等等。這些治學方法與學術理念皆有獨到的學術創見。
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是一個致力于文獻史料研究與學術創新的團體。劉躍進先生是該學會的資深會員,先后擔任秘書長、會長等職務,尤其是自從2003年擔任學會的常務副會長兼法人代表后,他一直竭力推動該學會的發展與創新,服務于學術界。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組織史料學會議,重視學科的發展。如在2004年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他和與會專家們共同提出“史料收集整理是研究的先導,呼吁通過文獻的收集、整理尋求研究的新突破口,帶動整個學科的發展”(10)。其二,設立史料學分會,擴大學會的影響力。在劉先生的主導下,該學會于2006年成立近現代文學史料學分會和古代文學史料學分會,2017年成立民族文學史料學分會。各分會積極吸納年輕學人入會,定期舉行學術研討會,擴大了學會的影響力,助力史料學的研究更趨細致、專業化,推動文學史料、傳統文獻研究的發展與創新。
劉先生重視文獻積累與學術創新,并將學術創新貫穿到研究工作的始終,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出于自身文獻積累、學術積淀方面的“先天不足”。因時代原因,他早年失去了很多學習的時機,大學時代所謂的文獻學課,“實際上是工具書的檢索課,遠遠不能涵蓋文獻學的內容,連邊都不沾”(11)。這樣就造成了文獻基礎、學術積淀上的先天性營養不良,就是所謂的“悟性不錯,基礎較弱”。這是對文獻缺失的焦慮,也是對學術積累不足的自我認知。于是,他心中難免浮現“一代不如一代的悲情”,而消解這一“悲情”的最好方法則是努力閱讀文獻、創新學術。
其二,文獻積累是理解文學屬性、進行學術創新的重要條件。凡是有成就的文學研究大家,都比較注重總結文學史,審視文學史的書寫。劉先生認為文學史具有文學與歷史雙重屬性,而理解文學屬性需要具備三個條件:藝術感受、理論素養、文獻積累。(12)其中,文獻積累是理解文學屬性、進行學術創新的重要前提條件。
其三,強調回歸文獻與實證研究是當下學術創新的最佳路徑。近年來,學術界已經開始糾正理論先行、迷信西方現代學說,以及膜拜中外文學概論與文化理論的偏頗和極端做法,更加注重文獻資料的積累。于是,大多數學人將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獻,以期從大量的文獻積累中尋求學術研究與創新的生機。這就是劉先生所說的近些年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第二個明顯變化”(13)。事實上,就結果導向而言,這一轉變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科研項目注重文獻整理與學術創新,如近些年所立項的國家社科項目、省部級項目明顯偏向于文獻整理、文本研究與學術理論創新的結合;二是高端論著中兼具文獻整理、文本細讀與學術理論創新。
劉先生認為,“我們每一個人,終其一生,不過守其一點而已,小有所成,就已經很不容易了”,并以進入王國維所謂的“人生第一境界”之不易比附人生“小有所成”的不易。(14)故而,他將學術積累與學術創新作為終生奮斗的事業,竭力創造有益于學術與社會的文章論著,以達到“小有所成”。
二、家國情懷:人文學者的執守
文獻積累與學術創新的目的是闡釋文本、解讀經典,以便更好地發掘經典文本所蘊含的思想精髓、文化內涵。這在《講演錄》中同樣得到充分的展現。
首先,學術研究要關注人。《講演錄》中多次提到文學研究者對人的關注,如“文學首先是寫人的,寫人的喜怒哀樂,寫人的最精微感覺”,“不管你怎么標榜高深,人文學科離不開人,離不開社會,一旦脫離現實,脫離社會,這樣的學術是沒有生命力的”(15)。知人論世是古代文史研究中常用的一種方法,它不僅能考證具體作品產生的背景與相關史事,也能使研究者更加了解歷史,增強人們精神世界的向心力與凝聚力。所論之“世”,既包含作者所處的社會生活大環境,也包含作者所面對和關注的物質情況與生活狀況。因為不同的階層與生存環境、物質條件,使作者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故此《講演錄》強調文學研究要結合社會現實考察文學作品與史料,注重分析社會階層、關注文人的生存環境和物質條件。(16)如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價值》一文,結合社會現實分析兩晉時期家族譜牒類著述增多的原因:西晉時世族大家修撰譜系作為炫耀門第的一種風尚;東晉的南渡士族為保留歷史記憶而修撰家族譜牒;入主中原的五胡借助譜牒標榜正宗,或推行漢化政策,從而使自己政權的合法化。其結果是,兩晉時姓氏族譜類圖書急劇增多。(17)這樣的分析合情入理,結論令人信服。
其次,學術研究要與人民群眾的需求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關聯。自古以來,優秀的文學作品都關注社會與民生,關注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具有真善美的特質。研究者只有“深刻地理解人民大眾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關注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人民群眾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才能獲得發展的生機,才能提升學術的品位”(18),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將學術研究與民族的未來、民眾的需求密切結合,這樣的研究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這在《講演錄》中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揭橥古代作家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家國情懷,如陸游、杜甫與他們的詩篇;二是尋繹近代以來的學術前輩將文學研究與政治結合的軌轍,證明學術研究的旨歸是為解決社會問題。劉先生列舉20世紀40年代初姜亮夫先生提出“夏民族以龍為圖騰”的理論命題,經過黃文山、李則剛、衛聚賢等學者的接力,至聞一多《伏羲考》明確指出龍是我們立國的象征,發明龍圖騰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理想,說明學術研究與家國命運結合起來方能具有生命力。同時,他還列舉魯迅主張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姜亮夫先生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屈原和《楚辭》、敦煌文獻,以及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研究古代文化是為活著的人,研究杜甫是為了現代人等事例理論命題(19),說明文學研究與現實生活結合的必要性與重要性。針對當下學科劃分過細、學科之間的界限森嚴等弊端,他大聲呼吁學術研究者要走出狹小的圈子,“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20)。這些做法與命題,充分體現了一個學者的學術格局與視野、職業持守與家國情懷。
再次,注重學術普及工作。盡管學術普及工作不屬于專精的學術研究,但它是與當下社會結合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是家國情懷的具體體現。劉先生列舉諸多有成就、有聲望的學者著述十分注重學術普及的例子,如余冠英《詩經選》《三曹詩選》《樂府詩選》、俞平伯《唐宋詞選釋》、錢鐘書《宋詩選》等。(21)普及工作的最佳途徑就是深入社區與基層,到群眾中宣講傳統文化。為此,劉先生提出通過社區、學校、企業三種途徑傳播傳統文化(22),并身體力行到北京孔廟國子監進行國學講座,使“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忠孝合一的道德教化的在平民百姓中發揚光大(23),使傳統文化深入基層,走進尋常百姓家。他還呼吁學者重視學術普及,使學術真正服務于社會。學術普及使眾多的非專業基層民眾能接觸傳統文化,了解國學,感受文化的溫度,從而具有人文情懷。
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24)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學經典蘊含著人文精神與家國情懷,承載著凝聚民族共識的使命。我們只有揭橥并推廣、傳播這些思想意蘊、精神內涵,方能展示其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完成文化使命。就此而言,劉先生的《講演錄》堪稱是一部典范。
三、傳世意識:文化賡續的使命擔當
華夏文化雖歷經千載而未曾中斷,除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思想意蘊、精神內涵外,還要歸功于歷代學者的傳承與呵護。這些學者以賡續中華文明為使命,表現出強烈的傳世意識與文化責任感。作為功成名就的資深學者,劉躍進先生身上時刻體現出這種意識與責任感。
首先,接續傳統,繼承前輩學者的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想。人的一生是短暫的,得之于傳統與前人的多,能添加于其上的少,需要敬畏傳統與前輩。《講演錄》注重繼承傳統,繼承授業恩師、學術前輩的思想與理念。劉先生多次提到自己受益于本科時的老師葉嘉瑩先生、羅宗強先生,碩士導師姜亮夫先生以及博士導師曹道衡先生。這些前輩大家對其影響是多方面的。他說,葉嘉瑩“給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窗口”,改變了自己的學術選擇——由作家夢、文學夢轉變為古典文學研究的夢想,提升了理解文學作品的站位,改變了對生命意義的不同體悟,以至于自己后來在授課中模仿葉先生的講課風格,變為葉先生的忠實粉絲。(25)姜亮夫先生的治學方法與理念對劉先生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尋找資料的方法、解決問題的技能、開闊的研究視野。(26)這些方法與理念既是學術的方法論問題,也牽涉到學風問題,至今仍對自己乃至學術界有著重要影響。作為授業恩師,曹道衡、沈玉成等先生的學術思想與治學理念對劉先生更是影響至深。其他如傅璇琮、俞平伯、王伯祥、吳世昌、吳曉鈴等先生的知識學問、道德人品皆對其產生影響。這些老師不僅傳道、授業、解惑,他們所具有的堅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和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更是激勵學生后輩不斷前行的不竭動力。劉先生在其回憶性散文集《從師記》中詳細地介紹了自己與這些文學大家之間的交往,以及師從他們讀書、治學的感悟,稱“轉益多師是良師”(27)。前輩學者的道德學問是每位后輩學人學習的榜樣與楷模,進步的階梯。正是出于感恩,他把每位恩師的學術指導記在心上(28),落實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之中,為自身創建新的范式奠基、蓄勢。
其次,構建“中國文學”的體系范式。鑒于歷史的原因,100多年來,中國的文學因過分地強調學習“蘇東”與西方而出現“東倒西歪”的迷途現象,以至于出現“文學的概念被西方化,文學的本質被表面化,文學的評價被標準化,文學的功能被庸俗化,文學的形式被簡單化”等弊端。(29)基于此,近年學術界提出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學術體系,構建“中華文學”。作為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劉先生身先士卒,認為“這應當是新世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工作者所面臨的最重要的歷史任務”,并一直為此而孜孜以求。他認為,“中國文學”是“一個建立在大中華文學史觀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既是現實的實踐問題,也是深邃的理論問題”(30),并對中國文學的三大體系進行思考、論證。具體而言,“中國文學”就是以堅守傳統文化為基礎,具體文史貫通、古今貫通、中外貫通的宏闊視野,將探尋民族基因、鑄牢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作為使命,從而達到纘承“中華統緒”之目的。為此,劉先生研究董仲舒對《春秋》“大一統”觀的揭橥,司馬遷系統勾畫華夏文明自五帝以來“不絕如線”的譜系,以及古代帝王祖述五帝以求華夏正統地位的事實,從實踐與理論諸方面,將這一問題往前推進。這顯示了他宏闊的學術格局、高遠的學術站位。
作為先生30年來學術講座與大會致辭的精選本,《講演錄》既是對古代文學與文獻研究的結晶,對古代文學和當下學術研究的審視與反思,也是先生的學術歷程、學術思想的具體展現。吳承學先生曾言:“好的學者必有傳世意識,這樣才會有比較高的自許與文化責任感。”(31)《講演錄》體現出了劉先生較高的自許與文化責任感,“有益于學術,有益于社會”,也勢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
注釋:
(1)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欒保群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5頁。
(2)(4)(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5)(26)(29)(30) 劉躍進:《開窗放入大江來——劉躍進講演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436、379、379、264、264、170、266、109、170、87、111、170—171、174、119、340、337、245、169、484—485、477—479、447、111、88、210頁。
(3) 20世紀初,王國維綜合利用“地下發現之新材料”和“紙上之材料”而提出“二重證據法”,對后世的文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20世紀中葉以后,顧頡剛、饒宗頤、徐中舒等學者增加“民俗學的材料”,繼承并補充了“二重證據法”而提出“三重證據法”,并將此方法運用到文史、民俗等學科的研究中,其影響力得到學界的普遍公認。
(5) 張涌泉、金少華:《劉躍進〈文選舊注輯存〉述評》,《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2018年第2期。
(24) 習近平:《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展示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人民日報》2021年12月15日。
(27) 參見劉躍進:《從師記》,人民文學出版社 2022年版。
(28) 劉躍進、傅謹:《讀書·從師·成長——劉躍進〈從師記〉新書發布會》,《新閱讀》2022年第7期。
(31) 吳承學:《學者要有傳世意識與文化責任感》,《南方都市報》2013年12月12日。
作者簡介:梁奇,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上海, 200444。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