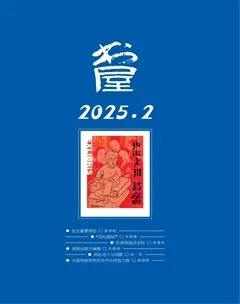勞承萬哲學美學的“三元結構”
2024年是勞承萬先生的鮐背之年,也是先生從事教學科研七十周年。于我而言,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需要禮敬的事情。第一次和先生見面,是1992年在全國農展館附近召開的美學會上,這成為我的人生和學術研究的重要轉折點。在1993年至1997年間,我在先生主持的湛江師院中文系工作并執弟子禮,沐浴春風,聆聽教誨,奠定了從事學術研究的根基。離開先生以后,我們交流密切,從書信到微信,延續至今。有一次和自己的學生聊天,曾說我們是真正的“名門正派”:國學源自劉夢溪先生,因為我是夢溪先生的大弟子;西學則源自勞承萬先生,他是康德專家韋卓民先生的弟子。除了未能免以門第自高之俗,這也包含了一點微妙的愿望,即盡管自己跟隨兩位先生都學得不好,又轉移了領域,但還是希望年輕人能接上這一高貴和純粹的“學統”并發揚光大。兩位先生盡管學術領域相去較遠,但均為有道行、有風骨、能為青白眼的高士。相對而言,對偏居南海一隅的勞先生,我會更多一些牽掛之情。除了當年的知遇之恩,他的哲學美學研究也成為我最重要的學術啟蒙和理論來源,不管是最初的美學研究,還是后來的城市研究。
先生的學術研究和貢獻,一般被后學劃分為三大領域:一是以《審美中介論》《審美的文化選擇》《康德美學論》等為代表的哲學-美學研究;二是以《詩性智慧》《中國古代美學(樂學)形態論》和《中國詩學道器論》為代表的中國美學-詩學研究;三是以《中西文化交匯中近百年之理論難題》《中國文化之特質》《根系學術形態論》為代表的“哲學美學-中國古學”研究。其中,我個人學習且受惠最多的是哲學-美學研究。中國美學-詩學研究雖與我所從事的中國詩性文化研究有關,但由于他最看重的是牟宗三先生,而我曾提出要把牟氏的“以儒家改造康德”變為“援康德補孔孟”,所以與先生的共同語言并不算多。
關于先生的哲學美學對我的影響,曾有一個十分生動的例子。二十年前,先生在推介我的《苦難美學》時寫道:“一個窮孩子,向仙人求食,仙人的手指指向那里,那里便有吃不完的東西。最后仙人問窮孩子:‘滿足了么,你還要什么東西?’這窮孩子說:‘我要你的手指頭。’劉士林有點像這個窮孩子,他要的是康德的‘手指頭’(先驗方法論)。”當時,我只是覺得這個比喻很有趣。而今看來,如果說我曾得到過“仙人”的“金手指”,那也必須補充說:先生就是“仙人”,“金手指”就是他的“形式美學”。
在當代中國美學研究中,幾乎可以把每家每派都追溯到馬克思的“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這一偉大命題,它不僅揭示了人類在歷史中一切生命活動的實踐機制,也深刻解釋了人類的精神現象、文化現象和審美現象發生演化的基本原理。勞承萬先生把“美的規律”劃分為廣義上人化自然的“大律”和藝術生產的“分律”,前者是包含著知識、倫理、審美內涵的“人的本質”的根源,后者才是剔除了知識和倫理內容的“美的本質”。總體上說,正是有了“美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形式化”這個命題,才為美學研究建立了更純粹的邏輯起點和更為根本性的理論命題,同時為開展一種真正獨立于哲學和倫理學的美學研究提供了可能。先生的美學不是一般的藝術哲學或純粹美學,在本質上仍是一種哲學美學理論。在美學方面,先生最重要的貢獻是提出了“美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形式化”,以“審美主觀形式”為建立與知識學、倫理學、實踐哲學等相區別的美學理論奠定了一塊重要基石。在哲學方面,先生又不同于席勒的“審美外觀”理論或二十世紀的藝術哲學,而是在邏輯上具有聯系“真”和“善”、“科學”與“倫理學”,在實踐中具有溝通“自然”和“社會”、連通“工具理性”和“實踐理性”的橋梁功能,它們有機聯系并不斷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力量和更廣闊的實踐功能的“三元結構”。
我對先生“三元結構”最膽大妄為、不計后果的運用,是在城市研究和規劃領域中的運用。一個是“高處不勝寒”的先驗哲學,一個是“喧嘩與騷動”的人間煙火。在一般人看來,這兩者必然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但借助先生的“金手指”,我驚奇地發現,城市研究同樣要遵循“三元結構”的原理和規律。當年我在《澄明美學:非主流之觀察》后記中曾寫道:“我最初從事美學思考時,也曾一度深深地陷入十分危險的美學迷途中,直到1993年到勞先生身邊,并經歷了他的邏輯洗禮之后,我才開始了自己十分寶貴的美學覺悟過程。而且,在我建構與闡釋我的美學理論過程中,勞承萬先生的美學研究,也為我提供了極為豐厚的邏輯資源。”實踐證明,這種我稱之為邏輯洗禮和美學覺悟的經驗,盡管始于美學,但由于本質上是思維方式的轉變,即從理性的、倫理的獨斷論走向了同時從真、善、美三個角度來認識自我、分析對象、看待世界,因此其用途遠遠超越了學術和理論研究,走向了更為悠久的歷史世界、更為廣闊的現實世界,甚至其思想的鋒芒還指向了遙不可及的未來世界。
在建設性意義上,我們認為,在西方由康德原創、在中國由勞承萬重構的“三元結構”,“源于主體的知識、道德和情感三大生命機能,對應于人類的物質、社會和精神三大活動領域,與以人工智能定義未來生命相比,兼容了人的道德和情感需要,包容了生命的生物本能和文化基因,不僅是認識人類自身的科學和系統思維,也為研究和探索未來城市提供了基本理論和方法。進一步說,無論未來人類在思想意識、科學技術、文化道德上如何變化,但在一定要符合真善美的原則以及一定要滿足人類物質生活、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上,則是永恒不變的”。由此,我們為未來城市建立了一個內在邏輯清晰、層次布局分明、內涵豐富完整的定義和原理,未來城市是以“真-未來產業-新型經濟城市”“善-未來社會-新型政治城市”“美-未來文化-新型人文城市”為基本原理和實踐機制的城市發展理念和模式。由此可知,具有深厚邏輯、寬闊結構和有機聯系的康德哲學,也是真正的未來哲學。以“真-善-美”為內在結構的城市的基本原理和主體框架,不僅解釋了歷史上的城市,也打開了未來城市之門。
2024年元旦的次日,先生發來微信說:“今天上午我發現上海文藝出版社退給我的《審美中介論》的手寫稿大約有二十多斤重,可見我當年付出的大量心血!你有機會可以來參觀一下,你會感嘆搖頭!當今的人無法相信,無法想象!連我自己都不相信是我親手寫的一大原始景觀。”當時我發熱到三十七點五攝氏度,起來吃了一片退熱藥,只回復了先生四朵小紅花。《審美中介論》手稿為什么會有二十多斤重,因為它最初是上中下三卷,當時出版的《審美中介論》只是上卷,中、下卷后以《審美的文化選擇》為名合并出版。再后來出的修訂版,則是《審美中介論》和《審美的文化選擇》的精編版。盡管出版過程十分曲折,但已搭建起“三元結構”的主體框架。孔子曾說過“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在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偉大而寂寞的人物,因為各種原因而被遮蔽起來。如果在當代也開列一個學術逸民的名單,我想勞承萬先生無論如何是要入選的。從當代學術文化的總結和保護傳承而言,我衷心希望,年輕一代的學者要多關注勞承萬先生這樣的真學者,使每一種重要的當代學術都有傳承人,這對于繁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推動中國話語和中國理論更好地走向世界,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