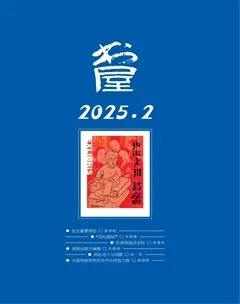讀《延安典故》,有所思
一
用文學表現延安時代,從延安時代已經開始。“好將一點紅爐雪,散作人間照夜燈。”延安時代的許多作品照亮了前行的路,已成為不朽的經典。《延安典故》既是對歷史的致敬,又是“我心寫我口”的文學書寫,是在感恩與反芻中繼往開來。公木詩曰:“你把一代的精神,賦以活的呼吸,吹向來世。”掩卷沉思,誠惶誠恐:我做到了嗎?
二
“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延河、寶塔、窯洞……這些延安的標志性符號,既老又新,歷久彌新。創新是文藝的生命。《延安窯洞是如何打成的?》《延河:流水十四章》《〈為人民服務〉是如何成為傳世名著的?》等,對歷史進行還原與再現,從老故事中看出新神韻,在老現場發現新故事,把過去時態的空間呈現于當下,希望在新的視角新的敘事中見事見人見真諦。
三
沉浸于延安時代,感受到革命年代的純真、激情與詩意,乃至冷冽。內心感動,靈感涌現,為歷史補筆。造境摹寫現實,寫境鄰于理想,深化延安故事的意蘊。《小米的宗旨》《馬,毛澤東打天下的馬》《張思德與〈為人民服務〉》等,開拓新的故事入口,擦拭那些蒙塵的詞語與往事,讓情節化的敘事引領我貼近延安時代的血脈與心跳。
四
細節!細節就是歷史,細節就是力量。稽考鉤沉碎片化文獻,下功夫搜集細節,珍惜細節,乃至一些人眼中無足輕重的枝葉。注重細部的畢現,目光在細微部停留,防止在宏觀敘事中把一個偉大的時代寫“空”寫“窄”。《中共七大歷史現場》《那斧鑿進文化江山的延安往事啊……》等,大歷史與小細節互映,讓人既看見政治大氣象,又看見窯洞的人間煙火,這些篇章在《美文》《北京文學》《中國青年報》等報刊刊載后,一些朋友對我說,從中看到了過去沒有見過的細節,政治的細節、會議的細節、人的細節,有一種閱讀的親切與喜悅。
五
文學之美,美在文采。無有文采,何談文學。中國山水間常常建立一座空亭,群山郁蒼,草木薈蔚,空亭翼然,吐納云氣。蘇東坡說:“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我期望《延安典故》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向山水間的亭子學習——“江山無限景,都聚一亭中”。
六
《延安典故》追求文學性和故事性。《馬,毛澤東打天下的馬》《小米的宗旨》等,將點狀敘事與線狀敘事結合起來;《哲學的窯洞,哲學的延安》將一個個哲學問題放置于窯洞、延河等場景之中,轉虛為實,穿越時空,面對面地傾聽哲人對話。我試圖找到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之間的秘密通道,寫出親歷其境的現場感,讓文字散發出歷史與文學的雙重魅力,探索間,吾惶惶然。
七
故事的入口即是思想的入口。用文學書寫大時代大事件,必須進入思想的內核,亦須警惕“黨八股”。毛澤東反復批評的“黨八股”中,看不見自然,看不見日常,看不見真誠,看不見屬于人的樸素表情,既缺乏思想的光,也缺乏文學的光,只在那里高蹈大詞,流于空談與表態,淪為文字游戲,辜負了文質彬彬的偉大傳統。寫《延安典故》,擬讓政治與文學互滲互喻。搦管揮寫處,我感到自身的膚淺,內心有一種慚愧與辜負。
八所思
“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郁郁黃花,無非般若。”鶯飛草長,在文學的修煉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