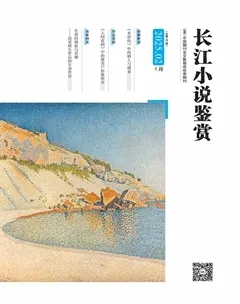《水滸傳》中的酒人與酒事
[摘 "要] 《水滸傳》文本與酒文化強關聯,小說中對飲酒的描寫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與情節發展的設計。可以說,《水滸傳》的許多情節都建立在個性鮮明的酒人和曲折生動的酒事上。酒意象于人物形象來說是一種使得人物性格鮮明的輔助和媒介。酒意象或使人產生情感錯位,或使人暴露深層心理。在情節發展中,酒既有聯系人物的作用,又能另起事端,使情節發生突轉,變得跌宕起伏。金圣嘆點評酒描寫乃《水滸傳》必不可少的點睛之筆,本文將結合金圣嘆的點評,分析闡釋《水滸傳》中的酒人與酒事。
[關鍵詞] 《水滸傳》 "酒人 "酒事 "飲酒描寫 "金圣嘆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2-0003-04
《水滸傳》中關于酒的描寫數不勝數,僅金批《水滸傳》就有三百多處寫到酒。小說中不僅有酒人、酒物、酒事,還有酒文、酒器、酒肆、酒具等。金圣嘆評書亦不忘論酒,他在第二十八回中說:“飲酒,其珠玉錦繡之心也”“千載第一酒人”“千載第一酒場”“千載第一酒時”“千載第一酒懷”“千載第一酒風”等[1]。浩浩蕩蕩一段“酒評”,可見酒描寫對于《水滸傳》的重要性。在這么多與酒相關的描寫中,酒人與酒事是書中最突出的部分。
一、酒人
金圣嘆盛贊《水滸傳》:“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1]《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位人物各具特色,但有一個共同喜好:無酒不歡。水滸英雄齊聚梁山,共同理想之一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漢的酒量與武力成正比,不論是武松還是魯智深,都是一碗酒一分本事,十碗酒十分本事,越醉越有本事。好漢們可以無肉不能無酒,行者與花和尚都是先喝下十來碗酒才要肉食。好漢的命運也與酒息息相關:楊志因酒失了生辰綱討不了好出身;李逵因毒酒喪了性命;林沖因酒獲生又因酒受困。即使是拒絕飲酒的青眼虎李云,他的命運轉折點也是半盞酒。總之,書中人人飲酒,處處有酒,人與事都離不開酒。連“打醬油”的人物鄆哥、唐牛兒、李吉、虔婆等都會喝酒。作者不僅在寫水滸“好漢”,還從審美角度寫水滸“酒漢”。作者在事件中塑造酒漢形象,以重大事件為情境,以酒為媒,使人物脫離常規,暴露深層心態,或形成情感錯位[2]。
1.醉漢失言
酒有麻痹神經之效。飲酒之人若貪杯,精神就會進入非理性狀態,言語行為一反常態,進而暴露自己的潛意識,酒后吐露真言。第三十九回中,作者設法讓宋江酒后疏狂,題下反詩,使得宋江暴露城府,顛覆了舊有形象。
縱觀全書,宋江是一個比較完美的人物,既講忠義,又有出眾的能力。作者多角度表現宋江在“忠孝義”層面獲得的聲名:體制內,是同事喜歡上司偏愛的宋押司;在家中,是孝順父親的“孝義黑三郎”;在江湖上,“及時雨宋江”的名號無人不知。《水滸傳》第二十二回,虔婆當街高呼宋押司殺人,無人肯信,原文寫道:“原來宋江為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可見其有過人的交際本事,擅長籠絡人心。第二十三回,公人礙于宋江的面子不抓他,同事朱仝幫宋江逃避追捕,知縣也不相信宋江會殺人,說明宋江在官場左右逢源。對于宋江的才智與領導能力,作者不吝描寫:宋江三次攻打祝家莊都善用策略、指揮得當,有極佳的領導能力;做鄆城小吏時,不論黑白兩道,宋江都能交往;作為領袖,對愿上梁山者,宋江都能以禮相待,并妥善安排好兄弟之間的位次關系。
然而,太過完美的人物會顯得“臉譜化”、不真實。金圣嘆稱,一百零八傳,《宋江傳》最難讀[1],因為宋江“假”。第三十九回就是將“完美”的人物宋江打入極端情境,以酒刺激這個“假人”,再通過醉題反詩的描寫,暴露出宋江不為人知的一面。
《西江月》
自幼曾攻經史,
長成亦有權謀。
恰如猛虎臥荒丘,
潛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雙頰,
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報冤仇 ,
血染潯陽江口![1]
金圣嘆從醉題反詩切入,將“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一句看作《宋江傳》提綱挈領之句,認為宋江乃善用權術之人[1],由此詩可以一窺宋江心緒:第一,自幼受儒家思想浸染,心懷士大夫理想,諳熟權謀之術。第二,學吏出身,雖能力出眾,但難以在官場晉升,一直等待時機。第三,救助閻婆惜后被刺配江州,地位一落千丈,心中十分不甘心。第四,早晚要找回公平,發泄心中不甘。
宋江素日言行完美,酒后卻自白有權謀與野心,感嘆自己境遇不如人,流露出宋江隱藏的深層情緒,有自視甚高與憤懣不平的一面。其已然醉到吐露不滿,再喝數杯后卻不忘給賞銀,證明宋江已將籠絡之道用得出神入化。再結合宋江所做的矛盾之事:義釋晁蓋;計賺秦明,殺其全家;游說徐寧等人落草,共同壯大梁山;不顧弟兄利益接受招安;為免李逵造反騙他飲毒酒等。與宋江潯陽樓上酒后言行一致。
金圣嘆不喜城府極深、玩弄權術之人,故稱宋江為“全劣”。“然吾又謂由全好之宋江而讀至于全劣也猶易,由全劣之宋江而寫至于全好也實難。”[1]作者對于宋江的刻畫是極其成功的。其中,又以潯陽樓的醉后描寫最為出彩。
2.酒漢打虎
第二十三回中,自飲酒到遇虎,武松的心理形成多次情感錯位:武松連喝三碗酒,店家稱“三碗不過崗”,不再上酒。武松不屑,連喝許多碗后,發惱讓店家再添酒,情緒十分狂傲。喝完十八碗后,武松并未倒下,自如走出店門,心里更加得意。店家提醒他,景陽岡上有虎,已害死二三十條人命,現在正是危險時段,且住一晚再走。武松不信,夸下海口,走了一段路后,發現樹干上寫著警告語,武松依舊不信,認為是店家詭詐。再往前走,一座山神廟門上貼著“有虎”的印信榜文,他這才相信真的有虎。此時武松的心理第一次錯位,他覺得害怕想要轉身回去,轉念卻想,回去沒面子,于是他自我安慰,硬著頭皮繼續走,這是第二次錯位。走著走著,日色西沉,沒有看見老虎影子,他產生第三次心理錯位,認為并無什么老虎,唬人而已。但林子黑壓壓的,他心里未免恐懼,這是第四次心理錯位。武松趕忙踉蹌沖過亂樹林,緊接著看見一塊大青石頭,又放松警惕,形成第五次錯位。他正躺下要睡,背后亂響,老虎跳了出來,武松驚恐大叫,看老虎朝他撲來,酒瞬間嚇得化作冷汗,此為第六次錯位。
從知道有虎開始,武松每走一段路,心理活動就發生變化,一共產生六次心理錯位。這里展現出打虎英雄作為平凡人的復雜的情感狀態。學者孫紹振指出,文學作品提供了一種藝術假定狀態,使武松遇虎且不被老虎吃掉,以此為前提,來刻畫他過崗打虎的心理動態[2]。過崗與打虎時的情境固然是造成武松心理錯位的主要原因,但是,打虎前的飲酒積蓄了情感勢能,促成之后情感錯位的強度。作者特意詳細描寫武松豪飲的過程:武松喝到第幾碗了,又吃了多少肉食,武松如何與店家斗嘴叫他上酒,在言行中透露酒狂的得意本色等。作者寫武松豪飲十八碗的過程時,除了要寫十八碗本身,還要在酒家與武松的一來一往中,以反襯法生動刻畫出武松遠超常人的能、傲、狂。若沒有“三碗不過崗”的預警,若不是武松性傲好飲,十八碗酒期間的言語拉扯就無從寫起。飲酒篇幅寫得愈是生動,愈能透出景陽岡大蟲之險,襯出武松的狂傲。飲酒時“我卻吃了三碗,如何不醉”“要你扶,不算好漢”“我卻又不曾醉”“卻不說‘三碗不過岡’”,言語間自得無比。過崗途中又“一步一驚嚇”“欲待轉身再回酒店”“十八碗酒化作‘十八碗冷汗’”。武松心理的前后錯位,源自情境的變化。而前后錯位之大,在于老虎的危險性,更在于武松的自傲與后來的驚恐之間的反差。
3.醉和尚鬧酒
《水滸傳》第四回,在情節上本可以“魯智深因醉酒大鬧五臺山,被打發到東京相國寺”一句帶過,作者卻詳細描寫了魯智深如何酒癮難耐,如何設法飲酒,又如何兩番因酒鬧事。此節描寫于情節上用處不大,但對于刻畫人物形象卻大有必要。
金圣嘆評:“寫魯達為人處,一片熱血直噴出來,令人讀之深愧虛生世上,不曾為人出力。”[1]魯智深武力高強,是生命力的體現。作者將習慣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自由自在的魯智深安置在滿是禁欲氛圍的寺廟內,使其在極端壓抑的環境中“飲酒醉鬧”,形成言行錯位,表現出魯智深身上不可壓制的生命力。原先做提轄時,魯智深滿身熱血、行俠仗義,來到五臺山卻顯得格格不入,滿身的功夫與沖勁無處安放,化作極強的破壞力。“醉鬧山門”的描寫極力表現了魯智深的破壞欲:甩膀子折斷亭柱,打倒臺基上的金剛,徒手敵對數百人,直打到法堂下。弗洛認為:“生命欲受阻越嚴重,破壞欲就越強烈;生命越得到實現,破壞欲就越小。破壞欲是生命未能得到實現的后果。”[3]佛門戒律森嚴,粗魯性急的魯智深在這里需要“入鄉隨俗”“久靜不動”。雖然一開始他便不守規矩,在禪房內酣睡,在佛殿后撒屎尿,但其最本質的生命力沒有得到抒發。在酒的觸發下,魯智深才可以一反之前的“不合時宜”,迸發出最原始的生命活力。
除了上述言行錯位外,還有醉鬧時,三方勢力的情感錯位。醉鬧山門時,魯智深、僧眾、長老的情感狀態如下:
站在魯智深的角度:喝醉回寺睡覺,何錯之有?你們要打我,我就打你們。還得讓長老做主。從智深醉罵金剛的話中可以看出,平日里他受到嘲笑和排擠:“你個鳥大漢,也咧開嘴來笑灑家。”“你個鳥大漢不幫敲門,卻拿著拳頭嚇灑家”。
站在僧眾的角度:看不慣魯智深,又嫉妒長老對魯智深的偏愛與看重,趁他喝醉犯戒趕他走。如“好個沒分曉的長老”“你快下山去,饒你幾篾子”“智深好無禮”“長老說道他后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
站在長老的角度:看重魯智深的潛力,能袒護就袒護,第一次醉鬧,魯智深“不受上罰,反受上賞”。“你看我面,且去睡了,明日卻說。”“休要惹他,你們自去。”“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
僧眾本不該管卻多管閑事,長老應該管但偏袒護縱容,魯智深不講規矩還委屈告狀。在多元錯位關系下,魯智深在長老的袒護下,由無理方變成占理方。
醉鬧過程中最有趣的錯位是魯智深自身的錯位,喝酒犯戒、醉鬧山門不對,他卻覺得自己有道理還告別人狀。前文作者剛寫魯智深拳打僧眾、毀壞金剛、呵佛罵祖,后文卻筆鋒一轉,魯智深看見長老,酒已醒了七八分,馬上委屈求助道:“長老,與灑家做主。”魯智深看似長相兇悍、言行粗魯,破壞力極強,卻也有孩童心性。在外是別人的保護者,在長老身邊卻是被保護者,能夠袒露脆弱的一面,這樣的錯位使魯智深的形象顯得可愛、俏皮。
二、酒事
酒不僅對單個人物產生具體影響,還能將紛繁復雜的人物關系、千頭萬緒的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酒不但能夠推動情節發展,還能使情節跌宕起伏,充滿曲折變幻。《水滸傳》中有大大小小的飲酒描寫,在情節中的表現方式大致可以分為飲酒生事、以酒綴事、以酒謀事等。當然,酒描寫對于非情節部分也有影響,比如第九回,洪教頭急著和林沖比試,柴進卻說先飲酒,等月頭上來了再比。第四回,作者特地在兩次醉鬧之間加一段看似勸誡酒徒的警語,實則是將其作為閑筆來阻隔兩段醉鬧描寫,有舒緩敘事節奏之用。下面本文主要就“以酒綴事”與“飲酒生事”進行闡述。
1.以酒綴事
以酒綴事就是通過酒來連綴情節。金圣嘆認為情節應當具有完整性,要“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再“重收到青萍之末”[1]。他提出以一個物件或者非物件貫穿情節始末,形成線索,這種技法叫“草蛇灰線”[1]。酒不僅藏身在《水滸傳》的大量情節之中,還貫穿于全書。
第十回中,除了風、雪、火之外,作為非自然元素的酒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覷。如同武松的“哨棒”、紫石街的“簾子”,酒在這里也是條一拽就動的“草蛇灰線”,在情節的變化中,林沖的命運線也隨著酒波瀾起伏。林沖被調草料場途中,天寒地凍,想吃酒卻買不到。到了草廳,老軍送他酒葫蘆,并告知他何處可買酒。酒在此處為林沖的命運與后文的情節走向埋下伏筆。林沖去買酒,店家認得酒葫蘆便留他店中小酌。正因在此飲酒,林沖才不至于遭遇“雪重屋塌”的天災,間接躲過陸虞候人為制造的“火禍”。因酒,人物的生死命運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復仇后逃跑途中,林沖因搶酒引發事端,后又喝醉倒在雪地中。后路既斷,前有新禍,人物卻因酒醉陷入徹底被動的狀態。
第二回中,作者設置了三次酒宴,以這三場酒宴為線索,人物關系由對立面變為統一。捉盜酒:史進聽聞少華山新來三個強盜,專門打家劫舍,攪擾村民,為了保護村莊,設宴與莊戶共商捉盜之事。釋嫌酒:史進捉到陳達后,朱武、楊春使苦肉計來救陳達,朱楊二人與史進互相試探,最后以酒宴釋嫌,并產生友誼;友誼酒:史進再設中秋酒宴款待三人,被官兵圍捕,史進一把火燒了史家莊。
2.飲酒生事
《水滸傳》中常有好漢飲酒引發一些事情。有時,飲酒生事是為“逼”好漢上梁山。比如宋江在潯陽樓倚闌飲酒,醉后狂書反詩,遭黃文炳舉報后被判死刑,后上梁山。林沖雪夜欲上梁山,醉后題詩恰被朱貴看到,于是順理成章上了梁山。有時候飲酒生事是為了引出其他人物,如武松不滿自己的酒食不如孔亮,對店主和孔亮大打出手,而后引出宋江出場。有時候飲酒是醉漢發泄,如魯智深飲酒后兩番醉鬧五臺山等。
在這些情節中,最精彩的當數楊志因酒失生辰綱。第十六回中,楊志等人因為飲酒醉倒,被吳用劫了生辰綱。作者兩度描寫天熱難當。又寫楊志如何鞭打軍健,逼迫他們前行,軍健不滿不愿再動,老都管也冷嘲熱諷楊志。雙方矛盾的激化與不合時宜的天氣為后文楊志買酒做了鋪墊。吳用七人裝作賣棗販子,白勝化裝成酒夫挑著兩桶酒。七人先是向白勝買了一桶,眾軍健看見也要買,楊志不肯。為解楊志疑心,劉唐故意在另一桶里兜了半瓢酒,楊志看劉唐喝了酒無事,于是不再疑心,和軍健一起喝酒解渴。喝著喝著卻越發無力,楊志一行人眼看生辰綱被劫走。楊志一路謹慎,軍健一路辛勞,卻因一桶酒失了前程。因為這桶酒,情節變得撲朔迷離,十分具有戲劇性。
三、結語
《三國演義》有青梅煮酒論英雄,《水滸傳》里則是不喝酒者非好漢。酒人無酒則失去靈魂,酒事無酒便無情節發生的可能,酒文無酒則難以成文。酒可謂是《水滸傳》的文眼,撐起了人物性格,勾勒出人物群像,指明了事件發展。酒不僅貫穿人物一生,更貫穿文本之中,使《水滸傳》的情節更加生動。酒文化不僅影響了《水滸傳》的書寫,也不斷影響著后世的文學發展。
參考文獻
[1] 施耐庵.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M].金圣嘆,評點.文子生,校點.河南:中州古籍出版,1985.
[2] 孫紹振.審美閱讀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 弗洛姆.逃避自由[M].劉林海,譯.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