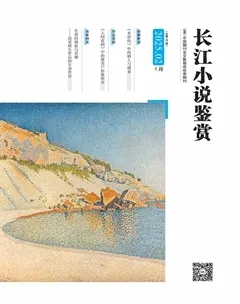亞里士多德悲劇理論視域下的《邊城》
[摘 "要] 《邊城》是沈從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貫穿他創作的“美麗總令人憂愁”的悲美思想在此充分而深刻地體現出來。故事發生在一個充滿善與美的世外桃源,然而情節于中途急轉直下,導向死亡氣息濃厚的悲劇結局。本文嘗試以亞里士多德悲劇理論出發,從“情節的整一性”“錯誤”“突轉與發現”“憐憫與恐懼”幾方面切入,分析《邊城》的情節設置、人物塑造及悲劇效果,探究沈從文如何描繪命運必然性下的人的存在及傳達他對人性美的堅守與追求。
[關鍵詞] 沈從文 "《邊城》 "亞里士多德 "悲劇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2-0015-06
一、情節的整一性
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是對一個完整劃一且具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悲劇的情節應該是完整的。他說:“所謂‘完整’,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所謂‘頭’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發生者;所謂‘尾’,恰與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規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無他事繼其后;所謂‘身’指事之承前啟后者。所以結構完美的布局不能隨便起訖,而必須遵照此處所說的方式。”[1]而情節的整一性不僅要求情節沒有遺缺,還要求沒有與整體無關的多余部分。
《邊城》在情節上體現出了整一性的精神。故事圍繞著少女翠翠的愛情展開:翠翠與祖父看守渡船,相依為命。天保、儺送兩兄弟同時追求翠翠,實際翠翠早已心向儺送。哥哥天保派人上門提親,然而沒能得到回應,又在得知弟弟的心意后自覺競爭無望,隨船下行,弟弟儺送因此也停止了對翠翠的追求。天保溺水而死,儺送與父親對翠翠和先前遲遲不能給出明白答復的老船夫不免心生嫌隙,依然嘗試促成孫女好事的老船夫在兩人處都碰了釘子,儺送父親有意讓儺送另娶,儺送負氣出走,受到打擊的老船夫在一個夜里死去,留下翠翠一個人孤單等待儺送歸來。
《邊城》中構成悲劇的情節不存在遺缺,在翠翠與儺送沒能相見的兩年間,作者敘述了翠翠對儺送的感情,即沒有與整體無關的多余部分。本節重點論述《邊城》如何符合了亞里士多德悲劇視域下的“必然律或常規自然”。
亞里士多德認為:“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1]完整的悲劇絕不是按照時間和空間上的切近編排情節,而是在對事物自然發展的洞察基礎上組織它們,也就是說,創作者必須對因果的運作有著深刻理解,才能說掌握了寫作悲劇的技巧。《邊城》情節的轉折點是天保溺死,正是這場意外毀掉了所有人的幸福,到這里疑問自然出現,既然是意外,怎能反映出必然呢?有關悲劇的成因,沈從文曾說:“一切充滿了善,充滿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良善與單純的希望終難免產生悲劇。”[2]這里的“不湊巧”需放置在古希臘命運觀的語境下理解方見其妙,亞里士多德認為,因果性就是命運之表現,其客觀、莊嚴不言而喻。《邊城》中,翠翠的命運是預先注定的,悲劇不過是對命運的解蔽,善水的天保溺死,他的死又改變了翠翠的命運,這是命運組合事件的方式。
《邊城》第一節就交代了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這是祖孫二人相依為命的原因,也是他們人生的陰影。命運在這時就早早進入了讀者的視野。古希臘的悲劇詩人害怕觀眾忽略命運的力量,喜歡在情節上做這種安排,例如在俄狄浦斯的遭遇中,其殺父娶母的命運早早就在德爾菲的神諭中出現,后面無論俄狄浦斯的父母和他自己采取什么行動都是徒勞的。
翠翠的命運繼承自她母親,一方面是翠翠父親堅守軍人的職責,另一方面是翠翠母親無法割舍親情,兩種矛盾導致了她母親的悲劇。有研究者認為這反映了當地不許苗漢通婚的習俗,但無論怎樣,按照近代人的理解,翠翠沒道理必須遭遇相似的不幸,若能改變策略、正確抉擇,結果就會不同,所以不幸應由她自己負責。實際上這種看法是對命運的輕視和對人的能動性的自負,而《邊城》中的命運表現為一種不可操縱的必然。就像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舉的阿爾克邁恩、俄狄浦斯、俄瑞斯忒斯、墨勒阿格羅斯、提厄斯忒斯等悲劇素材那樣,命運以強力組合起遙遠孤立的事件,人不但無法逃脫,而且越掙扎越會接近令人恐懼的結果。《邊城》中,翠翠初次含糊地對祖父表露心事時,老船夫突然間從歡笑的氛圍中出離,“仿佛看到了另外一種什么東西, 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這時他還不能說清自己所察覺到的,然而預感一次又一次出現,他終于意識到翠翠“一切全像那個母親”,母女二人的命運自然是相同的,她的愛情將與死亡相伴。老船夫試圖擺脫命運的輪回,他“不能完全同意這種不幸的安排”,想竭力盡到自己的責任,讓翠翠有個幸福的結果,可一切努力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因為重視翠翠的想法,遲遲沒有答復天保的提親,致使天保直面弟弟儺送的競爭,失敗灰心之際落水溺亡;屢次打探儺送心意,然而關心則亂,言語失當,遭到誤解;每每尋到時機撮合翠翠與儺送相見,卻總是因為翠翠的無意或故意失去機會,就在這種一連串的不可抗拒的誤會與差錯中,翠翠走向了和母親一樣的悲劇。
二、悲劇人物塑造
本節以亞里士多德關于“錯誤”,即“hamartia”的論說分析《邊城》中的人物塑造。亞里士多德認為,高貴之人因為自身的hamartia陷入厄運,導致單一的苦難結局。Hamartia絕不是罪惡,而是某種過失與弱點。
Hamartia有未擊中、錯失的意思,即沒有切中預計的目標。從行動上講是這個人的行動并沒有合乎其本意,這包括無意的失誤和有意的犯錯(或近代道德觀上的犯罪),從品格上來講,就是一個人的品質有瑕疵,在亞里士多德的語境里,就是未能發展成“其所以是的是”[3]的那個樣子。
趙振羽將hamartia翻譯為罅隙[4],這種譯法形象地顯示出命運是如何滲入一個人的生活的。若這個人是完全的好人,他身上就沒有空間讓命運顯現。讓這種好人轉入逆境只會引起讀者反感,因為這近似于割裂了命運與人的行為的聯系,這樣的悲劇不但不能表現因果性,反而給人荒誕之感。
《邊城》中人物大多善良淳樸,有意的犯錯較少,不過若是將約定俗成的習俗視為規范,也有人物故意違背這種規范行動,從而推動悲劇情節發展的,例如《邊城》的世界中,戀愛是年輕人的事,向來是講求自由的,船總順順卻將天保的死歸咎于翠翠,主張讓儺送另娶。至于另兩方面即“行動的失誤”和“性格瑕疵”都比較容易發現,比如老船夫關心則亂,天保剛去世就去打探儺送的口風,這屬于行動錯失了目的;儺送將哥哥天保的死歸罪于老船夫的拖延,為此抗拒對方的試探,這就體現出他在性格上的不夠豁達。然而主人公翠翠的情況比較復雜,她的形象是天真純潔、秀美靈動的少女,身上體現了上述兩種類型的hamartia:翠翠因羞澀或恐懼,沒有見儺送,前后兩次錯過機會,使儺送沒能看到兩人感情的希望,最終選擇出走;相比天保,她明顯更加傾心儺送,卻不愿表示出來,反而抗拒祖父的關切與詢問,這似乎說明她缺乏主宰自己命運的勇氣。問題在于,若說翠翠的行動錯失目的,但她其實并不清楚自己的目的為何。她不懂愛情,不理解心中的悸動,她清楚認識到的需求就只有祖父的陪伴。若說因她性格的瑕疵造成了悲劇,作者卻贊揚她的性格,言語中體現出對她的愛惜,稍有對其缺陷的表述,如翠翠因為文化教育的缺失,不懂得如何用文字或藝術表達自我,作者也要在這里添上一句“這不是人生罪過”,為她開脫。如果在行動中尋找其瑕疵,又會發現翠翠的行動對事件的因果聯系起作用的方式是間接的、不露痕跡的,反而最積極的行動者、以一連串失誤使命運實現的是老船夫,并不是翠翠,翠翠自己的行動更多地顯示出一個天真純潔少女的可憐可愛的性情。這樣看來,她的hamartia是不明晰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目的不在于模仿人的品質,而在于模仿某個行動,劇中人物的品質是由他們的性格決定的,而他們的幸福與不幸應取決于他們的行動,他們不是為了表現性格才行動,而是在行動的時候附帶表現性格”[1]。沈從文對翠翠的性格描述與情節的設置表現出對這條原則的突破,在翠翠身上,可以見到沈從文描繪美的沖動如何勝過了對悲劇效果的追求。
亞里士多德認為,性格是一種潛能,只有在行動中才能成為現實。沈從文用大量筆墨描述翠翠的性格和所思所想,不安排她以行動直接造成悲劇的結果,這是一種讓她性格上的瑕疵免于成為現實的努力。
《邊城》寄托了沈從文改造民族性和重塑道德的愿望,他要展示一種自然純正的人性,尤其渴望照見城市知識分子的墮落處,特別是那些不幸地被知識扭曲的方面。這也就是為什么他不愿讓天真純潔的翠翠顯得無知。她與老船夫、儺送等人不同,雖然邊城世界中的“現實”是人人性格向善,但她處在變成這種“有瑕疵的善”以前的狀態。這樣的翠翠稱不上具有美德,但絕對與罪惡無關;雖非本真,卻也沒有沉淪,少女為一種虛幻的美感所籠罩,不過這種美極其脆弱,難以長久,必須依靠翠翠的“無知”維持。
即使在人人淳樸的邊城世界中,翠翠也比誰都無知于某些“常理”:唱的歌明明涉及男女求愛之事,卻不能定義她心中的感情;她不懂怎樣從自己這一邊促成姻緣,面對追求也沒有打定主意;她覺得陪伴爺爺、擺弄渡船就很好,既不清楚愛情于她的意義為何,也不知道真正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是什么,為此她感到空虛寂寞,卻又無可奈何。這份無知確實給她帶來一些不適,但少女其實并沒有因為它而“犯了大錯誤”,這樣看來,好像是命運粗魯地介入了她的生活。但是,如果我們想一想亞里士多德“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3]的著名論斷,就會明白翠翠那種自然精靈般的生存方式雖然展現出令人神往的美感,但顯然缺乏對理智的自覺運用,實際與理想的美德不合,便是其命運的罅隙所在。導致悲劇的hamartia和翠翠的高貴之處同源,從結果上看,這種安排既讓命運的滲入有據可依,也讓翠翠所承載的那份人性美得以保持在作者理想的高度之上。
三、“突轉”與“發現”
亞里士多德在討論悲劇情節時指出了悲劇情節的三個成分。他說:“‘突轉’與‘發現’是情節的兩個成分,它的第三個成分是‘苦難’。”[1]其中“突轉”和“發現”比較重要,亞里士多德推崇的復雜劇就是僅由“突轉”和“發現”構成的。
亞里士多德認為:“‘突轉’指行動按照我們所說的原則轉向相反的方面,這種‘突轉’,而且如我們所說,是按照我們剛才說的方式,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發生的。”“‘發現’,如字義所表示,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使那些處于順境或逆境的人物發現他們和對方有親屬關系或仇敵關系。”[1]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發現”是一個從不知到知的解蔽,它和“突轉”都是一種“轉變”。因此亞里士多德又說:“‘發現’如與‘突轉’同時出現,如《俄狄浦斯王》劇中的發現,為最好的‘發現’。”[1]
簡單來說,“突轉”就是人物在順境和逆境中間的轉變,事件的組織要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則,《邊城》情節整體上轉入逆境的標志是天保的死。天保派人上門提親沒能得到回應,又在得知弟弟的心意后自覺競爭無望,隨船下行,而同船伙伴說“這幾天他都不說話”,可見他正因失戀而心碎,而小說中幾次提及下游河道有幾處水兇浪急,儺送的船先前就出過事,輪到天保的船撞上石頭進了水,形勢本就十分危險,心中有事的天保溺水而死,就是可能發生的事。
同時,天保之死也是翠翠的命運使然,翠翠的命運并沒有像神諭那樣具體,沒有理由認為她的不幸一定表現為愛她的人的死亡,但聯系翠翠母親的悲劇,也就不讓人意外了。其中因果仿佛沒有道理可講,可見命運何其盲目!但盲目性也是必然性,如果命運可以為人的知性理解,那么就成為喜劇式的因果報應了,只有讓遙遠而互相孤立的東西整合起來,才能見出必然性的力量。
老船夫進城是為了打探第二個夜里示愛的歌聲為何消失,他為了翠翠的幸福而行動,卻探聽到天保已死,在見過船總順順和儺送以后,他意識到原本可能結成親家的兩家人的關系變得疏遠,而且對方把天保的死歸咎于自己和翠翠,先前的愛在此轉為了恨。老船夫又把發生之事與自己的解讀告訴給翠翠,翠翠雖然不太明白,卻隱約感到自己已經落入逆境,心中極亂地哭了起來。
“突轉”和“發現”同時發生在老船夫對翠翠說出那一番話時,其中包含天保溺死的信息,還有儺送一家已經怪罪上祖孫兩人的事,但翠翠在這里的發現并不是完全的,她只是發覺自己莫名其妙地要為一件沉重的事負責,她不能想象這結果是由自己某時某地的行動引發的,也意識不到自身hamartia的存在,她并沒有真的從無知轉變為知道。在亞里士多德論證“突轉”和“發現”同時發生的典范《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對自己殺父娶母的命運的“發現”是分層遞進的:王后伊俄卡斯忒的說明只是讓俄狄浦斯了解到是自己殺了前國王拉伊俄斯,還不愿意相信兩人是父子關系,直到派出調查的人回來報信,他才知道自己正是拉伊俄斯棄養的親生兒子,命運終于向他顯現。翠翠的命運在最后楊馬兵對她解釋清楚一切時迎來了進一步的解蔽,但即使在這時,翠翠是否在主觀上認識到了命運的必然性依然是可疑的,這就預示著“突轉”不會就此停止,翠翠不免還要從此刻的逆境邁向另一種逆境。
祖父死后,翠翠愿意讓祖父生前的好友楊馬兵陪她,楊馬兵愿意照顧翠翠,而且比祖父更擅長講故事,自然成為翠翠的依靠,而楊馬兵曾是翠翠母親的追求者,對翠翠母親的事較為熟知,他講了母親的種種舊事,又因為不了解祖父一直以來是如何謹小慎微地對待翠翠的“無知”,于是將一切的因果告知翠翠,到這里,她才總算“把事情弄明白”了:天保的死,儺送的出走,祖父的病故,這些本來沒有責任的事情原來全部間接地由自己的過失引起,這不能不引起她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反思,她會發現人似乎不該生活在這種無知當中。但正如柏拉圖在《美諾篇》中提出、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論述過的那個悖論所言,人不可能探究他不知道的東西,因為人不知道自己探究什么[5]。命運的必然性之于翠翠個人,沒有以越掙扎越深陷的模式起作用,而是讓她無知于自己的目標,只能隱約感到處境的轉變方向對她不利,卻不知道應當如何組織行動。積極地替她行動的是老船夫,但老船夫也只能將一個安穩的未來定為翠翠的目標,他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讓翠翠回避痛苦,而翠翠自己并不是在做過逃離命運的努力以后才失敗的,因此一個更好的結果對她將永遠成為一種潛在的可能。翠翠從此以后可能會轉變生活態度,試著用行動實現一些人所“合當追求”的目標,任楊馬兵在渡船上安放竹筒,接收過渡人施舍她的錢財或許就是一個標志,若依祖父的言傳身教,這種行為是不大恰當的,但她已經在競爭者陪嫁的碾坊與儺送的出走、自己的不幸之間建立起聯系,她會領悟甚至夸大金錢對愛情的影響,對一個天真純潔的少女而言這已經是令人遺憾的變化,然而她為了回避受傷、保護自己而構建起來的這一套非本質的因果性,在未來某天更大的不幸降臨時又會轟然倒塌,那時自然就是命運徹底解蔽的時刻。正如先前的分析,若視《邊城》中其他人物的性格和生存狀態為“現實”,翠翠則是在那之前的“潛能”,她被動地吸收著各種人情世故,學習邊城世界的規則,實際上轉變已在潛移默化地發生,但感覺上她仿佛能永遠對命運視而不見,而她的那種獨特的美感可以保持下去,直到這次的“發現”,使人理解到她即將或已經成為“有瑕疵的善”,后續的悲劇也就能夠預見了。儺送也許永遠不回來,也許明天回來,命運的利劍高懸于翠翠頭頂,準備給這個自以為從無知中解脫出來的少女最后一擊。《邊城》在此處結束,“突轉”表現為人物從順境到逆境的轉變,且只發生一次,這符合亞里士多德對理想悲劇的要求,而且給人留下深長的余韻。
四、憐憫與恐懼
亞里士多德這樣定義悲劇:“悲劇……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1]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認為:“憐憫是由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而引起的,恐懼是由這個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引起的。”[1]而他在《修辭學》中定義憐憫為“一種由于落在不應當受害的人身上的毀滅性的或引起痛苦的情緒”[6],恐懼則是“一種由于想象有足以導致毀滅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禍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緒”[6]。綜上,悲劇就是通過對他人痛苦的模仿來引發人們憐憫和恐懼兩種感情。
提到痛苦,不能不立刻想到亞里士多德對“苦難”的論述。“苦難”與“突轉”“發現”是悲劇情節的三大成分,他說:“它的第三個成分是苦難。……苦難是毀滅或痛苦的行動,如死亡、劇烈的痛苦、傷害和這類的事件,這些都是有形的。”[1]“苦難”就是在直接地模仿痛苦,是情節中最能引起恐懼和憐憫之情的了,相比悲劇中動輒對殺戮與毀滅進行赤裸地展示,《邊城》中對痛苦的呈現堪稱“溫柔”:老船夫靜悄悄地死在雷雨之夜,死亡的時刻無人知曉,身旁只有翠翠陪伴;天保的死僅為旁人的言語訴說,仿佛發生在另一世界;儺送在外部壓力與內心糾結的壓迫之下最終爆發,選擇出走,那時那刻的痛苦卻輕輕落在“同他爸爸吵了一陣”這簡單的幾個字上;而翠翠永遠以哭泣應對痛苦,只有哭泣的場合不斷變更。這種克制在文字描寫和情節安排上都可以明顯地表現出來。
亞里士多德將悲劇分為復雜劇、苦難劇、性格劇和穿插劇,最好的復雜劇只依靠“突轉”和“發現”構成,不要求“苦難”的成分。不是人物遭受的痛苦足夠強烈和可怕,就能成功引起憐憫和恐懼,好人無端地受苦,只能引起反感;壞人犯了罪而受苦,又不值得同情。不該遭殃者遭殃,才能引起憐憫,遭殃者與觀眾相似,才能引起恐懼,這里除了從hamartia方面理解為悲劇應該模仿有瑕疵的好人,將關注點落在人的共有的局限性上面,也可以認為這種人也應該在美德上符合理想,“寧可更好,不要更壞”[1],也如亞里士多德談及悲劇與喜劇的區別所說的:悲劇模仿優于我們的人。基于這點,“詩人就應該向優秀的肖像畫家學習,他們畫出一個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來的人更美。詩人模仿易怒或不易怒的或具有諸如此類的氣質的人,也必須求其相似又善良,例如荷馬寫阿喀琉斯為人既善良而又與我們相似。”[1]可見這種“好”就品質而言,應該是既優于現實,又能讓普通人發現這種品質與自己的相似的。
《邊城》引起憐憫與恐懼的方式沒有脫離喚起對他人痛苦的同情,只是重點不在對淋漓鮮血的展示,而是極力表現遭受不幸者的人性,這種人性在沈從文那里具有本質的高度,故此有理由要求引起普遍的悲劇效果。
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評論筆下人物:“因為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7]《邊城》中人物“極其平凡”“極其瑣碎”之處已在本文第二節論述過,那里顯示的局限性是一切人的共性,讀者自然能從中見出相似,引起恐懼;轉而尋找“極其偉大”“極其美麗”之處時,能夠發現的則是優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質樸,勤儉,和平,正直”[7]的人性:翠翠人美心善、純潔無瑕;老船夫淳樸厚道,熱情真誠;船總順順仗義公正;天保和儺送雖然脾氣不同,行事都與人為善,且具有男兒的剛強勁健之美。
這種人性的特點在于,第一,人物道德上并非完美;第二,雖然不一定符合現實,尤其是那些“都市中生長教育的讀書人”[7]的現實,卻符合他們的理想。因為在沈從文那里,這便是中國人所失落的過去的偉大民族性,因此自然能得到“極關心全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7]的讀者的認同。之所以《邊城》具有超越時空的感染力,是因為其對本質的、理想的人性的追求和對美的把握是人類永恒的關切。《邊城》中描繪的人性之美,正是由人所共有的一些品質充分發展而成,讀者將隱約感到自己存在尚未實現的善的潛能,只是實現的過程也是轉變的過程,此刻可以把握的美或許不免流失,因此不能不為此憂愁,這時看到人物因為自身的hamartia,命運滲入其生活,淪落不幸的境地,勢必會引起憐憫和恐懼。
參考文獻
[1] 亞里士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 第12卷 散文[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
[3]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4] 趙振羽.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形而上學解讀[D].長春:吉林大學,2013.
[5]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中短篇作品[M].劉小楓,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23.
[6]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M].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 第8卷 小說[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 陸曉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