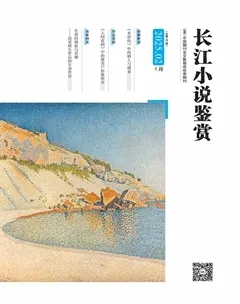《生死場》中植物意象與命運的交織
[摘 "要] 魯迅在為蕭紅步入文壇的標志性作品《生死場》撰寫的序言中,高度評價了該作“敘事與描繪景致之功勝過人物刻畫”。蕭紅憑借女性作家的細膩視角與勇于創新的筆觸,構建了一系列繁復多變的意象,尤其是植物意象,為她的文學創作賦予了鮮明且獨特的活力。《生死場》中,植物不僅是自然風光的點綴,還蘊含著深邃的象征意義,與小說中的人物命運緊密相連。這些植物意象不僅折射出作者個人的情感傾向,還深刻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預示她們的命運走向,并映射出她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生活境遇。本文剖析了《生死場》中出現的植物符號,以期進一步探究人物性格與其命運軌跡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蕭紅是如何巧妙地借助自然元素展現其獨特的文學魅力的。
[關鍵詞] 《生死場》 "植物意象 "人物命運
[中圖分類號] I207.4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2-0021-04
當前,學術界對蕭紅作品《生死場》的意象分析主要集中于動物意象,其中不乏深入洞見。有研究者細致探討了人與動物在命運層面的共通性,揭示了深刻的主題意義[1];也有學者從動物隱喻中提煉出現代性的潛在特征,拓寬了作品解讀的視野[2]。盡管這些研究視角獨到且富有價值,但它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同樣重要且值得探討的維度:植物意象。在蕭紅的文學世界中,植物元素頻繁出現,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動物相比,植物在自然界中顯得更為靜謐與被動,缺乏自主行動的能力。然而,正是這種靜態特性,使植物成為承載深層象征意義的理想媒介。蕭紅對自然界的深情厚愛,在她對植物世界的細膩描繪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呼蘭河傳》中關于童年記憶與祖父后花園的生動敘述便是明證。同樣,《生死場》中,蕭紅通過將特定植物與人物經歷緊密相連,構建了一種深刻的精神紐帶,進而形成了富有象征意味的命運隱喻。因此,進一步深入挖掘該作品中的植物意象,不僅能夠豐富我們對這一文本的理解層次,還將為解讀蕭紅的文學創作提供一個新穎且獨特的視角。
一、金枝:酸澀青柿映悲運
《生死場》中,金枝這一角色如同一顆酸澀的青柿子,承載了深沉的悲劇色彩。她的母親嚴厲斥責道:“小老婆,你真能敗毀家業,摘青柿子。昨夜我罵了你,不服氣嗎?”此前,金枝與成業在河岸邊的一次沖動之舉導致她未婚先孕,心中滿是對家人反應的深深恐懼,因此她選擇了沉默。在這種焦慮與不安的驅使下,她采摘時分心,不慎摘下未熟的青柿子,從而招致了母親的嚴厲責備。金枝的命運與其名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的名字寓意珍貴的“金枝玉葉”,而現實生活中的她卻如同鄉間那些不起眼的青柿子,既廉價又酸澀難咽。這一深刻的比喻,不僅揭示了金枝作為薄命佳人的悲慘處境,也映射了當時社會環境下女性的低下地位與無奈。
成業對金枝并沒有什么真摯的情感,而是被純粹的性沖動驅使。成業認為金枝僅是一個滿足自己生理需求的工具,而非受尊重的獨立個體。當金枝在家門口,滿懷希望成業能分擔她因未婚先孕而產生的恐懼與焦慮時,成業卻以蠻力將她擄住,無情地將她壓在墻角的灰堆上。他這種用腕力扼制“病的姑娘”的行為,并非出于對金枝的關心或愛意,而僅出于本能沖動。這不僅彰顯了成業對金枝感受的冷漠無視,也深刻體現了他對女性的物化態度,金枝對他而言,僅是一個欲望釋放的對象。從性別理論的視角審視,這段關系無疑揭示了父權社會結構下兩性權力的極端不對等。金枝在兩人關系中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無法掌控自己的身體與命運,宛如枝頭待摘的青柿子,無力決定自己的命運。對她而言,性行為并未帶來絲毫精神上的慰藉,反而使她承受了社會輿論的重壓和未婚先孕的苦澀后果。成業的主動,導致了金枝的被動接受,他的滿足是建立在金枝的痛苦之上的。最終,成業將少女金枝強行變成了母親,使她的命運變得如同那些尚未成熟的青柿子一般酸澀。成業嬸嬸的預言不幸言中:“等你娶過來,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會打罵她呀!”婚后的生活無情地驗證了這一點。金枝日復一日地承受著繁重的家務勞動,夜晚則成了丈夫發泄欲望的對象。她不僅要面對勞作帶來的身心疲憊,還要忍受生育帶來的劇痛。更悲慘的是,她還經歷了女兒夭折、丈夫去世等一系列沉重的打擊。在戰亂中,她流離失所,甚至在縫補工作中再次遭受侵犯。返鄉后,她又面臨母親的誤解與責備,在絕望中試圖遁入空門尋求解脫,卻未能如愿。
在鄉間,柿子常被視作廉價之物,這一觀念在農戶們驅車進城販賣白菜時體現得淋漓盡致。路過王婆的場院,他們隨手從車上丟下幾個柿子,輕蔑地稱:“柿子是賤東西,是不值錢的東西。”這種對柿子的貶低隱喻了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悲慘境遇。農村女性如同這些被輕視的柿子,享受不到任何社會資源的傾斜,卻仍被當作資源流通。在鄉間,女性出嫁與柿子的出售在某種意義上是類似的,她們的命運如同那些尚未成熟的青柿子,酸澀而廉價。蕭紅在《生死場》中,通過金枝這一角色,深刻描繪了女性在父權制社會中被邊緣化和被壓迫的處境。金枝的經歷,從被引誘盲目懷孕到家破人亡,再到躲避日軍騷擾時仍未能逃脫強暴,無一不揭示了封建社會中女性作為男性附屬品的地位。她的故事,不僅是個體悲劇的展現,更是對當時社會性別不平等現象的深刻批判。
這一隱喻手法與蕭紅自身的經歷緊密相連。她曾親身經歷過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迫,少時勇敢逃離包辦婚姻,追求個人自由和文學創作的夢想。這種個人經歷使她對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處境有著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從女性主義理論的角度來看,金枝的故事揭示了性別化的經濟價值:在男權社會中,女性的價值常常被低估,就像那些被認為不值錢的柿子一樣。她們的身體和勞動經常被當作廉價的商品來對待。同時,金枝的遭遇也展示了女性在性關系中的被動地位。她被迫接受成業的性行為,并最終成為他欲望的犧牲品,這體現了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無力感和脆弱性。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金枝都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壓迫。她的未婚先孕、丈夫的死亡、女兒的夭折以及日軍的侵犯,都反映了女性在社會動蕩和個人不幸面前的無助。金枝試圖通過逃避現實來尋求解脫,甚至考慮遁入空門,但最終發現連這條路也被阻斷。這進一步反映了女性在尋找自我身份和歸屬感時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她們在父權制社會結構中所承受的深重壓迫。
二、麻面婆:蒼白棉絮訴苦楚
在小說的開篇,蕭紅描繪了一位名叫麻面婆的女性。她的名字并非源于家族姓氏,而是因為其面容的丑陋,以至于她幾乎未曾以正式姓名為人所知。這一微妙的設定,深刻地揭示了她在社會中的邊緣處境。盡管小說未曾明確揭示她的全名,但通過蕭紅細膩的情感描繪,讀者得以窺探到這位女性復雜的內心世界,以及她所承受的無盡苦楚。麻面婆這位無主見、懦弱的女性,面對生活中的諸多不如意時,從未有過絲毫的抱怨。無論是丈夫二里半的嚴詞斥責、鄰里間的瑣碎爭執,還是孩童們的無禮打擾,她都選擇以沉默應對,仿佛是一塊溫熱的蠟,在生活的重壓之下緩緩融化,卻始終保持著內心的綿軟。她似乎永遠表現出一種難以名狀的憂郁,就像一片柔軟而蒼白的棉花,隨風飄蕩,這既是她個人命運的寫照,也是當時社會女性普遍境遇的隱喻。
故事一開場,鏡頭便聚焦于麻面婆忙碌的身影:在炎炎夏日下,她在樹蔭中汗流浹背地搓洗衣物,這份專注直到遠處傳來羊只丟失的消息才被打斷。出于對找回失物的迫切渴望,以及希望通過此舉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深切愿望,麻面婆開始了近乎荒謬的搜尋。她翻動柴堆,試圖重現冬日里的那次偶然發現,卻完全忽略了季節變化對動物行為模式的影響。這一系列看似無厘頭的行動,實則透露出她內心深處對于獲得認可與尊重的強烈期盼。然而,當最終意識到自己的嘗試并未帶來預期的結果時,那份突如其來的失落感如潮水般涌來,令她倍感沮喪。麻面婆的一生,幾乎完全圍繞著家庭瑣事以及與配偶之間的關系展開,她的身份被簡化為“二里半之妻”“羅圈腿之母”,而非一個擁有獨立自我和身份的個體。這不僅是她個人的選擇,更是當時社會環境對女性角色定位的嚴格局限。在父權制的社會結構中,女性往往被邊緣化,她們的價值和地位被嚴重低估。盡管如此,麻面婆仍舊懷揣著改變現狀的夢想,努力想要通過實際行動贏得他人的贊賞和認同。她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打破社會對她的束縛和限制,尋找屬于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但遺憾的是,這樣的追求往往伴隨著深深的無力感和自卑情結。就像那團任由外界塑造形態的白棉一般,她始終無法真正掌握屬于自己的命運軌跡。麻面婆的故事,不僅是個體悲劇的展現,更是對當時社會性別不平等現象的一種深刻批判。蕭紅通過她的筆觸,揭示了女性在封建社會中的悲慘境遇,以及她們在追求自我認同和尊重過程中所面臨的重重困難。
三、王婆:堅忍玉米抗風雨
《生死場》中,蕭紅以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多位女性角色,其中王婆的形象尤為鮮明,她的生命軌跡如同一部抗爭史,與金枝、麻面婆等角色的悲劇命運形成了鮮明對比。
王婆的形象在第一章便被生動描繪,她的頭發亂且絞卷,如同成熟的玉米纓穗,既展現了生活的艱辛,也預示了她堅忍不拔的性格。在封建男權社會的重壓下,多數女性逆來順受,而王婆卻以獨特的個性和堅忍精神脫穎而出。她的一生充滿了坎坷,三段婚姻均未給她帶來幸福,反而是一連串的打擊:第一任丈夫的暴力與拋棄、第二任丈夫的早逝,以及與趙三結合后連失三子的悲痛。然而,這些磨難并未擊垮王婆,反而鑄就了她堅忍的人生觀。王婆對待婚姻和男性的態度與小說中其他女性截然不同。在封建社會中,女性往往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但王婆卻從未對男性有幻想。面對再嫁,她不像祥林嫂那樣感到羞恥,而是淡然處之。在家庭中,她追求夫妻平等,即使面對性格剛強的趙三,也堅持己見,不為所動。這種獨立的思想和堅定的意志,使她在眾多女性角色中顯得尤為突出。
王婆的堅忍不僅體現在個人生活上,更體現在她對地主階層的憎恨和反抗上。當趙三等人計劃對付提高地租的地主惡霸時,王婆不僅鎮定自若地詢問事態進展,還鼓勵趙三采取行動,甚至提供了老式火槍并教會了他如何裝填彈藥。這一舉動不僅展現了她的勇敢和果敢,也體現了她對地主階層的深惡痛絕。在反抗階級壓迫方面,王婆展現出了超越一般女性的膽識和智慧。然而,王婆的堅忍并非沒有極限。當趙三因誤傷小偷入獄后,得到地主的幫助提前獲釋,他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對此王婆感到極度失望。她憤怒地質問趙三,揭示了她對忠誠與原則的堅守。更令人震撼的是,當王婆試圖通過服毒來結束自己生命時,趙三的非人表現讓她在生死較量中徹底反抗暴力與父權制社會。她以驚人的生命力證明了自己的堅忍與不可征服。
面對孩子的死亡,王婆的反應與金枝截然不同。金枝在失去孩子后,只能與冷漠的丈夫背對著哭泣,而王婆卻能從痛苦中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無論是第一個孩子小鐘的離世,還是兒子被逮捕處決,甚至是女兒為革命事業獻身,王婆都展現出超乎尋常的冷靜與堅忍。她像東北廣袤原野上的玉米,無論遭遇多少風雨洗禮,都能挺拔而立。王婆的堅忍和抗爭精神不僅體現在個人生活上,更成為那個時代里敢于抗爭、永不言敗的精神象征。她的一生充滿了挑戰與不屈,但她從未屈服于命運的安排。她用自己的方式對抗著命運的不公,勇敢地挺直腰桿,不斷地向下扎根汲取力量,努力使自己變得更加堅強。這種精神不僅讓她成為作品中最具有特色的人物之一,也激勵著無數讀者在面對困境時勇往直前。
王婆是《生死場》中一個鮮明而又鼓舞人心的角色。她的一生充滿了坎坷與磨難,但她卻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和獨特的個性贏得了讀者的敬佩。她對待婚姻和男性的態度、在反抗地主階層中的勇敢表現,以及面對孩子死亡時的冷靜與堅忍,都使她成為那個時代里敢于抗爭、永不言敗的精神象征。王婆的形象不僅豐富了作品的內涵,也為讀者提供了深刻的啟示:無論經歷多少風雨,只要保持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勇氣,就一定能夠戰勝困境、迎接光明的未來。
四、孩子:野草飄零顯悲涼
社會的進步程度,往往最能從其對孩子的態度中體現出來。《生死場》中那些在生死邊緣徘徊的人們,連自身的生存需求都難以滿足,更遑論對另一個生命的珍視與呵護。
孩子本應是愛情的甜蜜果實,卻在這里變成了婦女們愚昧而順從地承擔的生育任務,自然繁殖變得盲目且無序,生產成為女性獨有的犧牲儀式。五姑姑的姐姐在草叢中分娩,新生命在草堆與血泊中降臨,卻隨即消逝。生活的極度貧困迫使父母需要不停勞作以求溫飽,因此,在某些層面,孩子的失去對父母而言竟成了一種解脫。王婆去喂牛,孩子無人照看,不幸跌入草堆致死,更是悲劇中的悲劇。成業在憤怒之下,竟將剛出生的女兒摔死,在亂墳崗上,他看到的血染草叢,竟幻想成是捆綁小金枝的草繩。
孩子如同野草,不被期待地來到這個世界,承受著冷漠與暴力。他們的童年嚴酷而煎熬,充滿了辛酸與淚水,最終往往被冷落至死。草是卑微的,這些孩子也同樣被認為是卑微的。即便幸運地長大了,他們的生活也并不好過。小說中描述:“冬天,對于村中的孩子們,和對于花果同樣暴虐。他們每人的耳朵春天要膿脹起來,手或是腳都裂開條口。”他們被貧窮與嚴寒無情地折磨著。這些曾經的小草,長大后可能變成月英那樣牙綠掉、眼綠掉的可憐人,或是求生不得的金枝。而馬卻展現出連人類都罕見的溫情:“老馬是小馬的媽媽,它停下來,用鼻頭偎著小馬肚皮間破裂的流著血的傷口。”這一幕既諷刺又可悲,在生活的重壓下,人類竟變得如此冷血,甚至不如家畜。這種冷漠既源于生活的艱辛,也在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逐漸消磨了人們的情感,異化了人性。嬰兒如同野草般被隨意地生下,泛濫而不被珍愛,甚至不如畜生,這是一種令人戰栗的悲哀。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在這片土地上,正悄然消逝。
五、結語
通過對《生死場》中植物意象的深入剖析,我們不難發現,蕭紅以其獨特的女性視角和細膩的筆觸,將金枝、麻面婆、王婆等女性角色與植物緊密相連,構建了一幅幅生動而富有象征意義的畫面。這些植物意象不僅折射了女性角色的性格特征和命運走向,更深刻揭示了當時社會環境下女性的低下地位和無奈。金枝的命運宛如未熟的青柿子,滿含酸澀與苦澀;麻面婆的性格則像柔軟的棉花,缺乏自我的力量,顯得懦弱而順從;王婆則如同東北大地上堅忍不拔的玉米,挺拔而充滿生命力;而孩子們的境遇悲慘,如同被忽視的野草,在冷漠與暴力中掙扎。這些植物與形象,共同交織成了一首深沉而哀傷的命運悲歌。
參考文獻
[1] 王欽.“潛能”、動物與死亡——重讀蕭紅《生死場》[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10).
[2] 李兆玥.論蕭紅《生死場》中的動物隱喻與現代人格感知[J].長江小說鑒賞,2023(23).
[3] 季紅真.《生死場》女性人物原型與系譜考[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7).
[4] 劉東.跨域·“越軌”·詮釋——重讀蕭紅的《生死場》[J].文學評論,2020(3).
[5] 季紅真.魯迅序言對《生死場》的經典定位之后[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10).
[6] 葉君.《生死場》版本與修改考論[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6).
[7] 李福熙.論蕭紅小說的悲劇意識[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8(3).
[8] 皇甫曉濤.一語難盡——《生死場》的多層意蘊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多維結構[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3).
(特約編輯 劉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