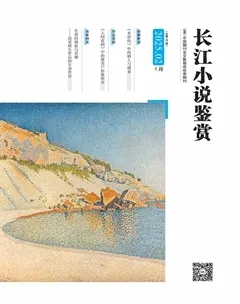《夢女》:女性主體的自我認同與存在探索
[摘 "要] 埃斯特·李,1989年出生于美國洛杉磯,現居德國萊比錫。她的作品《夢女》英文原標題為《Y/N》,“Y/N”是“Your Name”的縮寫,通常是同人作品中主人公的替代符號,可以被讀者的名字取代,使之與文中其他人物產生互動感,令讀者在閱讀小說時產生更好的代入感。故事圍繞一個普通的女孩展開,女孩原本從事著一份無聊的工作,談著一段注定沒有結果的戀愛,渾渾噩噩但又時刻維護著自己脆弱不堪的精神堡壘,試圖通過減少自己與世界的聯系來擺脫平庸與愚昧。偶像Moon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她開始踏上找尋“愛”的旅程。在這個過程中,她重新發現自己,發現別人,這是一段女性視角下逃離存在主義危機的旅程。
[關鍵詞] 《夢女》 女性主體 "認同 "存在主義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2-0071-05
一、女性主體文化
1.女性亞文化
女性亞文化,被視為屬于女性自己的文化。與父權制下的主流文化不同,女性作家在女性亞文化影響下,不再亦步亦趨模仿男性文學寫作方式,而是將女性作為主體,發出女性的聲音,生產出女性自己的文學。長期以來女性的聲音處于一種“被壓抑”的狀態,肖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說,人們在看待男性作家所寫的角色時,會認為他寫的是人性,而在看待女性作家的創作時,會認為她首先是一個女人,然后才是一個作家。這種雙重評價標準抵制和貶抑了女性的寫作,一方面貶低了閱讀女性作品讀者的審美趣味,另一方面否定了女性作品的價值。然而,女性作品是整個人類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們抒發女性的情感,表達女性的審美體驗,更重要的是,它們可以書寫并表達世俗的男女情愛之外的事物。女性亞文化突出的是女性特質并伴隨著女性平等意識的覺醒[1]。
正如埃斯特·李的作品《夢女》,表面上看來,這僅僅是關于瘋狂粉絲對Kpop偶像從路人到私生飯的歷程書寫,是泛濫的“夢女文”的代表,是低俗欲望的載體,作者的女性身份也會被當成這部小說“格局不高”的象征。可是,當我們真正閱讀的時候會發現,這本書披著“夢女”的外衣,實則書寫的是現代女性的尋愛之旅,是認同自己、尋找自我存在價值的過程。書中的男性處于被觀察的客體狀態,以“我”為代表的女性主體開始認識和發現他們。主人公“我”不再是被動、壓抑、服從的角色,相反,“我”在意識到與馬斯特森的戀愛沒有結果后,敢于反抗馬斯特森的觀點,敢于說出“相較于他,Moon對‘我們’的關系付出更多”,并毅然決然地離開。在兩性關系上,她也敢于說出自己的想法,書中不乏肉欲的描寫,她在小說中是用身體和靈魂一起去感受性愛的,不同于傳統身體道德化和性愛羞恥化的做法,她對情欲有自己的理解,“我對Moon并沒有性欲。我的性欲只是單純地愛著他的性欲,沒有保留,沒有遲疑”。但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也存在一定的主體性迷失,她在和馬斯特森的爭吵中下意識地滾下床,從桌上拿走自己的書,因為覺得“不擋別人的路是我生來的默認配置”。
2.夢女文化
夢女,來源于日語“夢女子”,指幻想自己與二次元角色發生互動的女性,現在也泛指真實生活中的部分明星粉絲。夢女會幻想自己與欲望對象發生各種各樣的故事,進而可能創造出代表自己的形象來與喜歡的角色進行互動,并將自己的幻想記錄下來,從而產生出“夢女向作品”(以下簡稱夢女作品)。這類作品像言情小說和偶像劇一樣,都是女性群體創作出來的以女性為主體的、基于幻想滿足自身需要的產物。
在成長過程中,女性通過言情小說和偶像劇了解男性,男性通過成人電影和男頻小說了解女性。大部分男性把女性作為發泄的客體而忽視其完整的人格,女性則追求一種靈與欲的結合[2]。女性需要精神的聯結大于肉體,她們可以通過想象來愛上一個可能并不存在的實體,正如網絡流行語“男人最大的魅力來自女人的想象力”,相當一部分女性在缺愛的條件下,會生發出對愛的極度渴望,與其說這是她們渴求愛與被愛,不如說她們在尋找一種被需要、被關注的感覺,享受在愛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夢女群體在幻想愛人的過程中感受到現實世界所沒有的奇妙感覺,是她們逃離現實世界平庸、瑣碎、繁雜的一種方式。在創作夢女作品時,她們能夠真實地釋放出自己的情感,創造一個完美、全心全意愛著自己和被自己愛著的人物,這是情感表達與宣泄的需要。夢女作品較之以往的傳統女性文化產品,如言情小說、偶像劇等而言,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不確定性,能由女性主體自主選擇角色,構思情節,夢女群體通過這種二次創作在其喜愛的角色、人物身上投射自身對于理想配偶的構思與設想,享受到擁有虛擬戀人的快樂。正如小說中主人公最后意識到的那樣,“我愛的不是他,我愛的是他的故事”,夢女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想象中或者現實中的二次創作,用女性自己的筆觸去描繪一個屬于自己的故事。夢女文化與乙女文化雖然都具有參與式文化的特點,但二者的本質不同在于夢女與其“夢對象”的關系并不僅僅局限于戀人,雖然愛情類型的關系設定仍然是夢女文化圈內的主流,但仍存在塑造親情、友情等關系的相關作品[3]。夢女文化更強調女性主體意識和自由選擇,而較少乙女文化中的“官方”色彩——女性只能被動選擇已經設定好的攻略對象。
同時,需要注意到,由于父權制體系下女性對愛充滿渴望,但對現實親密關系抱有疑慮和恐懼,因而,她們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更為保險的對象身上,比如為夢女群體量身打造的娛樂偶像。資本發現人性這一弱點,從而通過操控和人為造勢,塑造一個個形象特定的偶像,他們被認為是“安全可靠的”,不會像現實生活中的男性一樣“背叛”,吸引缺乏安全感的女性成為夢女。這些偶像首先是異化的人——他們被要求在鏡頭前展示包裝好的自我,而不是真實的自我,粉絲被他們的“與眾不同”所吸引,為他們塑造出來的“神”的形象買單。他們是“造夢者”,在一定程度上為粉絲們逃避現實世界的平庸提供了一個出口,讓粉絲們有一個精神依托,粉絲也可以通過想象自己與偶像的關系達到情感滿足。可是偶像歸根結底是現代娛樂產業的產品,他們與粉絲的關系是高度商業化的,是資本獲取金錢的代言人。這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情感剝削,在小說的開頭主人公就明確指出這一點,“我也知道這些男孩通曉人心……為粉絲提供在這場騙局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機會”,“他們在粉絲中喚起的可觀的集體意識,不過是一種吸引更多粉絲的策略”。
二、情感認同
1.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是能夠理智地看待并且接受自己以及外界,能夠熱愛生活,而且有明確的人生目標,并且在追求和逐漸接近目標的過程中會體驗到自我價值以及社會的承認與贊許。個體既從這種認同感中鞏固自信與自尊,同時又不會一味地屈從于社會與他人的輿論。缺愛者缺的不是愛而是自我認同。
當一個女性選擇以“夢女”這一標簽代表自身的時候,她不僅僅是單純地尋找一個幻想的欲望對象,或者是渴望在現實生活中找到類似幻想中的完美戀人,更多的是在尋找自我身份認同。
故事借另一個女性角色O之口說出了這一觀點:“我想要一種完完全全屬于我的激情,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擁有……我想要的是根本的肯定。”小說中的“我”在一開始并沒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包括友情、愛情和親情,從事著一份聽起來就不大有前途和薪資報酬很差的工作——為一家澳大利亞僑商公司的一款洋薊心罐頭撰寫英文廣告文案。對自己的所有具體情況,主人公都盡可能地隱去了,甚至直到小說結束讀者都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現實生活的平庸無聊使得她無法塑造自己的思想,她的“精神括約肌死死地收緊,以防一切低俗和愚蠢入侵”,她在自我認同上是消極的,沒有明確的目標,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認同感,她的內心從一開始就充滿恐懼,她“恐懼自己會墮落至面目全非”。似乎她隨時都可以被任何一個符號替代。小說第三章《花樓》中,她參加一場粉絲聚會時穿上仿絲綢的粉色斗篷扮演Moon的形象;在第八章中,她又借用O的身份證化名“吳雪”參加派拉貢廣場的粉絲活動。實際上,無論是Moon還是O都更像是主人公自己的化身,她厭倦枯燥的生活,渴望借用一個新的身份來感受不一樣的人生,“我厭倦了將現實視為僅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渺小的人生不可能容得下所有人類的體驗”。Moon的形象在小說前半段乃至快要結尾時都處于被主人公和其他人仰視的狀態,一個接近“神”的形象,“他的美可以輻射整個地球”,他存在于幻想之中。這個形象象征著自我主體對美好的向往,主人公迷戀的并不是Moon這個實體的人,更多的是他身上獨特的故事和經歷,作為一個碌碌無為的人,她找不到自我,更不可能認同自我,她是一個沒有故事的人。在主人公第一次給馬斯特森寫信的時候,她把馬斯特森的名字Masterson劃去asters,加上一個字母O,變成了Moon。而在尋找偶像的過程中,她遇到了女人O,這個女人曾經制作鞋底,其中一雙鞋底被主人公穿著,這個名為O的女人似乎是她和偶像之間的聯結,又像是她自己的化身,一次次幫助她尋找偶像。在故事的最后,O甚至和新男友一起計劃將主人公的故事拍成短片,讓主人公能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故事”。主人公在一次次對Moon的追尋中,真正認識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她堅持追尋只是為了證實一個想法——我是獨特的,我可以書寫出屬于自己的獨特故事。比起Moon更像是一個崇高無上的理想,O像主人公的鏡像,更像刺破她的一把利刃,O讓她更好更清晰地看見自己本來的面目。直到她看見自己,她才最終認同自己。
小說第七章《地球上的Moon之子》出現了一個獨特的人物形象,他自稱是“Moon的殘渣”,通過閱讀可知,他是一個殘疾人,他認為上帝用創造Moon剩下的材料制造了殘破不堪的他,他通過這個想法來為自己的存在尋找合理性,寬慰自己。他和主人公一樣,在對Moon的狂熱愛中找到自己可以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
主人公曾經的情敵——馬斯特森的前女友莉澤,在閱讀了第一個題為“Y/N”的故事后,對自己有了不可思議的認知,她將自己想象成Moon的母親,在內心欲望與渴求的驅使下,她開始迫切想要了解自己的生活可能出現的另一面,也就是說,她開始認同一個全新的自己,“只有我是Y/N”。
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和主人公一樣,希望靠依附在偶像身上來完成自己獨立人格的重塑,發現自我存在的價值。Moon不再僅僅作為一個娛樂形象存在,而是被現代人上升到“神”的高度的精神象征。與其說主人公愛著Moon,不如說她渴望取代Moon去體驗一種不一樣的人生,擺脫現實生活中的枯燥乏味。她渴望真正被認同,被自己的內心所承認。
2.群體認同
群體認同(Group Identity)是指人們通過與某個群體建立認同感來增強自己的安全感,可以提供歸屬感和支持。阿德勒心理學認為,人類最具根源性的需求是“歸屬感”。
小說中的“我”是一個韓裔德國人,這意味著她不太可能被德國主流社會完全接納為“自己人”,也不太可能被韓國本土接受,因為她的韓語很蹩腳,也很久沒有到韓國本土。書中沒有交代她的父母現在何處,但可以推斷出他們都是韓國人,主人公在去韓國尋找Moon的時候曾經說到“路過兒童大公園,進入往十里,那里是我父親成長的地方”,“大峙洞,我母親是在那里長大的”。或許主人公希望在父母以前生長生活過的地方尋根,獲得一絲文化認同,可是當她試著去想象父親生活過的地方時,她“只能看到大樓從天而落,將他壓垮”,這樣的想象就像無根的浮萍,是虛無縹緲的,不能給她帶來被本土文化接納的感覺。同時,當她回憶起母親的童年時,也只存在一段令人不愉快的記憶——母親自認為是最受寵愛的孩子,可是在家里的狗被人毒死時,外祖父只記得兩個兒子做了什么,在他的文章里絲毫未提及女兒,因此母親只能通過想象“那天早上她發燒臥床,從未跑出那扇門,從未抱過那只死掉的狗”來逃避父親可能并不是最疼愛她這個事實。這兩個例子可能意味著父母將原生家庭的痛苦原封不動地傳遞給了主人公。再者,文中唯一出現的有血緣關系的親人——多年未見的叔叔,也與主人公保持著冷漠的疏離感,他們盡可能用交談來緩解并不熟悉的尷尬,可是,從這位叔叔以為主人公沒在看他,快速彎腰擦掉她滴在地上的汗水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疏離與隔閡。
對于友情,主人公一開始便和室友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稱呼自己為她的陌生網友,同時覺得她們這一年的同居生活生出了一種“幾乎可以稱之為友誼的質地”。
她與哲學家馬斯特森的愛情是飄忽不定的,當別人詢問他們的關系時,她害怕直接承認,于是謊稱自己是馬斯特森的妹妹,他們的關系更接近肉欲,而不存在靈魂上的溝通,她曾故意將自己的筆記本留在他那里,希望他打開讀一讀,這意味著至少他對自己是好奇的,可馬斯特森沒有這樣做,在他們約會兩個月后,她仍然是馬斯特森正考慮愛的人,她對他沒有任何期待。
直到主人公開始接觸Moon和喜歡著他的一群人,她的世界才慢慢打開,她開始在“大魔法師”上創作故事,參加柏林粉絲會在咖啡店的活動,在首爾江南的小餐館遇見“Moon派”三人小團隊,在前往芭蕾舞團的路上遇見O……這一切讓她逐漸與社會產生聯系,與他人產生聯結,似乎她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尋找偶像的蹤跡,可事實上,這是她尋求認同的探索之旅,在粉絲團體中,在怪人中,她終于逐漸感受到被接納。雖然這對于她而言是尷尬的,“這些陌生人知曉我愛的人也是他們愛的人”,可是她依然愿意和粉絲們在一起,其他粉絲對偶像的狂熱也印證了她做出的選擇沒有錯,她的信念在粉絲群體中一次次被加強,她感受到他人對自己的認同。
小說第五章《真實的生活中》出現了一對戀人,他們靠著對Moon的愛相愛,彼此確信只有對偶像的愛超出對對方的愛他們才能真正聯結。這對戀人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他們之間的交流也只有Moon這一個詞,可是他們感受到被認同,感到被需要。
主人公在群體中擺脫了孤獨無奈,先前那種被人排斥的感覺漸漸消失。當她和粉絲們在一起時,雖然每個人的欲望都不同,對偶像也抱有不同的看法和期待,可是她開始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再被拒絕。
三、小說中的存在主義哲學
1.荒謬世界和個體孤獨
整部小說一直籠罩著淡淡的絕望與無力,主人公遇到的所有角色幾乎都是異化的存在,他們身上的色調是灰暗陰沉的,與主人公保持著疏遠的距離,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馬斯特森是不能被她真正認識與了解的,不能給她精神上的陪伴,甚至不能理解她在想什么,在他發現主人公愛上偶像Moon后,他覺得這是荒謬的,并且冷漠地推薦她去看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菲詩崴芙(Fishwife,有“賣魚婦”之意,亦有“粗野婦人”之意)全盤否定主人公的愛戀,同樣認為這是一種幻想,是一種“心癮”。和她有親緣關系的叔叔也在有意無意地與她保持距離。
在小說的世界里,主人公得到的只有否定和逃避,似乎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無意義的,是一種妄想。雖然她存在并且有著健康的肉體,但她的靈魂是缺失的。在療養院里,她不斷把其他病人認作Moon,似乎他們都可以像自己一樣被替代為其他人,可他們的“靈魂是獨一無二的”。這和主人公恰恰相反,主人公身體健全,但靈魂缺失;在療養院里的病人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可他們的靈魂卻是獨一無二的。這意味著在荒謬的世界中,人變成了空心人,沒有思想,隨波逐流,在小說主人公身上表現為愛的缺失與求愛不得。正是世界的荒謬與靈魂的缺失,導致了主人公內心的孤獨焦慮,她無法預知未來也無法掌控一切,于是將自己存在的全部意義放在偶像身上,創作了一部與Moon有關,實際上反映自身渴望的小說,到了小說后半部,主人公創作的小說幾乎與她所存在的現實合二為一,亦真亦假,共同構成一個荒誕、虛偽、毫無生機的小說世界。
2.人的自由選擇
存在主義哲學認為人類存在是沒有固定意義的,在荒謬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選擇,但同時需要承擔選擇帶來的責任和后果。
小說中,O的母親無法忍受自己因事故失去聽力,選擇走向死亡;以馬斯特森為代表的平凡人選擇繼續平庸;梅花和Moon選擇相愛,在荒謬殘破中相互依偎。他們每個人都可能是主人公的一個面,暗示了主人公可能作出的選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女性角色O,她像是主人公的一體兩面,與主人公存在著或明或暗的聯系,她既是區分馬斯特森和Moon的O,又是小說后半段主人公的“新身份”——吳雪,在主人公最后明白自己與偶像的關系時,她又是那個準備書寫主人公故事、結識新男友開始新生活的人。同時,O的母親在小說結局中走向了死亡,這或許意味著作為舊的、被清除了的主人公的靈魂——對偶像的愛死去了。首爾泛濫的蟬代表了迷茫空虛、失去生活信念的靈魂們,它們被藥水——現實消滅了。當“我”的肉體也走向陽臺,等待警報聲響起時,或許“我”會真正在靈與肉的層面死亡,又或許“我”的另一面——代表著“我”的O會活下去,開始新的旅程。最重要的是,“我”終于明白了,必須通過行動來賦予生活意義,來超越個人命運和現實存在狀態。
四、結語
小說以女性視角探索作為普通人的“夢女”對偶像的情感,并借此探討現代女性的情感訴求,以及女性如何在尋愛的過程中尋找自我,發現自我。粉絲對偶像的愛戀本質上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存在主義探索,夢女們通過愛來探索自我存在的意義,找尋他人的認同與肯定,借此逃避當今快節奏生活下人的“異化”,尋找精神的港灣。小說的情節故事是虛構的,可它反映的當代人的存在主義危機卻是真實的。
參考文獻
[1] 谷君.默克羅比女性亞文化思想探究[D].上海:上海師范大學,2022.
[2] 楊永忠,周慶.論女性主體意識[J].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10(4).
[3] 王樂源.同人文創作中的“夢女文學”現象探究[J].內蒙古財經大學學報,2024(1).
(特約編輯: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