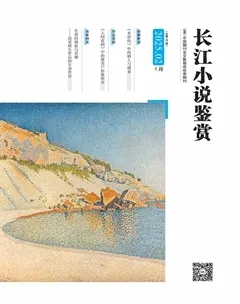《所羅門之歌》中吉他的人格失衡解讀
[摘 "要] 托尼·莫里森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裔美國女性作家。她的小說《所羅門之歌》通過黑人青年吉他的悲劇命運,深刻剖析了種族歧視對個人的巨大傷害。本文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對吉他的三重人格——本我、超我與自我進行剖析。吉他前期是一個在超我指導下的理智導師形象,而后期他成為一個受本我驅動的暴力復仇者。吉他的自我未能在本我與超我之間進行有效的協調與平衡,導致他在種族歧視的漩渦中既是受害者又成為加害者。通過對吉他人格失衡的深入分析,本文旨在增進讀者對黑人群體精神世界的理解,呼吁社會更加關注并正視種族問題。
[關鍵詞] 托尼·莫里森 《所羅門之歌》 本我 超我 自我
[中圖分類號] I106.4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5)02-0088-04
一、引言
托尼·莫里森,美國文學史上重要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探討了種族、身份和歷史等主題。《所羅門之歌》是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小說通過主人公奶娃的成長歷程,展現了美國黑人的精神探尋之路。吉他是小說中另一個重要人物,也是主人公奶娃的唯一好友,這一角色在小說中象征著一種極端的反抗方式,代表了那些深受種族歧視之苦,但又無法找到合適途徑解決問題的黑人。作者通過吉他這一角色,揭示了種族問題給黑人精神世界造成的毀滅性影響,呼吁以更加理性和平和的方式來解決種族問題。
弗洛伊德作為精神分析學的奠基人,提出了人格結構的三重模型,即本我、超我和自我。本我“受本能的驅使,遵循‘享樂原則’”[1]。超我是人格的道德部分,以“道德原則”為基礎,代表著內化的社會價值觀和標準。而自我是人格的決策部分,遵循“現實原則”,在本我的本能欲望和超我的道德約束中起協調作用。本文運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解讀《所羅門之歌》中吉他的人格失衡現象,分析其經歷的心理斗爭,以及這一斗爭與當時社會緊張種族氛圍間的聯系,以期增進讀者對吉他這一復雜角色的理解,進而對黑人群體在特定歷史時期面臨的心理壓力和社會困境有更為深刻的認識。
二、超我的浮現
超我在人格結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它“承載著社會內化的價值觀和道德規范,體現了社會法規和個人道德觀念的融合”[2]。在故事初期,吉他以其深厚的責任感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凸顯了其作為領導者的卓越品質。他不僅是奶娃的人生導師,引導其成長,也是黑人女性的支持者,對黑人族群深切關懷和維護。
吉他作為奶娃的人生導師,其行為體現出超越同齡人的成熟和洞察力。盡管吉他和奶娃在社會地位上存在差異,且吉他對奶娃的父親持厭惡態度,但在奶娃遭遇校園暴力時,吉他不僅挺身而出給予幫助,更成為奶娃深為信賴的知己。此外,在首次與奶娃共同造訪派拉特家時,吉他也表現出與其年齡不符的淡定與從容。相較于奶娃的混亂不安,吉他“在對話中未顯現出同齡人的猶豫和不安,而是率先打破沉默,開始了交流”[3],展現出他成熟的一面和極強的社交能力。吉他的自信沉著使其成為小說中一個可以讓人依靠且極具責任感的角色。在與奶娃的多次對話中,吉他展示出他深刻的社會洞察力,向奶娃傳授了很多關于黑人的歷史和文化知識,激發了奶娃追求理想抱負的動力。當兩人探討白孔雀無法飛翔的問題時,吉他告誡奶娃:“想飛,必須舍棄那些束縛自我的東西。”[3]這句極富哲理的話不僅為奶娃指明了人生方向,也體現了吉他的思想之深邃。吉他不僅是奶娃成長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非裔美國人社區中的典范,具有很強的領導力和影響力。
此外,吉他關懷并支持黑人女性,這一點在他與奶娃對待家庭和婚姻關系的不同態度上體現出來。一次對話中,奶娃向吉他講述了一個困擾他的夢境,夢中其母露絲被瘋狂生長的花朵吞噬,呼吸困難,而奶娃卻只是冷漠地站在一旁。對于奶娃在夢境中的無所作為,吉他表示強烈不滿,他質問道,“你為什么不去幫助她……把她從下面救出來……那也是你媽媽”[3],表明吉他對奶娃的冷漠行為感到憤怒,也表明了他對女性的關心與愛護。在對于婚姻關系的探討中,吉他與奶娃對哈格爾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當吉他發現哈格爾因被奶娃拋棄而崩潰時,他向哈格爾提出了富有哲理的建議:“你認為他屬于你是因為你想屬于他……‘歸屬’這個詞并不恰當。尤其是當你將它與所愛之人相聯系時。愛不應該是這樣的……你不能擁有一個人。你不能失去你不曾擁有的東西。”[3]吉他在此強調了女性自我價值的重要性,他鼓勵哈格爾更多地關注自身而非過度依賴奶娃,試圖喚醒哈格爾從奶娃的拋棄中走出來,教導她學會自愛。吉他的言行充分說明他對女性群體的深切關心與愛護。
在道德原則的指導下,吉他不僅成為奶娃的導師,以其道德智慧和人生經驗為奶娃指引方向,更成為黑人女性的守護者,為她們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與支持。吉他的行為,深刻體現了超我在道德行為中的核心作用,即引導個體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堅持道德原則,以符合社會規范和個體內心價值觀的方式行事。
三、本我的膨脹
本我“是一個無序且充滿活力的混沌狀態,其中充斥著各種本能沖動。它的核心驅動力是追求滿足本能的需求,遵循著‘享樂原則’”[4]。在持續性的種族壓迫與歧視的社會背景下,吉他的種族主義情緒不斷加劇。受仇恨心理和物質主義的驅使,吉他逐步摒棄超我的“道德準則”,成為一個極端的暴力復仇者。
隨著本我的膨脹,吉他將黑人所經歷的所有痛苦與不公全然歸咎于白人群體,對白人采取不辨是非的暴力行為。正如法農對殖民地黑人他者暴力的解釋:“在個人層面,暴力具有清潔功效,它讓本土人擺脫其自卑情結,擺脫絕望與不能行動狀態;暴力使其勇敢、恢復自尊。”[5]為滿足本我對自尊的欲望,吉他加入一個名為“七日”的秘密組織。該組織由七名年輕的黑人組成,他們以輪流殺害白人的極端方式作為報復手段。作為“七日”組織的一員,吉他秉持著一種極端的邏輯,他堅信:“當黑人兒童、婦女或男性遭受白人殺害,而法律與司法體系對此置若罔聞時,組織將隨機選擇一名相似的受害者,并以相似的方式給予制裁。”[3]在這種扭曲而瘋狂的認知下,當四個黑人女孩在教堂門口遭遇襲擊后,“七日”組織欲采取同樣的手段,對四個白人女孩實施報復性襲擊。事實上,“‘七日’的暴力行徑其實是一種私欲觸發的非理性活動,既疏遠了黑人社區,也背離了人性的善。他否認白人身上有善意,這種理念其實是用一種等級思想(黑人至上)去取代另一種等級思想(白人至上)”[6]。這種極端的種族主義觀念與報復心理,顯然已經徹底掩蓋了吉他的理性思考能力,導致他完全被對白人的壓倒性敵意所籠罩。
為踐行“七日”組織的殺戮指令,吉他逐漸認識到金錢作為實現組織目標的工具的重要性,并因此陷入物質主義的漩渦。當奶娃提出共同搶劫派拉特的計劃時,吉他立即應允,甚至積極策劃對派拉特實施暴力行動。在物質主義的誘惑下,吉他逐漸喪失理性,即使奶娃反復強調并未尋得派拉特的金子,吉他卻始終拒絕接受這一現實,甚至將微不足道的線索視為誅殺奶娃的依據。在吉他一味追求金錢的過程中,他徹底忽略了“七日”組織的核心信條“我們絕不拋棄黑人同胞”[3]。他無視此原則,毅然將奶娃納入暗殺名單,最終導致派拉特的死亡。對物質財富的盲目追求導致吉他走上屠戮同胞之路,成為一個極端的狂熱信徒與冷酷的劊子手。事實上,吉他對金錢的癡迷不僅體現了物質主義對個人價值觀的腐蝕,更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社會壓迫和種族歧視的背景下,個體容易被引入歧途。吉他原本是黑人同胞權益的捍衛者,然而,在本我物質欲望的驅使下,他的道德準則被徹底顛覆,導致了他對初衷的背離。
在本我的驅使下,吉他的暴力行為反映了他對現狀的絕望和對改變的渴望,同時也暴露了他對復雜社會問題的簡單化理解和應對方式。不斷升級的種族緊張局勢以及社會上根深蒂固的不公正現象共同塑造了他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推動他走上一條充滿危險的道路,以偏激和暴力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和追求。
四、自我的失衡
在人格結構理論中,“自我尋求外部世界對本我及其傾向施加影響,并努力用‘現實原則’代替在本我中不受束縛的‘享樂原則’”[7]。小說中,吉他的自我未能有效在本我和超我之間建立平衡。這種失衡導致他成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一方面被白人社會邊緣化,另一方面遭受黑人社區的孤立與排斥。更為嚴重的是,他的極端行為最終使他從受害者轉變為種族歧視的加害者,加劇了個體和社會的悲劇性。
吉他作為移民城市的黑人,“在城市消費浪潮中迷失,在種族和階級矛盾中無所適從,變成了典型的他者形象”[8]。一方面,吉他作為被白人社會邊緣化的受害者,其生活深受種族主義的影響。他的遭遇不僅揭示了種族歧視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更凸顯了個人在種族等級制度中的無奈與脆弱。另一方面,吉他亦遭受黑人社區的孤立。作為“七日”秘密組織的成員,他被迫放棄社交權利,在黑人社區中失去了親屬關系的紐帶。人際交往的缺乏加劇了吉他的不信任感,使其陷入物質主義的桎梏。事實上,吉他的經歷既指代社區成員共同面臨的種族困境,他的暴力行為也暗含對黑人社區內脆弱平衡狀態的潛在威脅。吉他渴望從這場無休止的種族斗爭中抽離,尋求個體的自由和解脫。然而,他的這一愿望被深層的恐懼和自我厭惡所掩埋,未能得到充分的表達和實現。他的暴力犯罪活動以及他對種族觀念消極的內化,進一步加劇了他與社區之間的距離,使其成為自己社區中的“他者”。
另外,盡管暴力能夠一時滿足吉他的本我權力欲望,這種報復手段對黑人社區的長期進步與和諧卻具有負面影響。在種族平等的道路上,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因為它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種族歧視的問題,反而會加劇不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阻礙社會的進步,“暴力是有代價的……采用暴力可以改變世界,但最有可能帶來的是更加暴力的世界”[9]。吉他的行為恰恰證實了這一觀點。吉他試圖通過暴力手段來打擊種族主義,但實際情形卻是加劇了社會分裂與沖突。為完成“七日”組織的任務,吉他不僅對好友奶娃實施暴力威脅,還殺害了派拉特,其所作所為不僅讓黑人同胞對他感到失望,心生憎恨,也加劇了黑人社區內部的分裂和矛盾。更為嚴重的是,他對白人無差別的謀殺行為,不僅加劇了白人群體對黑人群體的憎恨和偏見,也進一步固化了白人社會對黑人群體的負面評價。而使用暴力作為解決種族沖突的手段,更是一種極端的、不理智的行為,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種族問題,反而會加劇仇恨和暴力的循環,對社會造成更大的破壞和傷害。因此,吉他的憤怒和暴力行為雖然源于他作為種族主義受害者的痛苦經歷,但這種解決方式無疑是錯誤的。
吉他的自我未能有效地在本我與超我之間達成調停與平衡,這一失衡狀態直接引發悲劇性的結果,導致他被白人社會邊緣化,進而在黑人社區中也陷入被隔絕的境地,成為種族歧視的雙重受害者與加害者。因此,對于吉他及其悲劇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種族歧視的復雜性和危害性,為推動社會的包容與進步提供啟示。
五、結語
在運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對《所羅門之歌》中吉他這一角色進行深入剖析時,我們可以窺見一個在種族問題中掙扎的個體形象。故事初始階段,吉他呈現出在超我指導下的明智導師形象,顯示出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超我的行為調節能力促使吉他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堅守道德原則,以符合社會規范和個體價值觀的方式行事。然而,在種族問題日益凸顯的背景下,吉他逐漸陷入本我主導下的本能追求中。在本我的驅使下,吉他開始追求即時滿足和快感,忽視了對長遠后果的考量。這種沖動和盲目的行為最終導致他變成一個失去理智、盲目復仇的暴力者,暴露了他對復雜社會問題的簡單化理解和應對方式。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吉他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間未能維持有效的平衡,這種失衡狀態不僅使他成為種族歧視的受害者,更在不知不覺中轉變為加害者,加劇了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轉變深刻反映了吉他在處理個人欲望與社會規范間的沖突時所面臨的困境,也映射了受壓迫的黑人在面對種族歧視時普遍存在的掙扎心理。
吉他的悲劇性結局揭示了種族歧視的復雜性和危害性,種族歧視不僅對個體造成傷害,更對整個社會的結構和價值觀造成破壞。在應對種族歧視的威脅時,采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暴力手段顯然是不可行的,這種行徑極易導致種族間對立情緒的升級,進一步加劇不同種族間的緊張關系。此外,無差別地以暴力傷害其他種族的行為,不僅與反抗種族歧視的初衷背道而馳,更有可能加劇社會的分裂與混亂。因此,為構建一個公正、包容的社會,應采取理性、平和的方式去消除歧視和偏見,為所有人提供一個平等、和諧的生活環境。同時也要關注個體的心理健康,建立有效的人格平衡,以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和困難。
參考文獻
[1] 朱剛.二十世紀西方文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 Samuels R.The Pleasure Principle and the Death Drive[J].Freud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Science of Everyday Life,2019(1).
[3] Morrison T.Song of Solomon[M].New York:Vintage,2004.
[4] Freud S.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M].London:Penguin Freud Library,1933.
[5] Fanon F.Black Skin,White Masks[M].London:Pluto Press,1986.
[6] 文永超.“我想繪制……一幅批評地理的地圖”——論《所羅門之歌》的場域依戀與美國身份構建[J].當代外國文學,2022(3).
[7] Freud S.The Ego and the Id[M].New York:Norton,1960.
[8] 荊興梅.莫里森筆下城市新黑人的轉型焦慮[J].外國文學,2019(4).
[9] Arendt H.On Violence[M].New York:Harcourt Braceamp;World,1970.
(特約編輯:張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