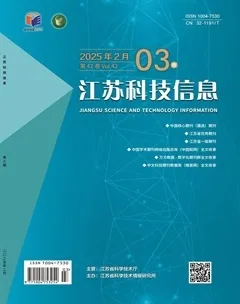公共圖書館協同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困境及因應之策

摘要: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文章以公共文化協同治理為論域,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協同動因-催化領導-制度設計-協同過程-治理效果”的修正模型,發現公共圖書館與國家文化公園協同過程中存在起始條件基礎薄弱、領導力作用有限、制度建設待完善、多元主體溝通不暢、評估反饋機制欠缺的問題,并提出議程共振、對話共鳴、多維互動、規制糾偏的優化路徑,以期提升兩者協同治理效能。
關鍵詞:圖書館;國家文化公園;協同治理;SFIC模型
中圖分類號:G25821文獻標志碼:A
0引言
國家文化公園是我國在《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中提出的基于大型線性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的原創性概念,旨在規劃建設一批國家文化公園,成為中華文化重要標識[1]。而公共圖書館作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平臺,在參與建設國家文化公園這一時代課題下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目前,部分學者對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進行了討論,其中:王星星[2]認為公共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主要表現為服務設施、資源、方式、業態多項融合;李叔鴻[3]重點思考了單一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背景下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創新發展;王協舟等[4]探討了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三館”協同參與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路徑等,多圍繞兩者發展模式展開研究,而對于兩者得以融合發展的理論邏輯探討相對較少。因此,基于協同學視角,嘗試應答在已有的公共圖書館建設體系上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理論依據,分析圖書館文化服務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融合問題及優化對策。
1理論基礎及適配性分析
在公共管理實踐中,人們開始關注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協同合作”重要性,系統性地提出了“協同治理”這一概念。
11協同治理理論
“協同治理”研究權威之一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Donahue等[5]最早在2004年使用這一概念,而后在一書中指明“一種特定的公-私協同方式,被稱為‘協同治理’”;Ansell等[6]認為其是“一種治理安排”;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認為“協同治理是個人、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全部行動”[7]。基于此,我國學者提出“協同治理=協同理論+治理理論”,即多元主體為提供公共服務或解決社會問題等共同目標而多方參與、雙向交流、權力分享的共同決策過程[8]。綜上,本文認為“協同治理”應當是在管理公共事務過程中,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和公眾等多元治理主體通過建立正式制度、進行協商對話后,以期聯合起來解決某項公共問題的過程。
12理論適配性分析
在公共管理視角下,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屬于社會管理職能活動之一,符合協同治理的理論內涵。首先,從主體立場來看,國家文化公園和圖書館都是國家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主體,在文化權益保障、文化傳承和文化自信塑造方面具有“載體-使命”的內在一致性[9];同時,兩者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公共產品屬性,具有“空間-服務”的耦合性,而治理理論能有效回應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低效的問題[10],最大程度地激發公共文化的歷史、社會資產和人文價值。
其次,從協同治理視角出發,符合文化治理范疇,文化協同治理是治理理論保障公民文化權益的創新性轉化;同時,在政府去官僚化和分權化的要求下,協同治理強調多元主體間的互構共生關系,這與公共文化建設的新要求是相通的。通過調動人財物各類資源,解決公共利益平衡、資源共建共享等現實問題,是一種理性、高效且持續的協作解決模式。
最后,結合當前研究現狀,“協同治理”已在政府與企業、非政府組織、公民之間跨部門協同合作得到普遍應用。我國在“圖書館+協同治理”研究中,關注圖書館聯盟[11]、城市閱讀空間[12]、智慧圖書館建設[13]等命題,在國家文化公園研究領域也多關注在協同學視角下的區域協同發展[14],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事實注腳。同時,部分地區圖書館以國家文化公園為主題,通過打造閱讀空間、舉辦閱讀推廣活動等形式進行服務融合,也為兩者協同治理提供實踐參照。
2基于SFIC模型的協同困境分析
21模型選擇
理論能為實踐的研究帶來理性的分析工具,構建模型可以幫助人們從應用可行性角度更好地分析協同治理的實踐過程。在協同治理理論中,來自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Ansell和Gash兩位教授通過對137個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政策領域的案例進行“連續近似分析”后提出了SFIC模型[6],具有較高的包容性和解釋力。但是該模型存在“缺乏外部環境因素、未擺脫‘線性結構’不足、忽略后果等”[15]遺漏,因此,在此進行適當修正,構建公共圖書館與國家文化公園的協同治理模型,如圖 1所示。在起始條件上將外部環境納入考慮,在原有基礎上嵌入對協同結果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總體來說,從組建協同動因、催化領導力、完善制度設計、優化協同過程、做好協同結果反饋5個方面來構建兩者的協同治理機制。
22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的協同困境分析
221協同動因:起始條件基礎薄弱
當社會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公共文化服務形成一定規模、主體之間具備一定合作基礎時,便會觸發協同動機。但是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協同基礎較為薄弱,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根據系統理論,組織處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環境之中,會受到政策、法律、經濟、科技等因素影響,因此,協同條件往往不對等;第二,國家文化公園呈現“線性文化遺產保護規劃”的條塊思維,各參與方資源稟賦差異、協同產出的預期、問題解決渠道多樣性、前期協作經驗等將制約協同的意愿及相互依賴程度。
222催化領導:領導力作用有限
從公共部門的角度來看,一項公共服務未進入政府議程設置之前,很難獲得真正的重視,這時就需要領導力的出現,這可能來自政府官員、智慧團、政治家等。國家文化公園無論實行的是中央垂直管理還是以地方為主的條塊管理,均是來自中央政府明確授權的管理機構進行的綜合管理[16],但是公共圖書館是按照法人治理結構進行管理的事業單位,兩者的管理邏輯、機制體制不同,因此,需要尋求兩者協同建設中值得各參與方尊重和信任的“領導力”來催化協同進程,同時又要注意避免陷入供給低效的內卷困境。
223制度設計:制度建設待完善
當文化管理部門、公共文化機構、文化創作者等多元主體在共同目標的驅動下,人們將會基于基本禮節與行為準則等內容進行制度設計,但是國家文化公園屬于新布局、新概念,制度設計多是以綱領性總體設計為主,即使目前部分地區將圖書館納入其中,但是出臺政策條文措施不夠具體;在公共圖書館領域,也尚未有一項完整的政策明確如何參與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體系;此外,國家文化公園是以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為主的領導小組統一領導,因此,公共圖書館作為不相隸屬機關,要思考在參與建設中如何掌握話語權,在制度設計中如何在充分吸納各方意見下避免“最小公分母式”的政策僵局。
224協同過程:多元主體溝通不暢
在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首先各參與方要在面對面對話的基礎上,就目標、組織安排、資源協調等內容達成初步統一。如果獲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那么將促進參與方的思想共識,繼續為總體目標的實現而努力,從而構成過程循環。但在有效參與方面,國家文化公園作為一個較為復雜的體系,涉及多個利益相關方,因此,在協同治理過程中要關注這些利益相關方不被排除在外,不僅有機會對方案提出意見,還能施加一定的政策影響。在思想共識方面,作為獨立組織,有著各自的目標和利益訴求,這種“自主性-責任困境”[17]的內在沖突會影響效能,因此,在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公共圖書館與其他參與方的利益訴求存在重大分歧時需要協調,思想共識才能達成理想狀態。
225治理效果:評估反饋機制欠缺
建立效果評估和信息反饋機制是實現協同治理科學化、規范化、長效化的重要抓手。在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實踐中,一方面,協同治理成效的評估標準滯后。在傳統的官僚制或外包中,各方職責界限比較清晰,但是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并不存在唯一的權威來確保參與成員的行為標準是否規范、行動是否一致,同時私人機構的參與也會擴大權責的規范空隙,這種情況造成了協同治理中評估關系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信息反饋機制不健全。協同主體在協同行動中應當對出現的問題及時總結,當目標出現偏離時應當及時向組織反饋,并尋找合適的方式予以糾正。
3圖書館協同治理國家文化公園的因應之策
基于上述命題的提出,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優化路徑進行思考。
31議程共振:構建主體協同發展格局
在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下,圖書館和國家文化公園作為我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應當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和體制機制創新。
一是要強化頂層設計。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管理機制按照中央統籌、省市負責、分級管理、分段負責的總體布局,而圖書館以“政府引導、聯盟合作、社會參與”的組織形式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2],因此,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應當貫徹多元協同共治,實現資源的有效集聚,注重分工優化和創新激勵,創造良好協同發展治理格局。同時在國家政策框架內,要及時出臺地方性政策,建立健全兩者融合發展的組織路徑和制度安排,維護協同治理的秩序和效果,通過高位協作來最大限度地消除地方性行政壁壘。
二是深化改革開放,推進改革舉措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科學規范。要推進“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角色從控制到協作的轉變,吸納其他力量共同參與國家文化公園的公共文化供給。同時推進圖書館法人治理結構改革,吸收有關方面代表、專業人士和社會公眾參與管理[18],利用集體的智慧對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進程中的關鍵問題進行集體決策,提升專業化水平。
32對話共鳴:回歸“價值共創”理性
圖書館參與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對要積極尋求協商對話、構建互惠關系以及相互學習,以此破除利益壁壘,回歸“價值共創”理性。
協同過程的有效推進,依賴于主體間的平等對話、理性協商。從對話的實現方式來看,一是發起多方參與的協商會議,有效地傾聽多方意見、剖析問題,從而制定行動目標、標準以及進程。在《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就初步確立了以聯席會議等為主的地方協調機制;二是組建聯盟,作為實現區域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促進整體發展的聯合體,已在圖書館界得到廣泛實踐。如多地成立了中部六省公共圖書館聯盟、“長征之路”圖書館聯盟。因此,要借助會議、組建聯盟的力量達成共識,促成有效協作。
互惠關系的構建基于各參與方的思想和物質層面。在思想層面,通過利益聯結的各參與方會發現各自的利益訴求是可調和的,通過加強內部交流和協商,尋求解決辦法,達成思想共識;在物質層面表現為成果的獲得,如果協同治理取得了具體的成果,可以認為獲得了組織或公眾認可、實現協同價值或達成計劃目標,從而鞏固合作關系,促進互惠關系的構建。
協同能力的建立和提升同樣會制約協作進程。對于組織成員而言,要提升溝通與協調、團隊合作、風險分析等能力;對于組織來說,要通過知識積累、知識轉換和知識創造的組織學習過程提升效能。因此,對于圖書館而言,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提升文化服務能力,創造性地融入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之中。
33多維互動:助力文化遍地開花
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圖書館和國家文化公園要樹立服務導向的思維范式,推動組織、技術、人力等多元素在資源、空間、活動等場景中積極互動。
資源是文化服務得以有效開展的基本保障。在公共資源統籌利用方面,公共圖書館要實現“條塊思維”到“資源整合”的轉變,通過對歷史文獻典籍的保護利用和新媒體閱讀推廣的融合,實現地方優秀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同時在數字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借助數字圖書館、智慧圖書館開拓文化服務內容,將諸多技術手段融入文化資源建設體系之中,如上海市圖書館建立紅色資源名錄數據庫,向公眾提供千余個紅色革命紀念地的信息。
空間場景是圖書館依托國家文化公園的文化意蘊進行文化傳播、感知和消費的呈現場所。一方面,可以依托場館進行空間再造和優化,打造以長城、大運河、長征、黃河和長江文化為主題的閱讀服務空間,如貴州省圖書館為助力長征國家文化公園(貴州段)建設,打造了長征文獻主題館。另一方面,國家文化公園各段建設中也可形成跨區域的線性閱讀空間,做好文化供給服務,對國家文化公園沿線的城市書房、農村書屋、流動點等場所建立“文化站”,如紅色書屋。
要創新和深耕以紅色文化、革命文化等文化精神為內容的活動,通過專題展覽、文創產品等形式助力服務供給,如2023年湖南省圖書館前往革命紀念地和國防教育基地開辦“讀步課堂·婁底”研學營。同時,公共圖書館將自身公共文化服務功能與國家文化公園文化主題相結合,能充分發揮其全民閱讀陣地和愛國主義教育陣地的作用。
34規制糾偏:尋求長效可持續發展
協同治理的策略特別適用于需要長期合作的情況,但是高質量發展視角下的可持續發展,是發展質量、動力、公平的有機統一。
一方面要遵循以問題導向為原則的合作方式,構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契合的評估方法和指標。多元主體間要加強階段性成果的回溯和檢驗,以客觀數據和主觀反饋進行項目總結,確保行動能有效進行。比如通過內部評價、社會調查、專家點評等進行描述性評估,通過專業的數據采集和分析工具進行定量指標化評估等。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各主體之間的責任考核和利益協調機制。一是要明確各主體權責,預防有利相爭、有責推諉的現象;二是要通過制度規則協調利益訴求,綜合考慮優勢互補和短板共克的原則,促成組織間或個體間本著互利和信任原則進行互動與合作;三是建立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打破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比如內部官員輪崗、績效責任共擔。
4結語
推動國家文化公園和公共圖書館的協同合作,消弭兩者協同建設困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仍然需要深入探討兩者協同合作的本質屬性和內在邏輯,不斷審視兩者在文化治理場域內制度、利益、權力和價值之間的博弈,以此尋求利益最大化,推動公共圖書館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建好用好國家文化公園的目標實現。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EB/OL].(2017-01-15)[2024-11-19].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1322.htm.
[2]王星星.公共圖書館與國家文化公園融合發展研究[J].國家圖書館學刊,2023(4):69-77.
[3]李叔鴻.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背景下公共圖書館服務創新研究:以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宜賓段為例[J].四川圖書館學報,2024(3):20-25.
[4]王協舟,殷韻潔.圖檔博(LAM)協同參與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價值取向、現實困境及推進路徑[J].檔案學研究,2024(1):102-109.
[5]DONAHUE J D, ZECKHAUSER R J.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M]//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96-526.
[6]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4): 543-571.
[7]全球治理委員會.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R]//俞可平.治理與善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8]周凌一.地方政府協同治理的邏輯:縱向干預的視角[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
[9]王星星.圖書館助力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理論邏輯、實踐樣態和基本策略[J].圖書館,2023(5):88-93.
[10]曹任何.合法性危機:治理興起的原因分析[J].理論與改革,2006(2):20-24.
[11]朱偉珠,李春發.服務于協同創新的京津冀跨區域公共圖書館聯盟平臺構建分析[J].現代情報,2017(10):78-83.
[12]董麗晶,謝志遠.協同治理視角下城市新型公共閱讀空間建設研究[J].出版發行研究,2020(1):74-77.
[13]王靜,宋迎法,李新春,等.基于SFIC理論的智慧圖書館建設過程中協同治理模式研究[J].圖書館學研究,2019(13):20-23.
[14]劉曉峰,孫靜.協同學視角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互嵌[J].東岳論叢,2022(9):104-110.
[15]田培杰.協同治理:理論研究框架與分析模型[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13.
[16]傅才武.讀懂國家文化公園[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3.
[17]TSCHIRHART M, CHRISTENSEN R K, PERRY J L. The paradox of branding and collaboration[J]. Public Performance amp; Management Review, 2014(1):67-84.
[18]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圖書館法[EB/OL].(2018-11-26)[2024-11-19].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2ZjEzNWY0NjAxNmYxY2U5MTcxNDExODE%3D.
(編輯何琳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