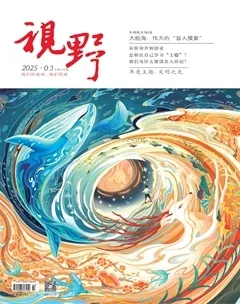大航海:偉大的“盲人摸象”

科學的精神,就在于懷疑,在于不停地找尋答案,拋棄成見。哥白尼懷疑托勒密的地心說,才有了日心說的說法。人們把物體下落看得理所當然,所以古人總擔心走到天邊會掉下去。西班牙宮廷的元老們在論證哥倫布跨越大西洋找印度的時候,才擔心船駛到地球的另一面會沒力氣爬升回來。及至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才找到了依據。然后這200年間人類就如同找到了世界運行的終極規律一樣自信地生活著。為了牛頓定律具有普適性,學者們還發明了以太的概念。直到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推導出了引力場,空間因引力而變形,才解釋了為什么引力能在太空空空如也的環境里傳導。但是愛因斯坦就觸及到了宇宙的終極真理么?
沒有懷疑,科學不會走到現在,人類對地球的認識,地理大發現其實也是一個不斷盲人摸象的過程。
盲人摸象的成語,在我們的語言里是一個不自量力、滑稽的行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但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何嘗不是如此。在這里,我愿把盲人的每次觸摸想象成獲取知識的一個步驟,一次探險。你永遠觸及不到事物的終極模樣,卻可以一次次地接近真實。
古代我們中國人對天地的想象是“天圓地方”,天空就像一個穹窿罩在地上,于是有了女媧補天的傳說。共工怒觸不周山是另一個和天地有關的傳說,共工是古代的水神,掌控洪水,他打仗戰敗了生了氣,撞向不周山,把支撐天庭的四個柱子中的一根撞斷了,天塌下來砸到了大地,大地傾斜了,從此水都往東流。既然天圓地方,大地是否有盡頭?盡頭處又是什么樣子呢?這里面我們中國人的禪機派上了用場,比如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到了天涯海角的五指山下,還是沒跳出如來佛的手心。但的確也有人曾經認真地擔心過到了地的盡頭會不會掉下去。
不管怎么說,即使憑直覺,古人都知道大地的盡頭是海洋,海洋的邊上是什么,古人就不清楚了。
關于地圓說,中國人似乎也是先行者。如東漢時張衡《渾儀注》里寫道:“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于內。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但表述又很模糊,和天體的樣子差得比較遠。
元代西域天文學家扎馬魯丁向元世祖忽必烈進獻西域儀象七件,其中就有地球儀。按《元史·天文志》的描述,這架地球儀“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湖海,脈絡貫穿于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這是700年前的事情。
不過即使到了西方傳教士帶來了地圓說的明代,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將信將疑的,比如明末大科學家宋應星著作《談天》,就專門評論道:“西人以地形為圓球,虛懸于中,凡物四面蟻附,且以瑪八作之人與中華之人足行相抵。天體受誣,又酷于宣夜與周髀矣。”
這里的宣夜與周髀指的是古人理解天的三種學說,一是蓋天說,二是渾天說,三是宣夜說。這三種對天文的認識是漢代的天文家提出來的,是國內最早的系統解釋天文現象的學說。按照蓋天、渾天的體系,日月星辰都有一個依靠,或附在天蓋上,隨天蓋一起運動;或附綴在雞蛋殼式的天球上,跟著天球東升西落。而宣夜說主張“日月眾星,自然浮生于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
那時候的中國人其實也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注意到月食是地球在月亮上的影子。
讓我們還是回到西方的大航海時代,畢竟東西方的各種天文地理學說駁雜多樣,如同漫天繁星,只是到了大航海時代才終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
自宋應星的年代再回溯100年,那正是西方如火如荼的大航海時代。就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1492年,德國人馬丁·貝海姆制作出一個存世年代最久的地球儀,地球儀上面寫一句話:“世界是圓的,可以航行到任何地方。”自然,哥倫布發現的美洲還沒來得及顯現在地球儀上。這個存世的地球儀,反映了不僅地中海上的兩顆“牙”,甚至更北的國家似乎都充滿了對世界探究的氣氛。
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兩顆“牙”就曾被來自地中海對面的北非摩爾人占領,到了15世紀,他們好不容易把異教徒趕走了,實現了復國。伊比利亞半島上,西班牙占了絕大部分地盤,葡萄牙面向大西洋偏安一隅,資源和人口都弱勢,這也就激起了王室的危機意識,恩里克王子一心想通過海洋來擴展版圖,找到國家的生存空間,一場盲人摸象從此開始。
葡萄牙的水手們要從非洲沿岸開拓出一條航路,橫亙于眼前的第一道障礙就是寬達1300至1900公里的沙漠,沙漠意味著岸上沒有補給,前路一片未知。非洲這片不毛之地上,一個海角深入大洋,這就是被稱為“死亡之角”的博哈多爾角,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這里是歐洲已知世界的盡頭。水手們傳說海角后面就是“黑暗的綠海”,其背后是太陽的領地,灼熱的陽光下海洋像開水一樣沸騰、翻滾,船只板壁和帆篷會燃燒起來,任何一個膽敢踏過這片洪荒之地的基督徒立即會變成黑人。1434年,葡萄牙航海者第一次越過了死亡海角,欣喜地發現一切如常,大航海時代正式開啟。
橫亙在葡萄牙水手面前的第二個任務便是繞過非洲。彼時的地圖上非洲大陸西海岸有一條通暢的水道,一直南下會到達一個通往印度洋的入口。幾十年后探險家迪亞士終于駕船來到了非洲南部的海域,當船隊航至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的水域時,海面狂風大作,驚濤駭浪,整個船隊幾乎覆沒,他們把這里命名為“風暴角”,為了吉利,葡萄牙國王若昂二世將這里改名“好望角”。迪亞士本來有希望沿著非洲東岸北上發現印度,可他的船員們歸心似箭,于是返航。開拓印度航路的任務落在了達·伽馬的身上,九年后達·伽馬率領艦隊經好望角成功駛入印度洋,兩年后滿載而歸。
非洲東岸以及東岸到印度洋的航線其實不難探尋,鄭和下西洋就曾經來到過這里,非洲人和印度人之間很早就有海上貿易,達·伽馬的成功就得益于一位得力的引水員。這里還要提到印度洋的季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三大洋中,唯獨北印度洋與眾不同,在冬、夏季風作用下形成季風環流。冬季夏季風向不同,正適合順風航行。阿拉伯人利用印度洋季風將伊斯蘭教傳遍了印度洋沿岸,鄭和下西洋也基本順著季風進行。
葡萄牙人完成了對亞歐航線的探險,但亞洲、歐洲和非洲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大陸,從古至今人員往來交流不斷,文化相互滲透,戰爭征伐不止,從地理學的角度看,新航線的開辟很難稱得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大航海時代最偉大的發現來自西班牙,一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第二則是麥哲倫的史詩級的環球航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他至死都以為是到了印度。為了紀念他的發現,其登陸的中美洲島嶼被命名為西印度群島。我們知道,中美洲是非常狹窄的一段地峽,歐洲的探險者因此有機會穿過陸地看到了太平洋。麥哲倫正是因此才堅信繞過美洲駛入太平洋,才能夠找尋到真正的香料群島。麥哲倫的航行歷時三年多,265人出發,回來的只剩下18人,他本人也因卷入菲律賓的部族爭端而殞命。
麥哲倫的偉大在于他在南美洲的最南端發現了大陸與島嶼之間曲折蜿蜒的麥哲倫海峽,從而完成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跨越。太平洋是所有大洋中最為浩瀚的,而美洲的土著族的文明還沒有進化到遠航太平洋的程度,哥倫布的船隊是在完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跨越大洋的。食物吃光,他們連船上的皮繩都吃掉了。船員大批死于壞血病,其慘烈程度任何此前的探險難以比擬。
正因為此,麥哲倫環球航行被譽為與登月相提并論的人類歷史上的探險壯舉。
(摘自《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