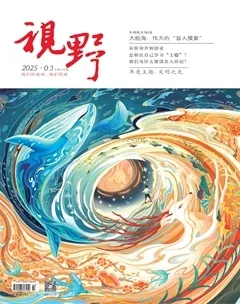乾隆十二年,他設計了一次科學檢驗

麥哲倫的船隊1521年完成環球航海,這個事件是貨真價實的“史上第一”,但他這個“史上第一”代價高得出奇。說的不是時間。耗時三年固然不短,但真正慘烈的是生命的損耗:船隊出發的時候有二百七十人,三年之后完成環球旅行回到西班牙時,總共只剩下十八人。除了一部分是航海過程中因為跟各地土著沖突而喪命,絕大多數船員死于壞血病。
他們患壞血病,因為缺乏維生素C。而缺乏維生素C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海上航行沒有新鮮蔬菜,也沒有新鮮水果。
那個時候,歐洲的航海技術已經相當發達,航船載重量不錯,能裝幾百噸東西,有食物,有飲水,但新鮮蔬菜和水果不會太多,因為當時沒有冷藏技術,保存時間有限。就那么一點水果蔬菜,還得優先保證大小頭目。水手們分不到多少,或者根本就吃不著。沒有新鮮蔬菜和水果,就沒有維生素C的來源。
維生素C為什么重要?它是合成膠原蛋白必需的成分。膠原蛋白是所有人體組織的粘合劑。你用磚砌墻,必須有水泥才能把磚塊給穩住了。人體各個地方的組織結構,必須有膠原蛋白才能保持結構穩定。
這不是說多吃點膠原蛋白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時海上航行缺乏蔬菜水果,但并不缺少肉食,肉食里面有膠原蛋白,可是海員們照樣出現壞血病。原因在于,膠原蛋白吃進肚子里之后,都會被消化分解,便不再是膠原蛋白,而只是零散的氨基酸分子。人體組織需要的膠原蛋白,都必須在體內合成。
人有生命,生命的根本特征之一是新陳代謝:舊的細胞不斷死去,新的細胞產生來填補空缺。膠原蛋白也一樣,舊的膠原蛋白不斷老化,新的膠原蛋白不斷合成來填補空缺。要合成膠原蛋白,需要有氨基酸做建材,更需要有維生素C做催化劑。
因為這個機制,就算海員們天天吃豬蹄也幫不上忙。吃下去的豬蹄分解成氨基酸,這只能提供建材,但沒有維生素C,就沒法合成新的膠原蛋白。這種狀況超過六個星期,人就要出現壞血病。
人若是患上壞血病,最早看到的癥狀是牙齦腫脹,這是因為牙齦里的膠原蛋白消失,牙齦無法保持正常,嚴重的時候牙齒會全部脫落。
接下來會看到皮下出血。這是因為,血管壁能形成一個密閉的管道靠的就是膠原蛋白。膠原蛋白不足,血管壁就出現縫隙,里面的紅細胞、血漿等等就會滲漏出來。當然這種情況不僅僅出現在皮下,只不過皮下比較容易被看到,所以我們能看到病人皮下出血點,出現瘀斑。血漿滲出還會造成身體組織浮腫。
關節是兩塊骨頭銜接的地方。這個地方的骨骼不能直接接觸,如果這么硬碰硬,很容易磨損。所以關節里有軟骨,起著襯墊緩沖和潤滑的作用。軟骨的主要成分就是膠原蛋白。膠原蛋白不足,軟骨就變薄、變脆,甚至可能破裂。那么關節一活動就會有劇烈疼痛。
這些情況如果不及時糾正,病人就會因為各個器官結構崩塌、功能耗損而死亡,或是就因為內出血過多而直接死亡。
但是,這些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醫學知識。在麥哲倫那個年代,也就是十六世紀的時候,沒人知道壞血病是因為這個引起的。他們只知道出海的人,在海上待了大約兩個月之后,就會出現上面說的這些恐怖癥狀。那個年代的船員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離奇故事:在茫茫大海上看到一艘無目的飄泊的船,登船之后看到全體船員死亡,身上沒有暴力傷痕,如果仔細看,可以看到尸體都有腫脹的牙齦和脫落的牙齒。
關于壞血病本身的觀察已經很有歷史了。希波克拉底在兩千五百年前記載的一些疾病,從癥狀看應該就是壞血病。歐洲人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對壞血病有明確的記載。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的海軍船艦建造得很不錯,戰斗力還是可以的,但是他們的水兵卻不斷有人死亡,不是在戰斗中戰死,而是因為患上壞血病,病死的。
壞血病的原因,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沒人知道。當時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病人血液腐敗了,于是產生了“壞血病”這個名字。這本來是個舊時代產生的名詞,不過一直沿用下來了。
至于血液“腐敗”的原理,都是古代那種基于冥想的清談。清談大多聽起來有道理,就是沒法用客觀檢驗來證實,結果就是每個大師都有一種不同的理論,誰都說服不了誰。
病理知識糊涂,治療方法也就糊涂。醫生遇到壞血病人,就只能盲目嘗試各種東西,啤酒、威士忌、水芹、水苦荬,什么都試過,為增加成功率,多半是十幾種,甚至幾十種東西一起給病人吃。有時候還真看到療效,比如他給病人吃的東西里有檸檬,那么這確實能讓壞血病好轉。問題是,他給的東西太亂,即使看到癥狀好轉,他也沒法判斷到底是里面哪種成分起了作用。
這么糊涂了幾百年,后來是一位叫林德(James Lind,1716-1794)的醫生改變了局面。
林德是蘇格蘭人,他少年時的志向是當外科醫生。那時候的歐洲,要當外科醫生,不是到醫學院上學,而是跟外科醫生當學徒。1731年,林德成了這樣的一名學徒。二十三歲那年,他出師了,取得外科醫生資格,就到英國海軍當外科醫生。
海軍的心頭大患是壞血病,這在前面已經提到,所以林德很快就面對大量壞血病人,這就必須想辦法。他試了許多當時流傳的治療方法,沒看到療效。但他從文獻里看到,過去做過的各種嘗試里,確實曾經有過見效的時候,說明那些嘗試過的方子里,肯定包含有效成分,問題在于怎么能把那個有效成分給抓出來。
于是,1747年,也就是我們這兒的乾隆十二年,林德設計了一個檢驗。他找來十二個癥狀很嚴重的壞血病人。這個人數本身就值得注意。古人探索藥物,都是盯著一個病人用藥,他卻一次找來十二個病人,這就是一個重要的思維方法突破。
接下來他給病人分組,分作六組,每組兩個人。這十二個病人,每天正餐內容一樣,今天吃土豆就全吃土豆,吃面包就全吃面包。不同的地方是,他給每個組不同的輔助食物,行話叫輔食。每一組的輔食內容是:
第一組,每天一杯蘋果酒;
第二組,每天一杯醋;
第三組,每天一杯二百四十毫升的水,里面加幾滴硫酸;
第四組,每天一杯海水;
第五組,每天一杯大麥茶加一點辣醬;
第六組,每天一個橘子、一個檸檬。
關于實驗里用到硫酸,大家不用擔心病人會被灼傷。我們身體里的胃酸,成分其實是鹽酸。鹽酸跟硫酸都是強酸,但只要濃度足夠低,對人體并沒有什么傷害。
這里面大部分東西都含酸,這是因為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壞血病由血液腐敗引起,而酸性物質可以扭轉血液的腐敗。
第四組用的海水不含酸,林德之所以選它,或許是因為這東西對海員來說唾手可得,如果真能有用就太方便了。第五組里的辣醬里含有一些醋。至于大麥茶,就不知道林德是怎么選中的了。從現在我們對它的了解來說,大麥的維生素B含量頗高,對腳氣病有好處。但大麥里的維生素C含量基本是零,對壞血病是沒有幫助的。
實驗做到第六天,做不下去了,因為他開始實驗的時候,船出海已經兩個月,儲備消耗了不少,到第六天,橘子和檸檬沒了。這個沒了,其他的幾個組也就沒必要繼續。好在這時候,他其實已經看到了結果。什么結果?吃橘子和檸檬的那一組,其中一個人已經恢復得很不錯,可以回去工作。另一個也幾乎完全康復。
至于別的組,除了喝蘋果酒的那組稍微有一點好轉,另外的那四個組,病情都在繼續惡化。
林德把實驗結果寫成論文發表了,但是并沒有引起重視。他的實驗結果本來足可以說明問題,只是那時候的病理學知識還停留在古代水平,結果他的實驗結果正確,他給出的解釋卻是錯誤的。他用當時流行的“酸性”來解釋橘子和檸檬的療效:橘子和檸檬為什么能治療壞血病?因為橘子和檸檬是酸的,這能讓病人的血液“酸化”。這么解釋就留下了漏洞。別人看到他的論文,就提出質疑:如果是因為酸性在起作用,為什么喝醋和硫酸的那兩組沒有療效?
這林德就沒法解釋。
更糟糕的是,他后來試圖改進橘子療法的時候,做出的努力弄錯了方向。為便于讓海員攜帶,他把橘子榨汁,然后把橘汁加熱濃縮。那時候化學知識還很落后,林德不知道維生素C怕熱,一加熱就被破壞了。所以他建議海員喝濃縮橘汁,卻沒有看到預期的療效。結果林德在世期間,一直沒能說服別人接受他的理論。
直到他去世之后,后人觀察到越來越多的實例,才覺得林德應該是對的,于是有人重復他的實驗,最后證實柑橘類水果確實能治療壞血病。那以后英國海軍就做出規定,遠航船隊必須攜帶足夠的柑橘類水果。后來民間船隊也模仿這個做法,又因為新鮮水果不好攜帶,探險家庫克還找到一個更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檸檬汁加到朗姆酒里。
因為那時沒有飲水消毒技術,從河里取來的水時間長了往往變質,滋生微生物和霉菌、水藻什么的,所以那時遠航船的飲料很大一部分是酒。庫克把檸檬汁加到酒里,既可以讓檸檬汁不那么容易變質,又提供了維生素C的來源。從那以后,壞血病就慢慢給控制住了。
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林德的實驗設計不算完美,但在那個時候,卻是個非常好的開端。因為,他的這個實驗,是歷史上第一次嘗試用系統方法檢驗藥物療效。
什么叫“系統方法”?通俗地說,就是用一切能想到的方法來排除偽療效。
醫學跟物理學等自然科學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人體有免疫系統,人腦受心理暗示。免疫系統能消滅入侵微生物,讓疾病自然康復。比如有一種病毒,感染人之后,97%的情況下,人都可以靠免疫系統的反擊而自然康復。如果這段時間病人正在吃香蕉,他可能就以為是香蕉治好了他的病。這就是偽療效。
而人如果對某個治療方法特別有信心,即使這種療法并沒有療效,他的信心也可以讓癥狀暫時減輕。這是另一種偽療效,醫學上叫作“安慰劑效應”。藥物療效的系統檢驗方法,就是從各個角度挑戰自己的結論,為的就是怕自己被偽療效蒙蔽了。
林德是最早嘗試系統檢驗的,他的做法還很粗糙,但已經有了系統檢驗的若干要素,具體來說有這么幾條:
第一,他不是只用一個病人做治療,而是同時用十二個病人。在現代研究方法學里,這個概念叫作“大樣本”。大樣本的意義在于能夠減少意外因素的干擾。如果實驗里只用一個病人,這個病人有可能是誤診,不是真的壞血病而只是口腔潰瘍。如果是這種情況,你就算只給他喝白開水,過幾天他的牙齦也就不腫了。但是這不能證明白開水可以治療壞血病。或是這個病人患病不是因為吃不到水果,而是因為胃腸有問題,不能吸收維生素C。那么你給他吃多少橘子都不行,必須繞過胃腸道,從血管注射維生素C才可能解決問題。而這種情況并不能否定“橘子可以治療壞血病”的結論。為了避免這些干擾情況,就需要找來多個壞血病人,同時治療。畢竟這么多人,個個都誤診或是個個都有胃腸吸收問題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第二,實驗對象分成若干個組,以便對比治療效果。這就是“對照組”概念的雛形。在古代,醫生們不停嘗試各種物質,試圖找到治療作用,一旦看到癥狀減輕,就認為是治療有效,卻沒想到用對照組來重復檢驗。實際上這樣的療效一旦用對照組來檢驗,很容易就能看到,同一種疾病,不管吃不吃哪種草,都是過這么幾天癥狀就會好轉。當初之所以看到那樣的療效,其實只是因為免疫系統在起作用,或者僅僅是一時的安慰劑效應。
第三,參與實驗的十二個病人,除了實驗設計里要試用的六種待檢驗輔食不一樣,其他的條件都盡量地一致:正餐的內容一樣,生活起居規律一樣。六個組里病人的病情輕重也大致對等。這一點也很重要,學術上叫作“條件控制”。如果沒有這樣的條件控制,讓病人自己決定每天的主食吃什么,那么今天約翰可能吃土豆,馬克可能吃燕麥粥。這么隨便吃,等到第六天,看到病情好轉,我們就沒法知道病人是吃柑橘吃好的,還是吃燕麥粥吃好的。為避免這樣的混亂,實驗期間就必須嚴格控制條件,排除這些干擾因素。那么如果療效有區別,就只能用這些輔食來解釋了。
第四,針對同樣的一個實驗目標(這里就是壞血病),用若干種不同的(但是根據現有理論,似乎是很有希望的)備選藥物來進行“攻擊”,對比變化,找出最有效的藥物。這有點亂槍打鳥的味道,但確實可以提高檢驗效率。實際上,即使在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做法仍然是探索新藥的一種重要方法。如今藥物研究的尖端技術之一——高通量篩選,其實就是大規模的排槍掃射。
這些檢驗原則后來進一步完善,有了更多的堵塞偽療效的做法,這里介紹其中比較重要的三個:
1.隨機:樣本選取應該隨機。就是說,不能只挑選具備某種品質的實驗對象。比如,若檢驗一種藥是不是能讓人有力氣,要是選來做實驗的人全都是特種兵,這樣的實驗設計就毫無意義。
2.量化:測試的標準必須是可以測量的。比如壞血病的檢查,應該包括牙齦腫脹是幾個毫米,甚至牙齦的顏色也可以用比色表來量化。能量化的檢驗才可能提供可靠的結論。無從量化的描述,比如“皮膚比以前更年輕了”,能讓關注容貌的潛在買家動心,但是得不出科學的結論。
3.可重復性:真正科學的結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可以重復。誰號稱一個驗證得到了陽性結果,那么別人照著他描述的方法再做一遍,應該也能得出同樣的結果才行。所以科學檢驗都必須有完整的實驗步驟。倘若只是說“我們已經通過獨家操作去掉了這種成分的毒性”,那只能算營銷用語,不是科研。
林德受當時錯誤醫學理論的限制,并沒能立即說服人們用橘子治療壞血病,但他的實驗仍然被后人認作醫學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因為,他最大的功勞不是發現橘子的療效,而是引領了科學檢驗藥物療效的方法。
對于林德來說,沒能證實橘子的治療功效,大致相當于失去了一條魚。而他開創了藥物療效的科學檢驗方法,可以說相當于找到了一種全新的打漁技術。林德當時沒能用這種打漁技術打到那條大魚,并不是說他的方法不對。他的挫敗只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而且他自己對這種全新打漁法也還沒太熟練掌握。人類歷史上無數革命性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研究方法,在剛剛誕生的時候都是很粗糙的。但是對于這些技術和方法來說,最珍貴的不是后來的發展和完善,而是當初有人能“想到這一點”。
林德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想到的系統檢驗藥物療效的方法,讓醫學擺脫了個人感悟時代,走進了科學驗證時代。這樣的檢驗技術,讓醫學界能摒棄那些謬傳幾千年的無效古方,探索出真正有效的現代藥物。
(奕辰摘自新星出版社《醫學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