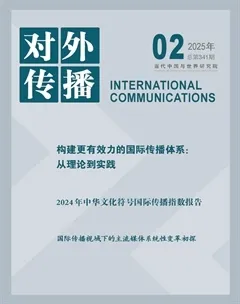建構復合城市景觀:城市跨文化傳播的新路徑
【內容提要】在當代城市中,物理城市場所和虛擬空間在媒體技術的中介下彼此糾纏,城市空間成為被媒介中介化的復合空間景觀(spatial hybrid)。基于此,本文梳理分析城市國際傳播效果突出的典型案例,探討在中國數字城市空間中,民眾、企業和政府等不同主體作為城市策展人如何構建城市跨文化傳播新機制及其傳播效果。通過數字技術將現實城市空間延伸至虛擬城市時空,多重主體的中介化實踐共同書寫“物質—虛擬”復合城市景觀,從而在交互空間中產生跨文化認同。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提出了中介化視角下城市跨文化傳播的新路徑。
【關鍵詞】復合城市景觀 跨文化傳播 中介化 數字城市空間
2024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推進國際傳播格局重構,創新開展網絡外宣,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格局。①提升中華文化傳播力影響力的時代要求為城市國際傳播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與發展方向。城市作為文化承載者、行動者、建設者、展示者,②為中華文化的國際敘事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與廣闊的空間。這些城市不僅是國際傳播的重點場域,還在連接過去與未來、東方與西方方面發揮著橋梁作用。通過打造反映中國式現代化成果的國際城市形象,可以向世界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價值與生活方式,展示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蘊含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
在全球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城市借助5G、算法、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術開展跨文化傳播與營銷,重構人與媒介、技術、文化、空間和傳播之間的關系,開啟新時代中國城市國際傳播的新篇章。一方面,社交媒體等數字媒介成為中國城市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場域。上海、杭州和廣州等城市通過舉辦國際活動提升知名度,將自然風景與短視頻結合,制造視覺盛宴;宣傳城市特產,打造獨特名片;并結合當下發展理念,樹立綠色城市、智慧城市的形象,③展示出城市在“物質—虛擬”空間中的傳播力、包容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媒介的物質性為重構城市形象增添了新維度,地標建筑、城市之光、大屏幕、霓虹燈、輕軌、地鐵、共享交通工具等城市空間媒介物作為線上線下復合空間的接口,④展現出數字城市的可溝通特性,重塑了新時代城市形象的傳播與數字景觀。
伴隨城市數字化進程,政府部門、媒體、文化機構、企業和民眾等不同主體逐漸成為城市形象建構與傳播的核心參與者,城市國際傳播的主體性問題變得日益重要且復雜。隨著中國政府放寬入境政策,越來越多外國游客來華觀光旅游,各城市借機傳播特色文化活動,增強城市海外關注度;海外游客發布的“China Travel”(中國游)系列短視頻火爆全球社交媒體,進一步增加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同時,中國企業作為城市的物質聯通橋梁和精神文化紐帶,成為中國城市景觀的重要策展人,如中國東方航空積極構建聯通全球的“空中橋梁”,充分發揮企業海外社交平臺矩陣優勢,探索物質與虛擬空間融合的多模態跨文化交流方式。城市國際傳播的主體性建設,不僅僅是簡單的傳受關系或形象投射與受眾認知問題,⑤而是媒介、空間、經貿、交往、文化等多個層面的主體關系網絡編織,構成了城市品牌傳播的內在支撐。
基于此,本文將以中介化為視角,分析在物理城市場所和虛擬空間交織的數字城市空間中,不同主體如何作為數字策展人利用數字技術延伸現實城市時空至虛擬城市時空,建構城市跨文化傳播的新機制。通過分析典型案例,探討中介化實踐下“物質—虛擬”復合城市景觀的跨文化傳播效果,分析中國城市跨文化傳播的新路徑。
一、數字城市:城市空間的復合轉向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數字化進程的加速,城市空間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的普及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定義和體驗,使其不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延伸,而是形成了一個虛實交織的復合城市景觀。澳大利亞學者斯蒂芬·歐文(Stephen Owen)和羅伯特·伊姆雷(Robert Imre)提出的“復合城市空間”概念為理解這一轉變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他們在2013年的研究中指出,復合城市空間是指社交媒體和數字技術如何調節現實城市環境,并探討了人與數字技術之間的互動關系。歐文與伊姆雷強調,復合城市空間的出現不僅是技術進步的結果,還反映了社會文化對城市空間的深刻影響。⑥他們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在數字化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間如何被重新定義和體驗,以及這對人們社交行為和空間認同的影響。加拿大學者安娜貝爾·泉-哈斯(Anabel Quan-Haase)和學者金·馬丁(Kim Martin)的研究進一步擴展了這一視角。他們通過對危地馬拉城市節日的案例分析,揭示了城市空間中的物質與虛擬之間的緊密聯系。研究表明,城市節日從傳統的城鎮廣場延伸到在線空間的過程,反映了城市空間的復合性。當代城市空間不再是簡單的物理場所和虛擬空間的對立體,而是一個兩者交織的復合體。通過對當地傳統節日圣托馬斯節的數字化擴展研究,泉-哈斯和馬丁分析了旅游公司、游客和當地居民如何通過不同的數字策展,將虛擬空間納入城市節日體驗中,并探討了這一過程對城市空間的認知和體驗的影響。⑦此外,芬蘭學者里德爾(Ridell)和英國學者澤勒(Zeller)的研究中進一步發展了“中介化城市主義”(mediated urbanism)的概念,強調了數字技術和媒介在塑造與重構城市空間中的核心作用。中介化城市主義強調,城市空間不僅是一個物理場所,同時也是一個受到數字媒介與技術深度介入的多層次、多維度環境。⑧這一概念為理解數字技術如何重塑城市空間的結構與功能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揭示了技術變革如何改變人們對城市空間的感知和互動方式。
這些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和社交媒體在城市空間中的作用已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應用層面,形成了一種新的城市景觀。復合城市空間的概念不僅為理解當代城市環境提供了新視角,也為探索數字技術與城市空間之間復雜互動的理論框架奠定了基礎。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應用的不斷深化,未來的城市空間將愈發復雜多元,數字和物質的界限將更加模糊,這為城市傳播研究帶來了新的挑戰和機遇。
二、城市空間生產及其跨文化傳播
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關于空間和城市的思考,對現代城市研究(urbanology)產生了深遠影響。他認為,空間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空洞的連續體,它是在人類活動和社會互動中不斷被生產和再生產的。這一觀點強調了空間的動態性及其與社會實踐的密切關聯,尤其是在理解城市環境的構建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空間可以被視為一種社會產品,意味著每一個空間都是過去與現在社會力量關系的產物。⑨他指出,空間不應被設想為由人、物體和行動填充的靜態空洞連續體,而應被視為在人類活動和互動中不斷生成和重構的過程。在城市中這一關系尤為突出,因為城市空間不僅承載了物質結構,更充滿了社會關系和權力動態。城市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通過社會實踐、經濟活動和政治權力的互動得以實現。
列斐伏爾的理論框架為理解當代中國城市空間的再生產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持。與列斐伏爾的觀點相呼應,學者米歇爾·德塞托(De Certeau)進一步闡釋了城市空間的動態性。德塞托認為,城市是在普通居民的日常互動與敘事過程中被逐步構建的。⑩城市不僅是建筑物和街道的集合體,更是居民生活的舞臺,是日常生活故事的書寫地。在這種觀點下,城市空間被視為動態的文本,城市居民既是作者也是讀者,通過日常生活實踐不斷編寫和重寫這本“城市之書”。在這一從下而上的城市空間生產過程中,城市的日常性和居民的主體性得到了突出強調。城市不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充滿了變化和動態的交流場所。德塞托對城市空間的理解還凸顯了跨文化認同的生產。在多元文化的城市環境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通過日常互動形成了復雜的社會與文化網絡。這些網絡不僅僅表現在物理空間的共享上,更體現于文化意義和社會身份的互動中。城市空間因此成為多元文化交流和認同構建的場所,城市居民通過日常社會實踐不斷談判、交流并重塑他們的文化身份。
復合城市空間的概念強調數字技術與城市空間的相遇。實體城市演變為“物質—虛擬”的融合時空,并通過數字媒介實現城市景觀的中介化。即是說,當下的城市空間性本質上是通過媒介和技術的中介活動(再)生產出來的。11 基于這一城市媒介觀,空間生產理論強調,城市景觀由過去的自上而下的物質建構演變為自下而上的多主體復合生產。城市景觀在此過程中打破時空和物質界限,形成跨文化傳播和認同。
三、城市中介化實踐中的跨文化傳播
(一)“物質—虛擬”空間:以城市符號建構復合傳播景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的中介化實踐已成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手段。通過不同主體的數字策展,多樣化的符號塑造了獨特的復合城市景觀,成功實現了跨時空的文化傳播。海外民眾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他們在中國城市中的親身經歷,已成為復合傳播的重要力量。伴隨中國游的復蘇,一些外國博主在中國旅游時拍攝的“city不city啊”“好city啊”相關短視頻走紅社交媒體,引起中外網友的廣泛轉發分享。這些外國游客將他們在中國實際享受的美景美食,親身感受到的生動真實中國發布在社交媒體中,利用社交媒體等更加分布式的通信范式實現從現實到虛擬的緊密中介化實踐,構建客觀、真實的中國復合城市形象。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航企業積極開展融媒體內容生產與線下主題活動,扮演著城市對外窗口和溝通紐帶的角色。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之際,中國東方航空推出《十城十遇》系列視頻,帶領網友深入十座中外名城。通過沉浸式體驗城市魅力,以多視角、多維度和多平臺講好中國故事,促進文化融合與交流。在可視化聚合傳播基礎上,民航企業可以依托客艙、機上娛樂系統等民航業獨特的物理空間,打通線上線下壁壘、打造沉浸式體驗。在東航新設的“威尼斯—上海”航線上,乘客可借助機上Wi-Fi實時訪問上海市對外信息服務平臺,瀏覽關于上海城市生活和文化介紹,開啟對上海的探索之旅。此外,“西安—米蘭”主題航班活動為國際旅客營造了獨特的復合城市跨文化體。登機牌、美食和定制紀念品等各種中意元素的巧妙融合,搭建了物理空間的文化連接點。海外社交媒體賬號發布的新航線相關帖文也得到海外網友熱情點贊和官方機構的互動轉發,使得線下航班活動的文化交流價值在虛擬網絡空間中得以延續,激發更多海外受眾形成更鮮明、深刻的中華文化認知。
政府和民間文化機構亦是城市中介化實踐中的關鍵主體。南京作為X平臺傳播力指數第一的中國城市,緊跟國內外熱點策劃了系列活動,吸引了眾多粉絲。圍繞“2024南京軟件大會”,南京官方賬號發布了關于人工智能和虛擬現實技術的應用視頻,展示了南京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實力,同時通過互聯網傳播至全球,提升了南京作為科技創新城市的國際形象。這些活動不僅提升了南京的國際知名度,也加深了全球觀眾對這座城市多元文化和體育活力的認識。
這種自上而下加自下而上的集合傳播模式,不僅強化了中國城市的國際形象,為全球觀眾提供了深入了解和體驗城市文化的機會。通過這一機制,動態生成的復合數字空間從官方到民間、從宏觀到個體、從觀看到參與、從線下到線上,形成了更加立體的傳播模式。
(二)空間生產:復合空間交互中的跨文化認同
在全球化、媒介化和數字化的背景下,城市跨文化傳播愈發依賴數字技術,將現實城市延伸至虛擬城市時空。由此建構的“物質—虛擬”復合城市景觀不僅拓寬了信息的傳播渠道,也使得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和深入,從而建構中國城市在國際傳播中的跨文化認同。
作為自下而上的傳播主體,民眾在中國城市跨文化認同建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外國人游中國”短視頻在全球社交媒體的流行。外國游客作為跨文化體驗者,以“他者”視角記錄并展示其在中國的真實體驗,因其獨立、客觀的立場更容易獲得海外觀眾共鳴與互動。這些視頻的觀看、分享與評論行為,使海外用戶實現跨文化在場,并巧妙地以視頻發布者作為中介,建立起共情傳播機制。來自愛爾蘭的一對夫婦記錄了他們2024年在中國城市的旅行經歷,相關視頻在社交平臺上獲得了超27萬人次的點擊量,顯示出外國觀眾對真實中國生活的強烈興趣。這種跨文化的復合傳播模式不僅打破了長期被扭曲甚至被妖魔化的中國形象,更通過“他者”視角巧妙解決了文化折扣問題,幫助更多國際民眾了解中國、讀懂中國。
企業在城市跨文化傳播中為海外民眾提供了文化交流與認同形成的溝通渠道。東航通過線上聚合呈現加線下主題航班成功結合了航空服務與城市文化傳播,不僅在線上引發網友積極互動,并在線下受到旅客好評,有效展現出中華文化的多元魅力。2024年,東航推出AI城市策劃活動,結合海外社交媒體的熱點話題#ChinaTravel制作《翼起出發:測測你會來到中國哪座城市》特效濾鏡,點燃全球用戶對中國城市的興趣。隨后發布的系列短視頻通過第一視角展示六座城市的風土人情,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有機結合,生動展現中國的經濟活力與文化底蘊,海外受眾反饋“中國是非常美麗的國家”,這些積極反饋顯示出海外觀眾對中國城市形象的認同感不斷增強。
中國的發展速度和開放的營商環境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從“China Travel”到“China Investment(中國投資)”,甚至“China Life(中國生活)”,中外合作共贏的故事成為展示中國經濟實力和包容友善的營商環境最有說服力的生動案例。
政府和媒體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和專業力量,在跨文化傳播中扮演著自上而下的重要角色。在云南大象遷徙的國際傳播中,各級媒體紛紛聯動策劃,通過應用具有跨國文化共性的多模態傳播話語,并結合大數據、基于位置服務(LBS)和5G等技術,使全球網民得以云端追蹤大象遷徙。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紛紛表示“云南象太可愛了”“被中國大象所治愈”等,并稱贊中國對象群的保護成效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這種柔性復合傳播方式不僅展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愿景,還傳遞了中華文化中的普世價值。
此外,政府和媒體還與本地企業合作,建構多主體的聚合傳播機制,推動城市國際形象的塑造。202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聯合上海文廣國際傳播中心發布國際版上海城市形象片“GO AND SEE SHANGHAI”(去上海)。該短片以兩位外籍關鍵意見領袖為主角,通過他們在東航航班上的對話,引發了國外游客對上海的好奇和期待。在這3分鐘的視頻中,上海的人文景觀、文化生活與美食體驗被巧妙串聯起來,展現了上海作為現代化大都市的獨特魅力。這一系列宣傳片發布后,引發了海外受眾的熱切關注,并成功推動了上海的國際傳播。
民眾的自發分享、企業的戰略策劃以及政府和民間機構的官方推廣,共同構建起復合城市景觀,推動中國城市的跨文化傳播和國際認同的形成。這種復合空間中的交互,不僅為文化傳播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也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
(三)空間實踐:城市跨文化傳播路徑
1. 建構集合傳播主體
伴隨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與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城市跨文化傳播的主體越發多元,各方力量共同參與中國城市形象的建構。但當前傳播學對城市傳播主體的研究視角仍顯得原子化與分散,缺乏對不同傳播主體之間聚合與聯動的思考。雖然不同主體的傳播行為均有“出圈”案例,但這種單打獨斗的傳播模式往往不成規模,效果有限。在信息量爆炸、渠道多元、傳遞迅捷的數字時代,單靠民間自上而下或官方自下而上的傳播行為都無法實現最佳傳播效果。近期,海外社交媒體中國旅游短視頻受到了全球網民的喜愛,這不僅歸功于中國持續優化的人員往來便利措施和地方政府和民間機構的旅游宣傳,也離不開外國游客自發在社交媒體中的傳播行為——是各傳播主體協同努力的成果。因此,建構和傳播立體、全面的中國城市形象需要政府部門、媒體、高校、文化機構、民營企業和民眾等多元傳播主體之間的頻繁互動與廣泛協作。
2. 挖掘中介化實踐中的“物”
近年來,媒介研究的“物質性轉向”引發了對城市傳播新路徑的思考,這要求在傳播研究中,關注任何一個在城市空間中“會說話”的物質存在。從城市中的地鐵、公交、共享單車等移動實踐,到數字屏幕、霓虹燈、城市之光等城市景觀,所有這些媒介構建了人與城市之間的多層次交互,賦予城市傳播實踐新的物質性維度。這些實踐不僅涉及人的移動和信息的流通,還與意義的共享密切相關。目前,我國已開始在全新的城市研究范式下,探索數字城市傳播創新路徑。近年來,紐約時代廣場的電子屏幕頻繁展示中國元素,“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也逐步建成了多條中國基礎設施。2023年,深圳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操控1500架無人機上演“飛龍在天”的燈光秀,以頂級視覺效果展現了數字深圳的獨特魅力。在這些案例中,電子屏、飛機艙、無人機等作為重要的媒介物,打造出中華文化與外國受眾相遇的多元場景,講述中國的故事。
3. 打通國內、國際傳播邊界
伴隨國家行為體、全球網民和各類組織機構深度參與全球傳播,信息的流動、互動和反饋機制發生巨大變化。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和大眾傳播不斷整合,復合城市景觀中的國內、國際界限也逐漸被打破。大象遷徙事件的傳播模式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本是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媒介事件,卻在多個主體的共同作用和互動下打破了時空限制,迅速成為全球關注的熱點事件,激發了全球的情感共鳴。相反,近年來中國國內許多熱門城市IP,如淄博燒烤、甘肅天水麻辣燙等,雖然在國內市場引發了熱烈反響,但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上的傳播效果有限。城市傳播是國際傳播的重要議題,如何有效打通中國輿論場和全球輿論場,真正實現國內傳播與國際傳播的融合,是未來城市跨文化傳播面臨的關鍵挑戰。
四、結論與討論
在當代的城市傳播研究中,中介化城市景觀的構建及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本文探討了如何通過物理與虛擬空間的互動,以及多元主體的參與,形成一種全新的中國復合城市空間。這一空間不僅重塑了城市的物理與文化景觀,也重新定義了中國城市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角色與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不同主體包括民眾、企業、政府和媒體各自扮演了獨特的角色。民眾通過廣泛使用社交媒體,成為跨文化傳播的自發推動者。他們的實地體驗和直接分享,在全球范圍內塑造了關于中國城市的多元而真實的形象。企業通過策略性的文化傳播活動,將商業行為與文化推廣有效結合,增強了城市形象的國際吸引力。政府、文化機構和媒體則通過自上而下策劃并支持各種文化活動,支撐起城市文化的系統性國際傳播。通過多元主體的集合傳播實踐,城市不再是單一的物理空間,而是一個動態的、多層次的、互動的復合體。這種轉變不僅增強了中國城市的國際傳播能力,也加深了全球公眾對城市文化的理解和認同。在這個過程中,城市的中介化實踐成為文化交流和傳播的新場域,城市形象的傳播更加深入人心,文化的傳播更加立體化、全球化。
城市的中介化傳播實踐是理解和應對全球性挑戰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和主體間的互動,城市能夠在全球舞臺上更好展現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和發展成就。未來的中國城市傳播研究應更加關注如何通過技術手段與策略性規劃,完善中介化傳播機制,以使中國城市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吳璟薇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長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閻慶宜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曹偉系中國東方航空集團黨組宣傳部媒體關系分部高級經理
「注釋」
①《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錨定建成文化強國戰略目標 不斷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 cn/yaowen/liebiao/202410/content_6983529.htm,2024年10月28日。
②《「理響中國」以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引領,加快推動城市文明建設》,光明網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9276770042907353wfr=spiderf or=pc,2023年6月21日。
③《2023中國城市海外網絡傳播力十大案例發布 泉州光榮上榜》,《東南早報》百家號,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8361268880467281wfr=spiderfor=pc,2024年1月18日。
④《新時代城市形象的傳播與數字場景重構》,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s://www. cssn.cn/xwcbx/cbx/202301/t20230103_5577757.shtml,2022年5月24日。
⑤姬德強、閆伯維:《在本土與全球之間:城市國際傳播的主體性構建》,《青年記者》2024年第4期,第89-93頁。
⑥Owen, S. Imre, R.,“ Little Mermaids and Pro-sumers: The Dilemma of Authenticity and Surveillance in Hybrid Public Space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5, no. 5-6, 2013, pp. 470-483.
⑦Quan-Haase, A. Martin, K.,“ Digital Curation and the Networked Audience of Urban Events: Expanding La Fiesta de Santo Tomás from the Physical to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5, no. 5-6, 2013, pp. 521-537.
⑧Ridell, S. Zeller, F.,“ Mediated Urbanism: Naviga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Terrai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5, no. 5-6, 2013, pp. 437-451.
⑨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1974], p. xx.
⑩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980], pp. xx.
11Ridell, S. Zeller, F.,“ Mediated Urbanism: Naviga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Terrai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vol. 75, no. 5-6, 2013, pp. 437-451.
責編:荊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