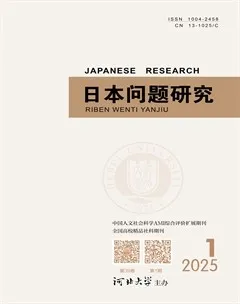地緣政治視角下日本參與北極治理的新困境

摘 要:日本作為能源消費大國,其傳統(tǒng)能源的進(jìn)口與運輸途徑因中東等政治風(fēng)險因素面臨極大不確定性。北極圈內(nèi)蘊藏的大量油氣資源及北極航道的開通,對日本具有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同時,北極環(huán)境的快速變化也將對日本的氣候、漁業(yè)、航運等多個領(lǐng)域產(chǎn)生顯著影響。由于非北極國家的身份限制以及北極理事會制度上的約束,日本長期以來在北極治理事務(wù)中不能擁有決策權(quán),遭遇著多重傳統(tǒng)困境。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后,北極地區(qū)地緣政治結(jié)構(gòu)出現(xiàn)了顯著的分裂。一方面,日本與擁有更多北極航道掌控權(quán)及豐富能源的俄羅斯合作的停滯,以及與近北極伙伴中韓等國合作步伐的放緩,使其在實現(xiàn)參與北極治理的國家根本利益方面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另一方面,日本雖進(jìn)一步加強了與美國在北極安全戰(zhàn)略方面的深度合作,并采取多元化立體參與治理模式積極與北歐諸國建立了更為緊密的合作關(guān)系,但這些舉措對于日本解決新困境效果甚微,反而將日本推向海洋軍事化的安全困境。
關(guān)鍵詞:地緣政治;北極治理;日本海洋戰(zhàn)略;外交困境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2458(2025)01-0014-17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5.01.002
引 言
地緣政治學(xué),作為專注于國際政治中地理因素的學(xué)科,其理論起源可追溯至德國地理學(xué)家、生物學(xué)家弗里德里希·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的學(xué)說。拉采爾將進(jìn)化論引入國家理論,提出了國家有機(jī)體論,主張國家具有擴(kuò)張“生存空間”的自然傾向。他還進(jìn)一步發(fā)展了環(huán)境決定論,強調(diào)國家發(fā)展與地理環(huán)境的緊密聯(lián)系。19世紀(jì)至20世紀(jì)初,地緣政治學(xué)以國家有機(jī)體論和環(huán)境決定論為基礎(chǔ),曾被德國、英國、日本、美國等國家作為擴(kuò)張國家利益的理論工具[1]。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學(xué)在英語圈內(nèi)也有著強勁發(fā)展勢頭。英國地理學(xué)家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1904年提出了“中心地帶”理論,將全球劃分為“中心地帶”“外弧線”和“內(nèi)弧線”三個區(qū)域。20世紀(jì)中葉,美國地理學(xué)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對麥金德的理論進(jìn)行了擴(kuò)展,將“外弧區(qū)”和“內(nèi)弧區(qū)”重新定義為“邊緣地帶”和“離岸”。邊緣地帶覆蓋了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到馬來半島,再到東北亞直至北極圈的廣泛區(qū)域。斯皮克曼進(jìn)一步提出了控制邊緣地帶即控制歐亞大陸,進(jìn)而影響世界之命運的學(xué)說。
二戰(zhàn)期間,由于“地緣政治”一詞與納粹德國的侵略行為緊密相關(guān),戰(zhàn)后該術(shù)語一度被回避。20世紀(jì)80年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對其廣泛使用,使得“地緣政治”重新進(jìn)入大眾視野。這一時期,美國的地緣政治學(xué)已成為追求國家利益的口號,斯皮克曼的理論也成為美國從“孤立主義”向“干預(yù)主義”轉(zhuǎn)變的政策基礎(chǔ),特別是在對蘇聯(lián)的遏制政策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進(jìn)入21世紀(jì),地緣戰(zhàn)略體現(xiàn)在美國維護(hù)其全球霸權(quán)地位上,包括其利用經(jīng)濟(jì)、外交政策控制歐亞大陸以確保美國的首要地位。
日本的地緣政治思想,一方面建立在服務(wù)于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上,二戰(zhàn)后日本被迫裁軍去武,利用日美同盟關(guān)系來維護(hù)自身的安全和擴(kuò)大影響力;另一方面建立在其島國地理環(huán)境的基礎(chǔ)之上,因為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自古以來日本就有向海外擴(kuò)展生存空間的強烈動機(jī),在這種動機(jī)的驅(qū)使下,作為重要性邊緣地帶的北極區(qū)域自然成為日本選擇的重要對象。
北極地區(qū)作為地緣政治中的邊緣地帶,近年來,因氣候變暖,北極圈冰蓋快速融化,該區(qū)域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和戰(zhàn)略資源開發(fā)引起了全球廣泛關(guān)注。如北極航道的全面開通,將成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重要紐帶,不僅會分散原有航道的貨物運輸量,降低傳統(tǒng)航線的地位和影響力,同時亦會削弱沿線國家的影響力。這一變革不僅將重構(gòu)全球海洋運輸體系,更將顯著提升北極地區(qū)在全球戰(zhàn)略格局中的地位。此外,新航線的開辟也將促進(jìn)沿線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并增強相關(guān)國家在國際地緣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力。因此,北極治理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關(guān)注的焦點。日本政府近年來也開始加快參與北極治理的戰(zhàn)略部署,持續(xù)加大對北極治理的投入。
俄烏沖突之后,日本作為近北極國家,于傳統(tǒng)地緣政治困境之外再添新困境。同時,這場沖突對東北亞其他國家也會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連鎖反應(yīng)。日本北極戰(zhàn)略的困境研究,對于近北極國家尤其東北亞國家如中國、韓國等更全面地理解北極地區(qū)的戰(zhàn)略價值,制定出更適應(yīng)全球變化和地緣政治競爭的政策和戰(zhàn)略,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日本北極戰(zhàn)略內(nèi)容與戰(zhàn)略限制
由于日本國內(nèi)經(jīng)濟(jì)高度依賴外部資源和能源供應(yīng),北極航道的利用以及對北極自然資源的開發(fā),對日本具有重大的經(jīng)濟(jì)利益(日本的集裝箱從橫濱港至荷蘭鹿特丹港,經(jīng)過非洲好望角的傳統(tǒng)航線需耗時29天。若選擇經(jīng)過新加坡馬六甲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的路線,可以縮短至22天。采用新興的北極航線,這一航程僅需15天即可完成。)。 例如,日本神戶港1995年遭阪神大地震重創(chuàng)后,一度喪失了東亞樞紐港地位。北極航道若得以正式開通,日本海也會成為一條繁忙水道,沿岸各港口也將重新迎來重大機(jī)遇,為日本恢復(fù)其物流基地功能提供新的契機(jī),有助于重塑其國際航運地位[2]。
日本參與北極治理主要集中于兩方面。第一,日本雖然不是北極圈國家,但由于大氣和海水的循環(huán),容易受到北極地區(qū)氣候變化的影響,參與北極治理關(guān)注北極氣候變化關(guān)乎其國家長遠(yuǎn)利益。第二,日本作為亞洲地區(qū)靠近北冰洋的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北冰洋航線,享受經(jīng)濟(jì)和安全利益[3]。相較于氣候影響等長遠(yuǎn)利益,現(xiàn)階段對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是經(jīng)濟(jì)和安全利益。
然而,隨著海冰融化,北極地區(qū)長期“凍結(jié)”的多邊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以及法律地位,亦開始逐漸“融化”成現(xiàn)實課題。目前,北極地區(qū)的權(quán)力決策和法律地位主要有四種決定方式。第一,北極沿岸國家(指美國、加拿大、俄羅斯、丹麥、挪威五個在北極地區(qū)擁有領(lǐng)土的國家)在涉及主權(quán)以及相關(guān)利益方面,具有他國無法干涉的決定權(quán)。第二,北極理事會(北極理事會,1996年根據(jù)渥太華宣言成立,由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冰島、挪威、瑞典、芬蘭八個北極圈國家組成。)作為北極治理的區(qū)域性國際組織,在北極事務(wù)方面具有部分決定權(quán)。第三,北極利益相關(guān)國家(該類國家是指北極航線途經(jīng)的國家和航行船舶所屬企業(yè)的所屬國,以及參與北極資源開發(fā)的國家等。)在某些具體事務(wù)中也具有一定的決定權(quán)。第四,聯(lián)合國大會對北極事務(wù)持有的部分決定權(quán)[4]。
受身份限制,日本參與北極治理完全被排除在第一種權(quán)力范圍之外。凡涉及北極主權(quán)相關(guān)事務(wù),均由沿岸五個主權(quán)國家決定。第二種通過北極理事會的途徑,對日本而言也無法參與到實質(zhì)性管理。日本的北極理事會觀察員資格所帶來的實際利益目前仍相對有限。由于北極國家在北極理事會中擁有絕對的主導(dǎo)權(quán)、參與權(quán)以及話語權(quán),并且在議題確定、議程設(shè)置、制度構(gòu)建等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中占據(jù)核心地位。日本作為觀察員國盡管能夠參與會議和提供協(xié)助,并且在北極事務(wù)中以科技合作為主要參與手段,但在科研會議中的參與機(jī)會相當(dāng)有限。實際掌握議題設(shè)置權(quán)力且在決策體系中具有重要影響的是北極國家的科學(xué)家團(tuán)隊。例如,北極理事會的關(guān)鍵制度文本大多由美、俄、加等國科學(xué)家起草。此外,由于北極理事會的決策結(jié)構(gòu)逐漸趨向于“專家化”,極地科學(xué)研究議程趨向于“政治化”,使得科學(xué)家的影響力擴(kuò)展至高官會議等決策層面。種種制度性歧視,使得觀察員國日本在北極理事會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被邊緣化,導(dǎo)致其在參與北極事務(wù)中遇到多重困境[5]。
日本對第四種途徑也不予信任。日本學(xué)者中谷和弘認(rèn)為,從以往制定的國際規(guī)則看,聯(lián)合國大會在制定規(guī)則過程中,有著強烈的反映發(fā)展中國家意愿的偏向,而且《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基于“人類共同遺產(chǎn)”[6]概念的深海資源開發(fā)也不符合市場原則(1982年《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明確指出,“區(qū)域”及其資源屬于全人類的共同繼承財產(chǎn)。第140條進(jìn)一步闡明,“區(qū)域”內(nèi)的活動應(yīng)按照本部分的規(guī)定,為全人類的利益進(jìn)行,不論各國的地理位置,無論是沿海還是內(nèi)陸國家,并特別考慮到發(fā)展中國家以及尚未完全獨立的國家,以及聯(lián)合國1514號決議和其他相關(guān)大會決議所承認(rèn)的其他自治人民的利益和需求。)。20世紀(jì)80年代,以馬來西亞為首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曾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提出將南極視為“人類共同遺產(chǎn)”的建議。該提案盡管未破壞《南極條約》,卻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日本學(xué)者認(rèn)為,未來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若出現(xiàn)諸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強烈主張,同樣的規(guī)則在北極被采納的可能性不可忽視[4]6。 不僅日本,美國作為海權(quán)大國,也仍然沒有加入《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
考慮到本國利益,日本認(rèn)為最佳選擇為第三種方式,即借由北極利害關(guān)系國的身份,同時借助與北極國家經(jīng)濟(jì)、科技、安全方面的密切聯(lián)系,間接獲得參與北極事務(wù)的部分話語權(quán)。
目前,北極地區(qū)相關(guān)利益行為體(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可劃分為四個利益圈。第一利益圈由美國、俄羅斯和加拿大等北冰洋沿岸大國構(gòu)成,在北極事務(wù)中占主導(dǎo)地位;第二利益圈由力量弱小的北歐五國組成;第三利益圈由北約、歐盟和歐洲區(qū)域性國家組織構(gòu)成;第四利益圈為中、日、韓、印等亞洲的非北極國家組成[7]。 第一、第二利益圈成員,雖實力迥異,但皆為北極國家或北極理事會成員,均是日本參與北極治理應(yīng)該密切合作的雙邊伙伴。
第一利益圈中,美俄兩國與日本在軍事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聯(lián)動關(guān)系更為突出。首先,戰(zhàn)后日本在軍事安全和外交領(lǐng)域?qū)γ绹囊蕾嚐o處不在,這種依賴在北極事務(wù)的參與中也得到了體現(xiàn)。特別是隨著新航道的開通,可能帶來的安全挑戰(zhàn)使得日本更加重視與美國的合作關(guān)系。其次,雖然日本與俄羅斯和加拿大都有在能源供應(yīng)和航道利用上的合作,由于地理鄰近性,日俄之間的合作顯得更為緊密。不僅如此,由于第一利益圈中美國、俄羅斯在北極理事會中舉足輕重的決策地位,日本更希望借助與這兩大主導(dǎo)國的合作,間接向北極理事會傳達(dá)有利于本國利益的聲音,爭取在決策領(lǐng)域中的日本話語權(quán)。相比之下,第二利益圈成員與日本的互動則更多是雙方各取所需。如果說第一利益圈對于域外國家參與北極治理持保守或抵抗態(tài)度,第二利益圈對域外國際行為體參與北極事務(wù)則持有更為開放的態(tài)度。原因在于:首先,北歐國家由于自身綜合國力的限制,單獨行動難以挑戰(zhàn)北極事務(wù)中第一利益圈國家的核心影響力;其次,北歐諸國的內(nèi)部合作更多是基于區(qū)域性的松散聯(lián)盟,限制了其在高級別政治議題上形成強有力的地緣政治合作。因此,第二利益圈的國家更傾向于借助中國、日本、韓國等域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力量,以對美國、俄羅斯、加拿大這三個北極地區(qū)的主要國家構(gòu)成戰(zhàn)略上的平衡[8]。 同樣,對日本而言,加強同北歐國家的雙邊合作也是其參與北極治理、提高話語權(quán)的多元化途徑之一。
二、日本參與北極治理的傳統(tǒng)困境及應(yīng)對
在北極相關(guān)的多邊權(quán)利義務(wù)關(guān)系及法律地位的角逐中,日本因其非北極國家的身份限制,在參與北極治理過程中始終面臨諸多困境。如日本的非北極國家身份,使其在北極理事會中只擁有觀察員資格。由于北極理事會成員國的壟斷性質(zhì)、日本參與北極治理起步較晚等,在國際政治未必對日本有利的情況下,航線的利用和資源開發(fā)以及環(huán)境保護(hù)等方面,均需要制定國際規(guī)則。在此背景下,日本不得不選擇上述參與北極治理的第三種方式,即通過與北極區(qū)域主導(dǎo)國家,尤其是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建立積極的雙邊聯(lián)系,爭取參與北極事務(wù)的話語權(quán)。長期以來,日本雖一直以科技優(yōu)勢為特色,在北極地區(qū)開展科研考察,與北極沿岸國家建立科技合作,積極開展北極治理活動。然而,在日美同盟框架下,作為重要盟友,日本必然追隨美國戰(zhàn)隊。因為,日本需要基于同美國的合作,努力爭取按照日本的國家利益參與制定國際規(guī)則的話語權(quán)。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于2014年制定了一系列北冰洋相關(guān)的國際規(guī)范。為確保日本在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國際海運、安保防衛(wèi)等方面的穩(wěn)定地位,日本認(rèn)為有必要積極參與IMO的國際規(guī)則制定。而IMO必然尊重北極理事會的意向。為此,日本最現(xiàn)實的選擇是強化日美同盟,與北極理事會的有力成員國美國密切協(xié)商,在調(diào)整兩國安保、防衛(wèi)方面利害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通過北極理事會將IMO的討論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推進(jìn)[9]。
日美同盟雖然在地緣政治競爭中為日本提供了戰(zhàn)略依托,使得日本獲得了一定的地緣政治優(yōu)勢。同時,這種依賴策略也給日本帶來了一系列挑戰(zhàn)和困境。日本在日美同盟的從屬地位,令其北極戰(zhàn)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和限制,在追求自身北極利益時須顧及美國的戰(zhàn)略意圖和反應(yīng)。換言之,“被卷入”與“被拋棄”的雙重恐懼,使得日本在北極地區(qū)一直處于戰(zhàn)略自主性缺失的困境。這種困境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日本北極戰(zhàn)略部署滯后;打破戰(zhàn)略平衡向傳統(tǒng)安全轉(zhuǎn)化。
(一)科技先行,戰(zhàn)略部署滯后
日本早期的極地科研及觀測活動,在北極和南極活動的時間跨度上相差無幾。由于北極圈地處俄羅斯、美國、挪威等多個沿岸國家的主權(quán)范圍內(nèi),尤其冷戰(zhàn)時期,日本在北極的觀測活動長期受到限制。冷戰(zhàn)結(jié)束后,日本在北極的科考活動自由度才被放開,又開始逐步活躍。日本雖在北極地區(qū)的科考活動較為先行(表1),但由于歷史原因,戰(zhàn)略部署方面較為滯后。直到21世紀(jì),隨著北極環(huán)境變化的加速以及地緣政治在該地區(qū)的迅速擴(kuò)展,北極地區(qū)的戰(zhàn)略重要性才在日本的國家戰(zhàn)略中顯著上升。
此外,日本北海道大學(xué)長期以來一直從事低溫環(huán)境下的自然科學(xué)研究。強大的科技實力成為日本參與北極事務(wù)的重要砝碼[10]。然而,從國家戰(zhàn)略方面來看,日本對北極地區(qū)戰(zhàn)略地位的關(guān)注一直比較滯后。日本外務(wù)省智庫鑒于大西洋和印度洋兩條航道的發(fā)現(xiàn)都對國際政治產(chǎn)生了重大且深遠(yuǎn)影響,曾多次提醒日本政府應(yīng)看到北極長期演變的地緣政治影響趨勢,強化北極政策的相關(guān)體制。外務(wù)省智庫還進(jìn)一步指出,日本應(yīng)借助最為擅長的科研、環(huán)保以及國際合作力,增強日本在北極治理中的存在感。
日本對北極地區(qū)戰(zhàn)略部署的滯后,也是因為受到美國北極戰(zhàn)略的影響。北極國家對北極圈的資源開發(fā)和關(guān)注度一直存在差異。美國最初并未充分重視北極的能源開發(fā),投資也相對有限。在奧巴馬總統(tǒng)任期之前,美國對北極事務(wù)一直采取較為低調(diào)的態(tài)度。然而,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2013—2017)內(nèi),美國顯著增強了對北極地區(qū)的關(guān)注,并發(fā)布了首個官方的北極戰(zhàn)略文件。因此,作為美國重要盟伴,日本在2008年3月首次制定其海洋基本計劃時,也仍未涉及北極議題。2009年7月,日本才向北極理事會遞交觀察員國申請。直到2013年日本政府才顯著加大其參與北極治理的力度,這一年也是決定日本是否能夠獲得觀察員身份的一年。2013年3月,日本學(xué)術(shù)界和智庫共同編制完成了《北極治理與日本的外交戰(zhàn)略》報告(在2013年3月由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提交的《北極治理與日本的外交戰(zhàn)略》報告中,小谷哲男指出,北極理事會將在2013年5月的第8次部長級會議上對觀察員資格申請做出最終決定。但中、韓、日三國都在游說北極理事會成員國,實際上三個國家之間正在進(jìn)行競爭,且競爭十分激烈。)。2013年4月,日本發(fā)布的第二期《海洋基本計劃》中,將有關(guān)北冰洋的措施定位為重點推進(jìn)課題。2013年5月,日本終于獲得北極理事會的觀察員國身份。2013年后半期,日本政府繼續(xù)蓄力推進(jìn)一系列北極事務(wù)相關(guān)政策與活動。同年7月,成立了北極問題聯(lián)席會。9月,外務(wù)省設(shè)立北極擔(dān)當(dāng)大使一職。同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團(tuán)召開了兩次有關(guān)可持續(xù)利用北極航線的國際研討會[11]。此后,2015年10月,日本政府正式發(fā)布《日本北極政策》,覆蓋了全球環(huán)境、科學(xué)技術(shù)、北極航線和國家安全等七個關(guān)鍵領(lǐng)域。2017年11月,日本進(jìn)一步推出了《北極重點課題與實施政策》,特別強調(diào)了將北極政策納入第三期《海洋基本計劃》框架的重要性,并明確提出了北極政策的五個重點課題(五個重點課題為加強北極海域調(diào)查研究、保護(hù)北極海洋環(huán)境、促進(jìn)北極海洋經(jīng)濟(jì)、確保北極海洋安全、推動北極國際合作。)[11]86。
2018年第三期《海洋基本計劃》中,日本正式將其北極戰(zhàn)略整合進(jìn)國家安全保障戰(zhàn)略體系[12]。 此后,日本內(nèi)閣于2023年4月批準(zhǔn)了第四期《海洋基本計劃》。這一時期,日本政府才真正意識到,接下來的5年是日本海洋政策轉(zhuǎn)型關(guān)鍵時期,應(yīng)重點推進(jìn)“綜合性海洋安全保障”和“可持續(xù)海洋建設(shè)”兩大支柱政策。不僅日本周邊海域的形勢將變得更加嚴(yán)峻,與海洋相關(guān)的國家利益也面臨著重大威脅和風(fēng)險。此外,在安全和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各種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在北極地區(qū)推進(jìn)與經(jīng)濟(jì)安全保障相關(guān)的綜合性措施的必要性日益增大。北極治理戰(zhàn)略在日本海洋安全戰(zhàn)略及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中的地位日趨上升。
(二)北極政策向傳統(tǒng)安全化的轉(zhuǎn)變
作為非北極國家,實際上日本卷入北極沖突的可能性較小。基于“知識”是北極治理議題設(shè)置和規(guī)范生成中的重要基礎(chǔ)這一理論[13],日本在北極問題上的對外政策主打?qū)嵱眯裕钥萍紴槭侄卧谀茉础⑦\輸、科考、生態(tài)保護(hù)方面與北極國家和近北極國家展開密切合作。隨著北極地緣政治影響力的增強,加之受美國北極戰(zhàn)略和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影響,近年來,日本在制定包含北極政策在內(nèi)的《海洋基本計劃》時,逐漸體現(xiàn)出由“非傳統(tǒng)安全向傳統(tǒng)安全”的戰(zhàn)略轉(zhuǎn)變。
2013年11月,美國國防部對外宣布了針對北極地區(qū)的戰(zhàn)略計劃(Arctic Strategy)。 隨后的2014年2月美海軍發(fā)表了《北極發(fā)展藍(lán)圖2014—2030》,該藍(lán)圖細(xì)致規(guī)劃了短期、中期及長期三個階段的戰(zhàn)略方向,并規(guī)定每5年進(jìn)行一次調(diào)整(短期計劃(2014—2020),維持水下和空中的軍事戰(zhàn)斗力,制定所需的戰(zhàn)略、政策、計劃并進(jìn)行人員訓(xùn)練;中期計劃(2020—2030),由于北極進(jìn)一步融冰,需增加水面艦艇的行動,同時持續(xù)進(jìn)行人員訓(xùn)練和人員確保,展開定期演示;長期計劃(2030年以后),預(yù)估東北航線和中央航線的可航行區(qū)域增大,需擁有持續(xù)作戰(zhàn)行動的能力,擁有維持前方部署的部隊。)。在美國的北極戰(zhàn)略倡議下,日本與美國在北極的協(xié)作也更傾向于安全防衛(wèi)。自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執(zhí)政以來,美國國防預(yù)算呈現(xiàn)出縮減的趨勢,這一變化對戰(zhàn)略核威懾及周邊海域防衛(wèi)等關(guān)鍵領(lǐng)域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由于這些領(lǐng)域與日本的國家安全與防衛(wèi)緊密相連,日本一直給予高度重視,并展現(xiàn)出積極尋求互補的合作姿態(tài),以共同應(yīng)對北極地區(qū)及更廣泛安全環(huán)境中的挑戰(zhàn)。
2013年12月,日本政府頒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zhàn)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NSS)中也明確指出,針對北冰洋地區(qū)安全保障與防衛(wèi)環(huán)境的潛在變化,盡管其緊迫性或許尚未達(dá)到最前沿,但作為對未來趨勢的預(yù)見性考量,這一議題應(yīng)當(dāng)被納入日本中長期防衛(wèi)體制的全面重新評估范疇之內(nèi)。從戰(zhàn)略導(dǎo)向來看,NSS強調(diào)以北極海域為宏觀視角,適時增強與海洋安全保障緊密相關(guān)的自主防衛(wèi)能力,以確保國家的安全與穩(wěn)定。
就具體合作而言,一方面,美日兩國為了強化覆蓋北冰洋的戰(zhàn)略情報收集能力,需要配備監(jiān)視衛(wèi)星和C4ISR系統(tǒng)等。未來,隨著艦船和飛機(jī)等在北冰洋及周邊海域行動范圍的擴(kuò)大,戰(zhàn)略和戰(zhàn)區(qū)反潛能力的擴(kuò)大和強化是必要的,需加強具有這種能力的艦艇和飛機(jī)及無人駕駛飛行器(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和無人水下航行器(Unmanned Underwater Vehicle,UUV)的有效利用。此外,還需要擴(kuò)大和強化彈道導(dǎo)彈防御能力,增加宙斯盾驅(qū)逐艦。另一方面,考慮到在北冰洋及周邊海域的艦船和飛機(jī)的行動,為了確保破冰和救援功能,需要整備破冰救援艦和北冰洋救援機(jī),整備北冰洋及北方海域規(guī)格的艦船和飛機(jī),收集和分析該海域的海象和氣象信息也是必要的[9]69。
根據(jù)《斯瓦爾巴德群島條約》,日本在北極地區(qū)的科研活動被限定在斯瓦爾巴德島新奧爾松的國際科研區(qū)域內(nèi)。日本在該區(qū)域的活動不僅受到挪威的嚴(yán)格監(jiān)管,且面積不足10平方千米,在地理上難以擴(kuò)展到北極其他國家的領(lǐng)土內(nèi)部。因此,日本主要依靠科考船來收集北冰洋沿岸的情報數(shù)據(jù)。目前,日本已與北極沿岸諸多國家合作,建立科研站點,并通過衛(wèi)星技術(shù)收集所需數(shù)據(jù)。
2015—2019年,日本科考團(tuán)隊依托四大重要研究基盤——國際合作據(jù)點、觀測船、地球觀測衛(wèi)星數(shù)據(jù)、北極區(qū)域數(shù)據(jù)歸檔系統(tǒng)(Arctic Data archive System,ADS),已成功實施了北極區(qū)域研究推進(jìn)項目(Arctic Challenge for Sustainability,ArCS)。該項目旨在為北冰洋主要航線提供全面支援。2020年6月,北極區(qū)域研究加速項目ArCS II開始執(zhí)行。ArCS II在掌握北極地區(qū)環(huán)境變化的實際情況并進(jìn)一步闡明過程中,加入了“國際法制度”和“國際政治”兩項人文社科研究,立足為北極的國際規(guī)則形成提供法律和政策應(yīng)對的基礎(chǔ),同時也體現(xiàn)出日本意欲在國際規(guī)則和國際海洋秩序方面擁有一定的話語權(quán)。
日本的北極戰(zhàn)略,無論是基于關(guān)注北極氣候變化維護(hù)國家長遠(yuǎn)利益,還是基于利用北冰洋航線和北極區(qū)域豐富資源,享受經(jīng)濟(jì)和安全利益,這種戰(zhàn)略布局長期以來基本在非傳統(tǒng)安全與傳統(tǒng)安全之間尋求平衡,體現(xiàn)了日本在維護(hù)國家安全與發(fā)展利益方面的綜合考量。然而,在日美同盟戰(zhàn)略框架影響下,日本北極戰(zhàn)略的天平呈現(xiàn)出向傳統(tǒng)安全傾斜的趨勢。這種轉(zhuǎn)變意味著日本在北極地區(qū)的戰(zhàn)略布局不再局限于經(jīng)濟(jì)利益的獲取,而是更多地考慮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和安全保障的需求。實際上,也是這一轉(zhuǎn)變一步步將日本帶入了加劇區(qū)域緊張和軍備競賽、限制北極國際合作、增加國家安全不確定性、損害日本經(jīng)濟(jì)利益等一系列新困境中。
三、日本北極治理戰(zhàn)略的新困境
日本北極治理的傳統(tǒng)困境及其應(yīng)對,涉及國內(nèi)政策的調(diào)整和對國際環(huán)境變化的響應(yīng)。在長期追隨美國的過程中,日本北極戰(zhàn)略的傳統(tǒng)困境一直包含著很多地緣政治的隱性挑戰(zhàn),如與中俄關(guān)系的復(fù)雜化等。國際形勢一旦發(fā)生波動,潛在隱性因素便會迅速顯現(xiàn)。
俄烏沖突后,北極地緣政治出現(xiàn)顯著分裂。日本同北極第一、第二利益圈的合作態(tài)勢也隨之迅速發(fā)生轉(zhuǎn)變。新態(tài)勢下,導(dǎo)致日本參與北極治理出現(xiàn)新的地緣政治困境。
(一)美俄對抗背景下日俄關(guān)系突變
在同第一利益圈國家的合作中,日俄一直注重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合作。同時作為鄰國,兩國在能源領(lǐng)域以及推進(jìn)北極開發(fā)治理方面,也是經(jīng)濟(jì)合作互補性與契合度較高的組合。
在環(huán)北極國家中,俄羅斯擁有廣闊的北極領(lǐng)土。據(jù)估算,全球約30%的未開發(fā)天然氣和13%的石油資源蘊藏于北冰洋,其中相當(dāng)大的比例集中在俄羅斯的淺水區(qū)域[9]64。此外,北極東北航道作為連接亞歐的最短海上航線,其大部分航段位于俄羅斯北冰洋沿海區(qū)域。俄羅斯一直寄望通過充分利用北極的自然資源和航道資源,促進(jìn)該區(qū)域的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并創(chuàng)造新的經(jīng)濟(jì)增長點以推動國家經(jīng)濟(jì)的整體發(fā)展。然而,由于北極地區(qū)自然環(huán)境極為惡劣,俄羅斯目前的技術(shù)能力難以有效開發(fā)這些資源,而日本的高科技成為俄羅斯推動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需的關(guān)鍵因素[14]。
對日本而言,北極石油天然氣等能源供給和東北航道的運用是日本國家經(jīng)濟(jì)安全方面的重要課題之一。首先,由于日本對原油和液化天然氣 (LNG)的需求幾乎完全依賴進(jìn)口,經(jīng)歷了第一次石油危機(jī)后,日本便積極探索降低對傳統(tǒng)能源依賴的途徑,并致力于儲存化石能源和核能等資源,以實現(xiàn)能源供應(yīng)的多樣化。其次,日本的能源物資運輸依賴于霍爾木茲海峽這一關(guān)鍵航道。在全球石油市場波動加劇和美國對伊朗實施經(jīng)濟(jì)制裁的背景下,伊朗曾數(shù)次表示可能關(guān)閉霍爾木茲海峽。選擇從俄羅斯進(jìn)口原油和液化天然氣,通過東北航道運輸,不僅可以避開霍爾木茲海峽等戰(zhàn)略要沖,還能縮短運輸時間,提升運輸路線的安全性。2011年3月,東日本地區(qū)發(fā)生大地震并引發(fā)福島核事故后,日本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量激增。從“能源安全保障”的觀點看,日本更加深刻認(rèn)識到能源供應(yīng)多元化的必要性,以及協(xié)同俄羅斯積極開發(fā)北極資源和航道的重要性。因此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執(zhí)政后,為確保日本在北極地區(qū)的有效介入,正式委任了北極大使,積極強化與俄羅斯在北極領(lǐng)域的戰(zhàn)略合作。
2013年5月,日本國際石油開發(fā)公司(INPEX)與俄羅斯國營石油公司聯(lián)合宣布,計劃開發(fā)馬加丹附近的鄂霍茨克海海底的油田,為日本實現(xiàn)資源多元化助力[15]。 此外,日本通過優(yōu)化“日本金屬和能源安全保障機(jī)構(gòu)”(JOGMEC)的現(xiàn)有勘探投資制度,增強了其在北極能源開發(fā)中的經(jīng)濟(jì)利益。2016年12月,JOGMEC與俄羅斯最大的獨立液化天然氣生產(chǎn)商諾瓦泰克公司簽訂了合作備忘錄,標(biāo)志著雙方將在東西伯利亞地區(qū)進(jìn)行勘探和油氣田開發(fā)合作[16]。
2014年烏克蘭危機(jī)期間,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但并未限制其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面對全球石油市場的波動,日本繼續(xù)加強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日本企業(yè)參與了俄羅斯的液化天然氣項目,包括庫頁島液化氣廠的第三期擴(kuò)建項目,以及北極液化天然氣2號項目(Arctic LNG 2)和波羅的海液化天然氣項目(Baltic LNG)。
2016年12月在日本舉行的日俄首腦會談中,雙方就8個項目分別簽署了68份有關(guān)企業(yè)等實施項目的文件。針對8個項目中的能源領(lǐng)域,雙方還設(shè)立了“日俄能源倡議協(xié)議會”。該協(xié)議會下設(shè)碳?xì)浠衔铮ㄊ汀⑻烊粴狻⒚禾浚⒐?jié)能與再生能源、原子能3個工作小組。日本還涉足俄羅斯的“薩哈林1號”和“薩哈林2號”油氣開發(fā)項目。在西伯利亞東部,日本與伊爾庫茨克石油公司在扎帕德(Zapad)油田的合作始于勘探階段,并自2016年起產(chǎn)出原油。自2017年底起,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也開始向市場供應(yīng)。該計劃涵蓋了日本公司的設(shè)備制造、測量設(shè)備和運輸船舶等多個領(lǐng)域,并已按預(yù)定計劃啟動供應(yīng)。由于亞馬爾半島大多是被永久凍土覆蓋的極寒地帶,運輸LNG的油輪必須具有破冰能力。在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中,日本商船三井公司聯(lián)合中韓兩國企業(yè),共同完成了破冰型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的建造工作,并已順利投入北極地區(qū)的航運服務(wù)中[10]94。同時,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項目與法國能源巨頭道達(dá)爾(Total)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tuán)(CNPC)等合資,在亞馬洛涅涅茨自治區(qū)薩貝塔進(jìn)行LNG生產(chǎn)的事業(yè),日揮和千代田化工建設(shè)等日資企業(yè)也參與其中。俄烏沖突爆發(fā)后,美國政府于2023年9月14日公布的對俄追加制裁中,涉及“Arctic LNG 2”項目的日本企業(yè)也被列入制裁名單。盡管美國政府的制裁不以投資者為對象,但對日俄間經(jīng)濟(jì)合作已產(chǎn)生了嚴(yán)重影響[17]。
2023年5月11日,俄羅斯正式將北極理事會主席國職責(zé)交接至挪威。北極理事會中七個西方成員國已決定暫停與俄羅斯在該組織框架內(nèi)的合作事宜。與此同時,北極理事會下轄的各項科研活動合作亦宣告中止。日本設(shè)在俄羅斯的北極數(shù)據(jù)觀測、調(diào)查活動以及雙邊交流、國際會議等活動也全部停止,日本不得不變更以俄羅斯為對象的合作計劃。 在ArCS II項目執(zhí)行期間,雙方因無法簽訂有關(guān)取得和提供數(shù)據(jù)的委托合同,俄羅斯已停止了對日本國內(nèi)的數(shù)據(jù)發(fā)送。盡管目前北極理事會在俄羅斯缺席情況下已重啟,但其運作也會受到一定影響,導(dǎo)致包括北極搜救、聯(lián)合科學(xué)考察、氣候變化、航道運行應(yīng)對等在內(nèi)的多項北極合作機(jī)制陷入部分停滯狀態(tài)。另外,由于俄羅斯的缺席,北極理事會工作組在執(zhí)行具體任務(wù)時將難以獲得俄羅斯的有效支持。此前簽訂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協(xié)議也可能遭遇難以充分執(zhí)行的問題。日俄關(guān)系突變,對日本參與北極地區(qū)的事務(wù)帶來較大負(fù)面影響。
可見,日本作為非北極地區(qū)的國家,在參與北極事務(wù)時亦面臨著平臺機(jī)制不健全以及被迫站隊等挑戰(zhàn)。此外,日本觀察員國身份的有效性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從而進(jìn)一步增加其參與北極事務(wù)的額外成本。相比美國、加拿大和北歐國家,日本在北極開發(fā)理念上實際與俄羅斯存在更高的接近度,加之俄羅斯是當(dāng)前北極國家群體中擁有最廣泛北極領(lǐng)土的國家,與俄羅斯合作的停滯,無疑增加了日本通過北極治理實現(xiàn)國家資源和航道運行領(lǐng)域利益的難度[8]21。
此外,瑞典、芬蘭成為北約成員國后,俄羅斯遭遇了更嚴(yán)峻的地緣政治挑戰(zhàn),放棄了原有的北極合作機(jī)制,開始積極構(gòu)建以自身為主導(dǎo)的“泛北極合作”網(wǎng)絡(luò)。俄羅斯已著重加強了與金磚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國以及東盟等國際組織的合作,共同應(yīng)對北極地區(qū)的挑戰(zhàn)和機(jī)遇[18]。這一舉措使得中日韓三個近北極國家在北極區(qū)域的合作面臨更為復(fù)雜的局面,合作進(jìn)程有所放緩。這對已失去俄羅斯這個重要戰(zhàn)略伙伴的日本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二)科技軍事化步伐加快,“被卷入”恐懼成為現(xiàn)實
在國家安全防衛(wèi)方面,穩(wěn)固維持日美安全保障體制一直是日本的首要考慮[19]。 俄烏沖突爆發(fā)后,俄羅斯與西方整體關(guān)系陷入斷裂狀態(tài),北極治理格局正逐漸演變?yōu)槊蓝黼p方分而治之的對峙態(tài)勢。如果說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北極戰(zhàn)略已顯現(xiàn)出向傳統(tǒng)安全轉(zhuǎn)化的傳統(tǒng)困境,在新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受地緣政治風(fēng)險積聚的影響,日本北極地區(qū)的戰(zhàn)略布局則呈現(xiàn)出科技軍事化步伐迅速加快、傳統(tǒng)安全維度轉(zhuǎn)型加速的特征。日本終未避免“被卷入”地緣政治風(fēng)險的新困境。
2022年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推出了新的《北極地區(qū)國家戰(zhàn)略》,更加強調(diào)通過國際合作來恢復(fù)美國的領(lǐng)導(dǎo)地位并維護(hù)美國的國家安全。從奧巴馬到拜登,美國在北極的戰(zhàn)略重點顯示出其安全戰(zhàn)略逐漸向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傾斜的趨勢。拜登政府將安全問題置于北極戰(zhàn)略的核心位置,與俄烏沖突后美俄關(guān)系分裂有關(guān)。美國為了維護(hù)自身的全球影響力,開始重新評估北極的安全環(huán)境和戰(zhàn)略重要性[20]。
對日本而言,一方面,俄烏沖突爆發(fā)后,日本與俄羅斯、中國的外交關(guān)系也面臨更加嚴(yán)峻的考驗。近年來,日本對中國在北極地區(qū)的活動特別是對中國戰(zhàn)略核力量及其適應(yīng)能力的潛在影響開始保持高度警覺。同時,俄羅斯不僅在北極區(qū)域增強了軍事部署,還在“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和鄂霍次克海區(qū)域加強了軍事力量,并積極推動俄羅斯海軍太平洋艦隊的現(xiàn)代化重建工作。日本對中俄兩國在包含北極地區(qū)的全球戰(zhàn)略部署始終保持高度警惕。
另一方面,鑒于北冰洋航線的擴(kuò)展,與之相連的北冰洋周邊海域航線亦將呈現(xiàn)擁擠態(tài)勢,尤其日本周邊,日本海及其宗谷、津輕、對馬島三個海峽的出入口,以及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的北太平洋海域航線,均呈現(xiàn)明顯的輻輳化趨勢。同時,不僅限于日本和俄羅斯,中國和韓國對這些海域的利用也在不斷增加。因此,這些海域面臨的海上安保和海洋安全保障問題也日益凸顯[9]67。 屆時,日本海及三個海峽防御體系的強化無疑是至關(guān)重要的,與此同時,日本也需對北海道周邊海域、北方海域以及北冰洋海域的全年行動能力進(jìn)行強化。為此,日本必將致力于提升自衛(wèi)隊在這些領(lǐng)域的情報收集能力,并優(yōu)化與加強后方支援及運用方面的策略。
日本2023版《防衛(wèi)白皮書》從安全保障角度提到,由于近年來北極海冰的減少,北極航道可航行的海域和時間不斷擴(kuò)大,北極區(qū)域未來用于軍隊海上運輸?shù)溶娛铝α繖C(jī)動部署的可能性也不斷增大。因此,日本在這一區(qū)域也出現(xiàn)了推進(jìn)軍事力量新部署等動向[21]。
日本第三期《海洋基本計劃》的主要目標(biāo)是全面評估并確保“海洋國家”的安全,提出重點建設(shè)海域感知(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MDA)系統(tǒng)(MDA系統(tǒng)不僅包括防衛(wèi)省、海上自衛(wèi)隊和海上保安廳等傳統(tǒng)海洋安全領(lǐng)域的信息,還包括洋流、海冰、水溫等海洋環(huán)境數(shù)據(jù),以及海洋氣象、科研、船舶航行、海底地形等相關(guān)信息。)。到了第四期《海洋基本計劃》,這一目標(biāo)已演變?yōu)橹贫ㄒ粋€關(guān)鍵的行動計劃,即通過MDA系統(tǒng)加強對北極海域的態(tài)勢感知。早在2015年制定北極政策時,日本政府就明確提出,應(yīng)建立MDA系統(tǒng),對可能影響北極海域安全、經(jīng)濟(jì)和環(huán)境的多樣化信息進(jìn)行集中管理,并實現(xiàn)相關(guān)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協(xié)同合作。在MDA體系中,海洋安全既包括傳統(tǒng)安全也包括非傳統(tǒng)安全,但由于該體系由政府主導(dǎo),傳統(tǒng)安全仍然是核心部分,這與北極地區(qū)以非傳統(tǒng)海洋安全為主導(dǎo)的利益結(jié)構(gòu)存在明顯差異。此外,該計劃還強調(diào)海洋科技的研發(fā)應(yīng)與防衛(wèi)省的指導(dǎo)需求緊密結(jié)合,確保研發(fā)方向與國家安全戰(zhàn)略保持一致[22]。
岸田內(nèi)閣時期,其“新安保三文件”中著重強調(diào)了推動海洋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將強化海上軍事能力建設(shè)與海洋安全保障并列作為實現(xiàn)日本國家安全的重要舉措。日本第四期《海洋基本計劃》中也強調(diào)海洋技術(shù)研發(fā)成果的軍事化轉(zhuǎn)換能力,期待以尖端海洋科技為抓手從根本上改變安全保障方式。
在美俄敵對關(guān)系背景下,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安全價值更加凸顯。2022年,美國發(fā)布的《北極地區(qū)國家戰(zhàn)略》也著重強調(diào)了與盟友及伙伴的緊密合作。該戰(zhàn)略支持美國的國土防御和全球軍事力量的投放,明確指出將與盟國和伙伴國合作以增強共同安全并抵御俄羅斯的“侵略”行為。然而,在分析美國北極安全戰(zhàn)略目標(biāo)時,可以發(fā)現(xiàn)美國依舊保持著在新安全領(lǐng)域進(jìn)行“零和博弈”的傳統(tǒng)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的核心在于控制北極的能源資源,并在北極合作治理機(jī)制中尋求主導(dǎo)地位。
俄烏沖突爆發(fā)以來,日本不斷調(diào)整對外戰(zhàn)略。一方面,積極加強日美同盟關(guān)系;另一方面,實際上日本也試圖通過這場沖突,推動自身突破安保底線,推進(jìn)戰(zhàn)略手段的“軍事化”,打破自二戰(zhàn)以來的軍事束縛。失去俄羅斯這一重要經(jīng)濟(jì)合作對象后,又追隨美國步伐在北極地區(qū)加快軍事化傾斜戰(zhàn)略,日本無疑已卷入更深層次的地緣政治困境。
(三)迫切加強同北歐諸國的合作
二戰(zhàn)后,面對日美同盟中“被卷入”和“被拋棄”的安全困境,日本從未放棄追求自主外交的步伐。自20世紀(jì)70年代后,日本便開始逐漸修正其過度依賴大國的國際關(guān)系觀念,在保持日美同盟的基礎(chǔ)上,開始進(jìn)入自主外交的探索期,積極發(fā)展多維度多元化外交。早在俄烏沖突爆發(fā)之前,日本智庫在向政府提交的報告中便多次提醒,“日本應(yīng)與北極理事會其他成員國,特別是關(guān)系薄弱的北歐國家加強雙邊緊密合作關(guān)系”[23]。
俄烏沖突爆發(fā)后,日本更加意識到參與北極治理不應(yīng)過度依賴大國。在北極地區(qū),日本修正大國依賴觀念、發(fā)展多元化外交的主要指向是北歐諸國。
然而從歷史上看,日本與北歐諸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交流一直較為薄弱。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雙方外交關(guān)系一度中斷。二戰(zhàn)后,日本與北歐各國雖逐步恢復(fù)了外交關(guān)系,且政治關(guān)系并未出現(xiàn)重大問題,但日本的外交路線開始轉(zhuǎn)向依賴美國,整個歐洲在日本外交戰(zhàn)略中的地位逐漸降低,北歐作為歐洲外圍地帶,與日本的外交聯(lián)系則顯得更加遙遠(yuǎn)。并且這一時期,日本與北歐各國都被卷入冷戰(zhàn)格局中的大國政治博弈,始終未能尋找到一條能夠緊密連接雙方的紐帶。
20世紀(jì)6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北歐福利國家以及中立國家的形象在日本國內(nèi)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和認(rèn)同,日本社會對北歐模式開始積極接納和借鑒。同時北歐國家也看到了日本在經(jīng)濟(jì)、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快速發(fā)展和變革。不過20世紀(jì)70年代后半期開始,第一次石油危機(jī)后日本經(jīng)濟(jì)陷入嚴(yán)重低迷,政府在福利方面的財政支持受到限制,政治家和媒體紛紛加強了對福利國家的負(fù)面宣傳,日本對北歐的批評尤為突出。
20世紀(jì)80年代,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美蘇對立再度升級。對于被美國要求在軍事上作出更大貢獻(xiàn)的日本政府來說,一方面想借用北歐嚴(yán)峻的軍事案例使日本增強軍備趨于正當(dāng)化;另一方面則試圖揭露在野黨勢力利用北歐批評政府的行為缺乏根據(jù),從而削弱其影響力。
冷戰(zhàn)結(jié)束后,全球性問題凸顯,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增加。日本與北歐各國在經(jīng)濟(jì)上開始逐漸重視對方的市場潛力;在政治上,務(wù)實合作氛圍也逐漸增強。北歐在脫碳技術(shù)和數(shù)字技術(shù)方面的卓越成就,也使得日本認(rèn)為雙方在這些領(lǐng)域具有深化合作的重要意義。鑒于日本在紅海的海上航線面臨諸多困境,作為替代路線,北極航道的潛在重要性日益凸顯[24]。
歷史上,日本同北歐之間的合作雖較為薄弱,但在俄烏沖突后,日本在面臨著北極傳統(tǒng)困境和地緣政治困境雙重壓力下,同北歐諸國的合作步伐進(jìn)一步加快。另外,從北歐諸國視角看,俄烏沖突后,應(yīng)對來自俄羅斯的軍事威脅,維護(hù)國家和地區(qū)安全成為其重要課題。而在北極事務(wù)上,北歐諸國向來缺乏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部署,部分國家制定的北極戰(zhàn)略亦存在內(nèi)部矛盾。整體力量分散,使得北歐諸國的話語權(quán)和影響力受到削弱。一系列因素合力,也迫使北歐諸國不得不尋求區(qū)域外國家的合作與支持。
2024年1月,時任日本外交大臣上川陽子在對芬蘭等北歐國家進(jìn)行訪問(這是自1985年安倍晉太郎訪問芬蘭以來日本外相首次踏足芬蘭。上川陽子也希望能發(fā)揮其女性外交部長的特性同北歐構(gòu)筑緊密的關(guān)系。)期間,雙方共同闡述了日本與北歐五國在四個關(guān)鍵領(lǐng)域的合作策略,包括北極及海洋事務(wù)、性別平等、綠色與數(shù)字科技、安全與防務(wù)合作,統(tǒng)稱“北歐外交倡議”。該戰(zhàn)略旨在促進(jìn)北極地區(qū)海洋秩序的共識,強調(diào)維護(hù)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秩序。在安全議題上,雙方認(rèn)為“歐洲、大西洋與印度洋、太平洋的安保不可分割”,并針對俄羅斯、中國等國家就當(dāng)前的安保形勢進(jìn)行了交流。從“北歐外交倡議”的四大議題看,在海洋安全保障方面,日本認(rèn)為不僅要繼續(xù)發(fā)揮日美同盟下美國對日安全保障作用,還需要強化與美國以外的國家建立軍事紐帶,謀求與域內(nèi)外國家之間在外交、軍事、目標(biāo)共享等方面緊密捆綁,建立以日本為核心的海洋軍事安全組織[25]。
北歐五國中的四個為北約成員國,日本與北歐諸國在安全與防務(wù)上的合作,同樣還有積極強化與北約的聯(lián)系的意圖,希望通過與北歐國家的合作提升自主防務(wù)外交效果。從北歐國家的角度看,近年來北歐諸國一方面向美國尋求防務(wù)資源,另一方面也緩慢嘗試自我防務(wù)建設(shè)。特朗普第一次執(zhí)政時期,美國奉行孤立主義,與其他北極國家之間齟齬不斷,導(dǎo)致北極國家出現(xiàn)了離心傾向,對美國的安全保障已失去信任。尤其特朗普提出收購格陵蘭島、對歐盟單方面加征鋼鋁產(chǎn)品關(guān)稅等貿(mào)易保護(hù)政策,引起丹麥、芬蘭、挪威等國不滿,導(dǎo)致北歐國家對美國的信任銳減。2018年,為加強五國間的防務(wù)合作,北歐國家簽署了 《北歐防務(wù)合作愿景2025》。特朗普二次執(zhí)政后,北歐諸國和日本雙方在安全防務(wù)合作方面均各有所需。
2022年12月,日本陸上自衛(wèi)隊正式接收了芬蘭帕托利亞公司制造的新一代裝甲車。同月,日本政府與瑞典王國政府簽署了《關(guān)于轉(zhuǎn)讓防衛(wèi)裝備和技術(shù)的協(xié)定》。2023年10月,在日本與丹麥?zhǔn)啄X的會談中,雙方就日本駐第三國防衛(wèi)官員兼任丹麥?zhǔn)聞?wù),以及丹麥向日本派駐武官問題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并達(dá)成共識。同年12月,日本與挪威首腦會談中,發(fā)表了日挪戰(zhàn)略伙伴關(guān)系聯(lián)合聲明,兩國重申了加強經(jīng)濟(jì)安全保障領(lǐng)域合作的決心。同時,日本決定為自衛(wèi)隊引進(jìn)挪威生產(chǎn)的遠(yuǎn)程巡航導(dǎo)彈(JSM)。
日本與北歐諸國同為科技先進(jìn)國家,日本還希望通過與北歐國家的合作提升自身在綠色與可再生能源及數(shù)字領(lǐng)域的全球影響力。1991年,日本在挪威的協(xié)助下,在斯匹茨卑爾根群島設(shè)立了用于監(jiān)測輻射和大氣情況科學(xué)考察站。2019年9月,在原有科學(xué)考察站基礎(chǔ)上由挪威政府出資又建設(shè)了新基地。此外,在挪威航天局的大力支持與協(xié)助下,日本宇宙科學(xué)研究所(JAXA)成功研制了SS5203號探空火箭,并于2021年11月從位于尼奧爾松島的火箭試驗場順利發(fā)射升空。該火箭的主要任務(wù)在于深入研究發(fā)生在卡斯普上空的電離大氣流出過程,以期揭示其背后的科學(xué)機(jī)制與規(guī)律,為北極地區(qū)的科學(xué)研究提供更為精準(zhǔn)與深入的數(shù)據(jù)支持。
近年來,日本與北歐諸國不斷加強包括綠色、數(shù)字和科技在內(nèi)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2022 年 12 月,日本海運公司積極參與挪威的碳捕獲與封存(Carbon Cature and Storage, CCS)項目,成功簽訂了液化 CO2 運輸船的運航合同,展現(xiàn)了其在應(yīng)對全球氣候變化方面的積極態(tài)度。此外,2023年,時任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大臣西村康稔和時任環(huán)境大臣西村明宏分別于 4 月和 8 月訪問了冰島。西村康稔在訪問期間發(fā)表了《關(guān)于地?zé)岷献鞯穆?lián)合聲明》,旨在深化兩國在地?zé)崮茉搭I(lǐng)域的合作。2023 年 7 月,得益于日本企業(yè)的投資,丹麥開啟了世界上首個以可再生能源電力生成的綠色氫為原材料的 e-甲醇制造與銷售項目。同年 9 月,日資制鐵企業(yè)在瑞典建設(shè)的無碳?xì)淠芄S順利完成,并投入運營。2023 年 10 月,日本與丹麥正式簽署了《氫、氨及其衍生物合作備忘錄》及《海上風(fēng)電合作基本協(xié)議書》,標(biāo)志著兩國在新能源領(lǐng)域合作邁入新的階段[26]。
由于北歐五國在北極問題上享有天然話語權(quán),日本十分重視北極蘊藏的能源資源以及北極航道潛力,旨在通過“北歐外交倡議”借助北歐力量提升在該地區(qū)的影響力、科技競爭力和安全防務(wù)能力。北歐國家通過與日本的合作雖然也能獲得一定的利益,但日本在雙方的合作中對北歐力量的借助更為積極和迫切。
日本與北歐合作的積極性與迫切性,還體現(xiàn)在“北歐外交倡議”中有關(guān)性別議題的加入。倡議第二項提及“攜手推進(jìn)性別平等,包括‘婦女、和平與安全’(Women 、Peace and Security,WPS)議題”。相較于其他三個議題,性別問題在日本參與北極事務(wù)中并不直接涉及經(jīng)濟(jì)或安全利益,更像是日本用來加強與以性別平等和尊重女性而聞名的北歐國家之間外交聯(lián)系的一種策略。2024年初,時任日本外交大臣上川陽子訪問北歐時也特別指出,希望發(fā)揮其女性外交部長的特性,同北歐構(gòu)筑緊密的關(guān)系,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日本在“北歐外交倡議”中提出要致力于將WPS提升至更為重要的外交政策地位,在國際合作的實踐過程中深入貫徹WPS的思維方式,并為此制定了獨具特色的“WPS in Action”方案,在方案具體實施過程中汲取北歐各國的先進(jìn)經(jīng)驗,以期取得更加顯著的成效。針對日本的WPS方案,北歐國家和日本也有過交流與互動。2023年11月,由國際組織“女性政治領(lǐng)袖”(Women Political Leader,WPL)、冰島政府及其議會聯(lián)合主辦的《雷克雅未克全球論壇2023》在冰島舉行時,自2016年起擔(dān)任WPL大使的上川陽子出席了該論壇。2022年日本舉辦第六屆世界女性大會(World Assembly for Women,WAW),冰島共和國總統(tǒng)約翰內(nèi)松發(fā)表了主旨演講,芬蘭總理馬林亦通過視頻強調(diào)推動女性權(quán)益保障事業(yè)的重要性。
事實上,日本作為傳統(tǒng)“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國家,在性別議題方面同北歐國家的“性別平等”概念存在諸多分歧。WPS議題,源于聯(lián)合國第1325號決議,旨在全球范圍內(nèi)維護(hù)婦女、和平與安全權(quán)益。2000年聯(lián)合國發(fā)布此決議,同時呼吁各成員國據(jù)此制定本國的WPS行動計劃。日本基于國內(nèi)傳統(tǒng)社會文化的影響,一直未制定本國WPS行動計劃。直至2013年,日本開始準(zhǔn)備競選2015年聯(lián)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時意識到,此狀況將對其產(chǎn)生極為不利的影響[27]。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借鑒澳大利亞的成功案例(澳大利亞2012年制定了本國WPS行動計劃,獲得加分后順利當(dāng)選聯(lián)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通過制定本國的WPS行動計劃,為2015年當(dāng)選聯(lián)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加分。
日本首次公開宣布著手制定本國WPS行動計劃的政策,是在2013年3月聯(lián)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上。同年9月17日,第68屆聯(lián)合國一般辯論大會上,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再次強調(diào)了這一政策的外交導(dǎo)向,明確指出WPS行動計劃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作為實現(xiàn)該外交政策的一環(huán),WAW會議從2014年開始召開,邀請世界各地活躍在各個領(lǐng)域的領(lǐng)導(dǎo)人,針對日本和世界面臨的各種課題進(jìn)行討論,并將其成果登記在聯(lián)合國文件上。日本與北歐諸國的互動與交流也多是在WAW相關(guān)會議上。
日本在聯(lián)合國1325號決議頒布后13年之久,才開始響應(yīng)議程,制定本國的WPS行動計劃,主要根源在于日本雖為發(fā)達(dá)國家,社會結(jié)構(gòu)中卻依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傳統(tǒng)文化觀念。這導(dǎo)致日本社會的性別不平等仍然突出,也導(dǎo)致日本在性別議題上的外交政策與國內(nèi)政策間存在顯著差異。日本將《婦女、和平與安全保障的行動計劃》定位為外向型政策,聚焦海外女性支援,避開了國內(nèi)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探討。在國內(nèi),安倍晉三提出的“女性經(jīng)濟(jì)學(xué)”和“綻放女性光輝社會”政策,主要目標(biāo)是為了在少子老齡化社會背景下,挖掘女性作為后續(xù)勞動力之潛力。每年度由世界經(jīng)濟(jì)論壇公布的《全球性別差異報告》顯示,日本多年來一直處于全球排名的后位。2024年,日本總排名為第118名(四類分項目中,教育項目排第72名,政治參與排第113名,經(jīng)濟(jì)參與排第120名,健康與醫(yī)療排第58名。),位于G7集團(tuán)最末位,而北歐五國總排名為冰島第7名、挪威第9名、芬蘭第10名、瑞典第12名、丹麥稍有后退位于第37名[28]。如上文所述,日本制定WPS行動計劃的直接動機(jī),主要在于助力2015年聯(lián)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席位競選。若進(jìn)一步發(fā)掘其深層和長遠(yuǎn)目標(biāo),可發(fā)現(xiàn)日本希望借助這一行動計劃,拓展本國在國際社會的軍事影響力。 同時,通過這一外交政策的實施,日本也期望能夠加強與聯(lián)合國及其他國家(諸如北歐國家)之間的外交聯(lián)系和彼此間的戰(zhàn)略合作。
盡管日本通過多元化方式,積極建立與北歐各國之間的合作,以加強在北極地區(qū)參與治理的存在感。然而,北極開發(fā)對北歐各國而言是一項兼具綜合性及長期性的任務(wù)。從合作理念與核心目的來看,北歐諸國更傾向于確保北極圈內(nèi)生態(tài)環(huán)境和科技民生等領(lǐng)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日本參與北極事務(wù)的動因雖然不排除應(yīng)對北極氣候變暖所帶來的挑戰(zhàn),但是對日本而言,北極地區(qū)最為現(xiàn)實且直接的利益體現(xiàn)在能源利益與航運利益上[3]72。日本為解決參與北極事務(wù)的新舊困境,積極加強與北歐諸國的外交聯(lián)系,然而因與北歐諸國在傳統(tǒng)文化和合作理念方面存在分歧,雙方合作關(guān)系的深度與長久性尚為不確定的課題。
結(jié) 語
日本地緣政治與其戰(zhàn)略文化息息相關(guān)。盡管地緣疏離,自古至今日本一直覬覦朝鮮半島和亞洲大陸。二戰(zhàn)后,日本結(jié)束了大陸擴(kuò)張戰(zhàn)略之愚行,在日美同盟框架影響下,安倍第二次執(zhí)政后,海洋戰(zhàn)略逐漸卷土重來。日本政府認(rèn)為,日本作為海洋國家應(yīng)該通過海洋資源開發(fā)和海上貿(mào)易更多謀取經(jīng)濟(jì)增長,同時還要為建立開放、穩(wěn)定的國際海洋秩序而努力。
全球氣候變暖后,北極海冰大面積融化,北極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海運航道價值凸顯,使得這一地區(qū)在全球政治經(jīng)濟(jì)中的地位逐漸上升,日本作為海洋國家也積極參與到北極事務(wù)之中。作為非北極國家的日本,因身份及北極理事會制度等重重限制,不得不采取靈活的雙邊合作策略。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日本在北極政策上的戰(zhàn)略變化也反映了其在國際政治經(jīng)濟(jì)形勢中的戰(zhàn)略調(diào)整和利益訴求,以及對北極地區(qū)安全態(tài)勢的重新認(rèn)識。這種調(diào)整同時給日本也帶來了新的風(fēng)險和困境。
二戰(zhàn)后,日本緊隨美國外交策略,雖能夠帶來一定的戰(zhàn)略利益和資源共享,但日本也不得不面對美國北極政策向國家戰(zhàn)略安全化轉(zhuǎn)變的趨勢,在北極政策上加強了對傳統(tǒng)安全的關(guān)注,包括加強防務(wù)機(jī)制建設(shè)、提升海上自衛(wèi)隊力量等,限制了日本在北極事務(wù)中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俄烏沖突后,日本與俄羅斯陷入分裂狀態(tài)。雙方在科學(xué)考察尤其是經(jīng)濟(jì)聯(lián)系上的中斷,對日本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俄羅斯在北極地區(qū)擁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和重要的航道利益,一旦與俄羅斯的合作中斷,日本在北極的能源供應(yīng)和航道安全都將面臨嚴(yán)峻的挑戰(zhàn)。 作為補救措施,日本與北歐國家雖然在數(shù)字科技、海洋保護(hù)與開發(fā)、環(huán)境能源綠化等領(lǐng)域展開了廣泛合作,但對于日本來說,這些領(lǐng)域的合作效果甚微。北歐國家更關(guān)注性別平等、環(huán)境和氣候保護(hù)等議題,與日本的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濟(jì)戰(zhàn)略利益存在一定的差異和分歧。此外,北極地區(qū)軍事變數(shù)被不合理夸大,使得日本與其他北極域外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qū)“近北極國家”之間的戰(zhàn)略利益呈現(xiàn)分化趨勢,合作空間受到壓縮。
日本獲得北極理事會觀察員身份后,也曾積極致力于推動對北極治理架構(gòu)的革新。盡管當(dāng)時中日關(guān)系正處于緊張狀態(tài),但日本在北極事務(wù)上對中國持相對理性的立場,并展現(xiàn)出與中國及韓國在北極參與合作方面的積極愿望。這一態(tài)度的形成基于一個共識,即中日韓三國在北極參與問題上攜手合作所能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遠(yuǎn)勝于各自為政的孤立行動。由于三個國家在近北極國家身份以及經(jīng)濟(jì)利益上有諸多相似之處,這些因素原本應(yīng)成為日本積極推進(jìn)與中韓北極合作關(guān)系的動力。然近年來日本持有戒備與敵意的理念,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三個國家之間的合作態(tài)度,偏離了原有的合作方向。這種方向性的偏離,對三方在北極區(qū)域的合作進(jìn)程,以及多邊合作過程中各國的經(jīng)濟(jì)利益與安全利益均產(chǎn)生嚴(yán)重負(fù)面影響。
因此,日本在北極事務(wù)中的合作策略需要更加靈活和多元化,注重自身的利益和訴求無可厚非,但要與各方保持良好的關(guān)系,尤其是為緩解上述影響并推動北極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發(fā)展,日本更需要加強與北極域外相關(guān)國家的溝通與合作,共同應(yīng)對北極地區(qū)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和問題。
[參考文獻(xiàn)]
[1]DODDS K.地政學(xué)とは何か[M].野田牧人,譯.東京:原書房,2012:68.
[2]陳鴻斌.日本的北極參與戰(zhàn)略[J].日本問題研究,2014,28(3):1-7.
[3]肖洋.日本的北極外交戰(zhàn)略:參與困境與破解路徑[J].國際論壇, 2015, 17(4): 72-78.
[4]中谷和弘.第1章 北極問題(概観)[DB/OL]//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北極のガバナンスと日本の外交戦略」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2013-03)[2024-06-12]. https://www2.jiia.or.jp/pdf/resarch/H24_Arctic/01-nakatani.pdf.
[5]肖洋.北極科學(xué)合作:制度歧視與壟斷生成[J].國際論壇, 2019(1): 103-113.
[6]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EB/OL]. (1982-12-10)[2024-07-08].https://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texts/unclos/unclos_c.pdf.
[7]葉艷華.東亞國家參與北極事務(wù)的路徑與國際合作研究[J].東北亞論壇,2018(6):92-104.
[8]岳鵬.北歐國家北極戰(zhàn)略評析[J].區(qū)域與全球發(fā)展,2022(2):5-22.
[9]金田秀昭.第 6 章 北極海と日米同盟(その 2)——注目を要する安全保障·防衛(wèi)面での懸念への対応[DB/OL]//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グローバル·コモンズ(サイバー 空間、宇宙、北極海)における日米同盟の新しい課題.(2015-03)[2024-04-27]. https://www2.jiia.or.jp/pdf/resarch/H26_Global_Commons/07-kaneda.pdf.
[10]宋寧而.日本的安保理念、雙重身份與北極參與的戰(zhàn)略選擇[J].太平洋學(xué)報,2023,31(12):83-95.
[11]李振福,何弘毅.日本海洋國家戰(zhàn)略與北極地緣政治格局演變研究[J].日本問題研究,2016,30(3):1-11.
[12]內(nèi)閣府.第3期海洋基本計畫[EB/OL].(2018-05-15)[2024-02-23]. https://www8.cao.go.jp/ocean/policies/plan/plan03/pdf/plan03.pdfl.
[13]瞿瓊.國際實踐與規(guī)范生成:北極治理的過程建構(gòu)[D].武漢:武漢大學(xué),2020:145.
[14]喬蕊.21世紀(jì)初俄日關(guān)系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xué),2015:16.
[15]Japan and Russia jointly develop the Okhotsk Oil field[EB/OL](2013-05-29)[2024-04-27].http://news.cableabc. com/world/20130529000373.html.
[16]崔健,黎純陽.日本北極戰(zhàn)略的經(jīng)濟(jì)安全考量[J].東北師大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 2019(4): 33-40.
[17]竹本能文,GOLUBKOVA E. 米が対ロ追加制裁、北極圏LNG開発の関連企業(yè)も対象 日本勢が參畫[EB/OL].(2023-09-16)[2024-05-23]. https://jp.reuters.com/world/ukraine/6AA6RMYF35PQLNJJ2WBV5V2T4E.
[18]趙寧寧,張楊晗.俄烏沖突背景下俄羅斯北極政策的調(diào)整、動因及影響[J].邊界與海洋研究,2023,8(5):58-71.
[19]金田秀昭.第4章 北極海とわが國の防衛(wèi)[DB/OL]//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北極のガバナンスと日本の外交戦略」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2013-03)[2024-06-12]. https://www2.jiia.or.jp/pdf/resarch/H24_Arctic/09-arctic_governance.pdf.
[20]潘敏,廖俊傑.美國北極戰(zhàn)略的變化:動因、影響與中國的應(yīng)對[J]. 遼東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23(4):34-44.
[21]防衛(wèi)省.令和5年版『防衛(wèi)白書』[EB/OL].(2023-07-28)[2024-02-23].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3/pdf/index.html.
[22]北極の未來に関する研究會. 我が國が重點的に取り組むべき北極に関する課題と施策[EB/OL].(2018-06-05)[2024-05-13]. https://www.spf.orggt;global-datagt;oprigt;pdf_files.
[23]小谷哲男.第7章 北極問題と東アジアの國際関係[DB/OL]// 公益財団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北極のガバナンスと日本の外交戦略」研究プロジェクト. (2013-03)[2024-06-16].https://www2.jiia.or.jp/pdf/resarch/H24_Arctic/09-arctic_governance.pdf.
[24]日本経済新聞.北極·ジェンダー、対北歐で外交方針 上川外相が表明[EB/OL]. (2024-01-09)[2024-05-14].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92080Z00C24A1000000/.
[25]房迪.試析岸田文雄內(nèi)閣的綜合海洋安全保障戰(zhàn)略[J].日本學(xué)刊, 2024(2): 81-100.
[26]北歐外交イニシアティブ[EB/OL]. (2024-01)[2024-11-18].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604508.pdf.
[27]陳起飛.日本《關(guān)于婦女、和平與安全保障的行動計劃》外向型立場分析[J].山東女子學(xué)院學(xué)報,2021(3):84-96.
[28]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4[EB/OL]. (2024-06-11)[2024-09-23]. https://www.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24.pdf.
[責(zé)任編輯 孫 麗]
Japan’s New Dilemmas in Arctic Governance from a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CHEN Qif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Hebei Agrculture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major energy-consuming nation, Japan’s traditional energy imports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s are subject to significant uncertainty due to political risks in regions such as the Middle East. The abundant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the Arctic,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its shipping lanes, hold vital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Japan. Concurrently, the rapi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Arctic are poised to significantly affect various sectors in Japan, including climate, fisheries, and maritime transport. Due to its non-Arctic state statu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he Arctic Council’s system, Japan has long been unable to have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Arctic governance affairs and has long encountered multiple difficulties.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Arctic has undergone severe fragmentation. The halt in Japan’s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which wields significant control over Arctic shipping routes and possesses abundant energy resources, coupled with the deceleration of its collaborative pace with near-Arctic partners like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s plunged Japan into a fresh set of challenges in realizing its fundamental national interests in Arctic governance. On another note, Japan has intensified its deep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Arctic security strategies and has adopted a diversified and multifaceted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reby forging closer cooperative ties with Nordic countries. Nevertheless, these initiatives remain insufficient in resolving Japan’s new predicaments, and instead push Japan towards the security dilemma of maritime militarization.
Key words: geopolitics; Arctic governance; Japan marine strategy; diplomatic dilemma
收稿日期:2024-11-07
基金項目:河北省教育廳高等學(xué)校科學(xué)研究項目(QN2025471)
作者簡介:陳起飛,女,博士,河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講師,主要從事國際關(guān)系與區(qū)域國別研究、日本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