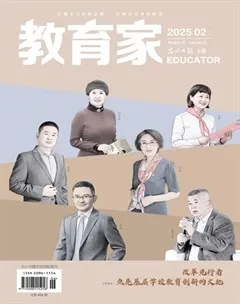曹永健:螢火微光里,閱讀照見無限成長

“我曾經(jīng)一度自卑,我的起點很低,但當(dāng)我意識到自己是一只螢火蟲的天命時,決定坦然接受自己的‘微小’,心中卻執(zhí)著于‘不渺小’。”一次年終總結(jié)中,湖南小學(xué)語文教師曹永健這樣寫道。
螢火蟲,體型較小,一般體長在幾毫米到十幾毫米之間。它們往往在黑暗中閃爍微光,美麗而神秘,常被視作浪漫的象征。2015年2月6日,曹永健申請了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將其命名為“螢火蟲閱讀館”。在此之前,他已經(jīng)開展了數(shù)年的兒童閱讀教學(xué)。自此之后,他以“螢火蟲”的意象命名自己以閱讀為主題延伸開來的種種實踐。
“小”老師的“大”理想
小學(xué)語文的教學(xué)重點是什么?在曹永健看來,識字、書寫等基礎(chǔ)知識與技能的教學(xué)固然必要,但閱讀能力的培養(yǎng)或許意義更為深遠(yuǎn)。他期望孩子們在童年時期就能養(yǎng)成閱讀的習(xí)慣,從中受到精神的滋養(yǎng),建立對自我、對他人、對社會的認(rèn)識。
用故事喂養(yǎng)孩子是曹永健在帶一年級時的自覺追求,他說:“在實踐中我發(fā)現(xiàn),沒有哪個孩子不愛聽故事,因為喜愛故事,他們會喜歡上一位老師、喜歡上一間教室。”在《小黑魚》中,孩子們“暢游海底”,領(lǐng)略了小黑魚的智慧和勇氣;在《逃家小兔》中,他們感受到愛與溫暖;讀《生命不息》時,他們接觸到沉重而神秘的死亡話題……一個繪本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孩子呢?如果再讀一本,讀了一本又一本呢?或許在某個時刻,人們會猛然發(fā)現(xiàn),孩子們的思維已經(jīng)悄然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積極變化。作為一位小學(xué)語文教師,曹永健努力不被“小”的限定詞所框定,而是幫助孩子們借由閱讀建立與廣大世界的深度聯(lián)結(jié),增強他們探索生活和答案的欲望。
曹永健的篤定源自個人的受益。“在工作之前我不太讀書,也沒什么藏書。整個高中讀的書,數(shù)得上來的可能也就那么幾本青春文學(xué)。”實際上,他在讀書時算不上一個“好學(xué)生”。因為嚴(yán)重偏科,在中學(xué)時期很難取得學(xué)業(yè)上的成就感,他也曾有過叛逆、逃學(xué)的經(jīng)歷。最終,這個老師眼中“不成器”的學(xué)生只考進(jìn)了一所師范類大專院校。2007年畢業(yè)后,曹永健回到郴州,進(jìn)入一所民辦學(xué)校任教。為了做好教育這件良心事,他特意找來一些名家的課堂實錄學(xué)習(xí),卻發(fā)現(xiàn)“有時他們說的理論、觀點你可能聽都聽不懂”。在巨大的不安中,曹永健開始尋求各種方式來為自己“補課”,也是自這時起,閱讀才真正走進(jìn)了他的生命。
“一個人的精神發(fā)育史,就是他的閱讀史。”這句話深深烙進(jìn)了曹永健的腦海。通過閱讀,他邂逅了朱永新發(fā)起的“教育在線”論壇,看到了其中優(yōu)秀教育實踐者的探索與分享,學(xué)著榜樣教師的樣子開展教學(xué),給孩子們讀故事、放電影,建設(shè)書香班級。同時,他不間斷地記錄自己每年對數(shù)十本書的閱讀與思考。幾年間,曹永健由私立學(xué)校考入公立學(xué)校,從郴州考到長沙。他認(rèn)為:“是閱讀這束光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借閱讀一次次走向遼闊的遠(yuǎn)方。”
2016年,曹永健去學(xué)校對口支援的國家級貧困縣支教,帶二年級。第一次去時,他就帶了一箱繪本。他清楚地記得,班上的64位學(xué)生中,50%以上是留守兒童,所有人都沒讀過哪怕一本課外書。孩子們對這位城里來的老師很感興趣,也喜歡聽他講故事,灰蒙蒙的教室里,他們專注地聽著,眼里閃爍著不同往日的光彩。
“為他們募集更多的書,創(chuàng)立一所閱讀教室。”不久后,曹永健心頭涌動著這樣的想法。他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發(fā)出倡議,邀請大家為這里的孩子搭建一個以書籍為核心的教室。不久后,愛心捐贈如螢光般匯聚在一起,照亮了斑駁教室里的一方小小天空,“鄉(xiāng)村螢火蟲閱讀教室”由此建立。這一年里,曹永健為孩子們購置了上百冊書籍,上學(xué)期,他帶孩子們讀獲獎作品、讀同類主題的繪本;下學(xué)期,他帶著孩子們讀故事類的整本書,在導(dǎo)讀課、推進(jìn)課、主題探討課中,將孩子們的思考引向深處。讀得多了,孩子們的表達(dá)欲也悄悄地“溢”了出來,自己創(chuàng)作起繪本故事。有人寫《公雞叫太陽》,有人寫《遲到的原因》,等等。人們讀來甚至能看到這些文字背后一張張可愛的面龐。后來,在教室書架的一側(cè),曹永健總會備上創(chuàng)作紙,孩子們常常在課間寫寫畫畫,逐漸養(yǎng)成了讀寫的習(xí)慣。
支教那年的家訪過程中,曹永健看到一位奶奶帶著孫女住在每月200塊租金的房子里,卻因為孩子愛上了閱讀,從鎮(zhèn)上買來400塊的鐵皮柜給她放書。曹永健還記得,另一個孩子坐在門前曬稻谷的草坪上,捧著書等待長輩回家,灑落在她身上的光分外溫柔。一年的支教期結(jié)束時,很多孩子擁有了自己的專屬“小書房”。閱讀,給他們打開了一扇扇窗。
以課程的方式促進(jìn)共同生長
回到長沙后,曹永健從一年級開始執(zhí)教。就像農(nóng)人擁有了一片自己的土地,他懷著期待播撒下一顆顆閱讀的種子,想通過六年完整的實踐,看看自己所理解的讀寫教育能給孩子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除了日常國家課程內(nèi)的閱讀教學(xué),曹永健還在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的支持下設(shè)計了階梯式的校本閱讀課。低年級以閱讀經(jīng)典圖畫書為主,在每日朗讀的繪本故事里,孩子們迅速消除了對學(xué)校、同學(xué)和老師的陌生感;中年級以共讀橋梁書、初階整本書為主,因為閱讀《夏洛的網(wǎng)》這類內(nèi)涵豐富的故事,孩子們的認(rèn)知水平也隨之提升;高年級以閱讀經(jīng)典兒童文學(xué)作品為主,《西游記》《小王子》等著作成為孩子們的“口袋讀物”。常態(tài)化的每日30分鐘閱讀之外,曹永健會在每周一次的精讀課上,選擇書中適合的主題與孩子們探討,豐富他們的認(rèn)知和思維。
“千萬別低估了孩子們。”曹永健說,在講述《這是我的!》繪本故事時,孩子們從討論身邊的文具盒、水杯等物品,想到操場、圖書館、博物館等場所,不自覺中產(chǎn)生了對私有、共有、共享的認(rèn)識。在讀完《不老泉》時,面對“如果你有一杯不老泉,會如何做”的問題,有的孩子回答,人如果不死就會像石頭一樣活著,她不愿意這樣活著,所以不會喝下不老泉泉水。有的孩子想到之前討論的情節(jié),認(rèn)為如果不死會打破固有秩序,那萬物不老,世界也會停滯。
與“讀”同時發(fā)生的是“寫”,在開放性的話題之下,孩子們自由地仿寫、創(chuàng)編,并擁有了自己的作品集。比如共讀《西游記》后,曹永健設(shè)計了由三個篇章組成的《大話西游》作品集:在“兵器譜”里,孩子們寫的是自己認(rèn)為最厲害的三樣兵器;在“人物榜”里,寫的是自己穿越到《西游記》里最想成為的人;在“競選臺”里,寫的是取經(jīng)團隊成員適合競選班級里的什么職位。孩子們的作品里,盛滿了各種奇思妙想。曹永健會設(shè)立各種“獎項”,想盡辦法地肯定他們,使每個孩子都能獲得獎勵,擁有持續(xù)表達(dá)、書寫的欲望。有時,曹永健還會將他們的文章發(fā)送至自己的公眾號,一個孩子最多領(lǐng)過1400元的贊賞作為“稿費”。
從教三年級開始,曹永健每學(xué)期會舉辦一次小古文大賽,先是讓孩子們誦讀、表演,而后仿寫、創(chuàng)編文言文作品。學(xué)生小付在三年級時曾創(chuàng)作了一篇文言文《老曹好學(xué)》。
曹幼時,敏而好學(xué),彼時家境貧寒,無書可讀。曹便借于藏書之家沉醉于書中也。
父母給之錢,曹不舍花之。終一日,錢攢夠,遂奔向新華書店,選于兩本心愛之書而閱。曹速讀完,便將之帶入校,借于同學(xué),后書遺失,曹心痛而惜之也。
曹幼時,勤奮練字,無需父母督促,每日習(xí)之。如今曹之字已如帖書,甚是美觀也。
此時,老曹已成名師,人問曰:“汝現(xiàn)已學(xué)業(yè)有成,為何仍不斷學(xué)習(xí)之?”老曹曰:“學(xué)無止境,吾為何不學(xué)也?”
在曹永健的班上,能寫出這種作品的孩子不在少數(shù)。
教學(xué)從來都不是單向度的工作。在曹永健看來,若是將帶著孩子們共讀共寫比作種花,花開時,自己也會因此沾染一身芬芳。“比如我給他們講故事、讀童謠,一部分滿足了孩子當(dāng)下的成長需要,一部分也回應(yīng)了我的內(nèi)在生命需要。一個人小時候的缺失很難彌補。想起來,我的童年是乏善可陳的,這些故事和童謠,其實對我或多或少有著‘治愈’之效。”同時,在高年級共讀共寫《小王子》《西游記》等經(jīng)典著作時,梳理既有研究、融入個人見解、引發(fā)教育生成,這些過程都令他感到無比幸福。“《小王子》告訴我們,本質(zhì)的東西是看不見的。孩子們那些難以被衡量的成長亦是如此。”
為了幫助孩子們形成自主閱讀的良好習(xí)慣,低年級時,曹永健在班級里創(chuàng)建“閱讀存折”,孩子們可以在存折里記下自己每日的閱讀量。三年級時,他曾發(fā)起一個月讀十本故事書的“1001頁”活動,結(jié)果讀得最少的孩子都有2000頁。這時他才發(fā)現(xiàn),孩子們的閱讀速度遠(yuǎn)超他的預(yù)料。六年級的“一周一書”計劃中,圖書柜上粘貼的表格讓大家的閱讀可視化,在榜樣的引領(lǐng)下,孩子們的共讀共學(xué)氛圍越發(fā)濃烈。曹永健“讓好書觸手可及,讓閱讀隨時發(fā)生”的期待也一步步趨近現(xiàn)實。每學(xué)期為班級選書時,他只要把清單發(fā)給家長,負(fù)責(zé)財務(wù)管理的家長就會購入,并定期向班級通報賬目。這屆學(xué)生所在的教室里,一共有三個環(huán)繞教室三面墻壁的圖書架,臨近畢業(yè)時,班級里的流動藏書已逾2000冊。
成人成己,微光熒熒
2015年年末,曹永健回老家過年。出于職業(yè)本能,加之對兒童閱讀教學(xué)的興趣,他問起身邊五年級的孩子讀過哪些書。孩子沉默了一會兒,然后搖頭。又問了幾位其他年級的孩子,結(jié)果依然類似。與自己上學(xué)時并無多少不同的現(xiàn)狀令曹永健深受觸動。“我們那時普遍不讀書,或者說接觸不到好書。家長們也不是不知道應(yīng)該讀書,但沒有能力支持孩子。條件當(dāng)然有限,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也缺少這種意識和指導(dǎo)的能力。”曹永健說,“鄉(xiāng)村的家長,或是忙著種田,或是在外打工,讓孩子吃飽穿暖,如果讀得上去就一直供,這是他們認(rèn)為自己為人父母能盡到的最大責(zé)任。”直到曹永健這一輩,也就三五個人讀到了大專。在他的記憶里,每年都有不少初中沒畢業(yè)的少年在社會上闖蕩,蓄著長發(fā),叼著煙卷。這不禁令人心痛。因為自身受益于“差生”覺醒后的補課式閱讀,他隱約覺得應(yīng)該做些什么。
在走訪村落里孩子們的家庭后,曹永健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寫下了成立一所“鄉(xiāng)村螢火蟲閱讀館”的夢想——“我有一個夢想,孩子們完成作業(yè)后,能在公益圖書館里找到自己喜歡的書,書本能成為他們安心的陪伴。我有一個夢想,孩子們的世界里不只有大山,還有翻越大山的夢想。那么首先需要翻閱的就是一本本書籍。這是一個因閱讀而生的夢想,這是一個閱讀人對于故土最大的夢想。”他在朋友圈發(fā)出倡議,籌集資金與圖書,不到五天時間就募集到兩萬五千元。此后半年,采購圖書、定做書柜、選定地點……最終,他將書屋開放在一位家里碾米、榨油,人熱情且常有人來往的伯伯家。2016年6月18日,鄉(xiāng)村螢火蟲閱讀館落成,2500冊圖書同時上架。
“那是村里的一件大事,很多人來看熱鬧。”曹永健回憶道。日常的借閱很簡便,孩子們只需登記姓名即可。疫情前,他常常利用寒暑假返鄉(xiāng),開展伴讀活動,帶著孩子們讀書、看電影,給他們講山外的世界。于他而言,這更多的是一種收獲而非付出。登記表上反復(fù)出現(xiàn)的孩子,高中畢業(yè)后考入長沙的學(xué)校;伴讀活動中,在奶奶臂彎里聽故事的女孩已經(jīng)長成初中生……因為閱讀帶來的聯(lián)結(jié),他與故鄉(xiāng)的故事還在續(xù)寫。
2021年年末,應(yīng)朋友們的需求,曹永健發(fā)起了“螢火蟲教師讀寫營”這一民間讀寫共同體,并成立了一個線上社群。從第一季的30人發(fā)展至如今的200人,社群內(nèi)的老師們每日都會交流教學(xué)思考。“我說的不一定是對的,但愿意分享”的生態(tài),使大家更好地凝聚在一起。他們的讀寫活動也越發(fā)系統(tǒng)化、主題化,貼近教師教學(xué)實際的書目、榜樣教師和專家學(xué)者伴讀的講座,使好讀、善讀的氛圍日益濃烈。2024年夏季,曹永健應(yīng)勢發(fā)起了線下教學(xué)工作坊的邀請,60個名額在10分鐘內(nèi)被一搶而空,來自陜西、深圳以及湖南下屬各地市的老師們匯聚在一起。那些在各所學(xué)校走在教學(xué)改革前列的“異類”在這里激情地討論、分享自己的思考,享受智識增長的愉悅。這一年也是曹永健書房最為熱鬧的一年,很多來到長沙的朋友都愿意來到他這里坐一坐、聊一聊。“我們一起彈吉他、喝茶,聊教育、聊人生,你會覺得每個人都是少年、都那么天真,那真的是很寶貴的時光。”
曹永健所做的這些并非應(yīng)試教育中的考核項,也沒有為他帶來任何物質(zhì)上的回報,但他仍舊樂此不疲。教育實踐中當(dāng)然有不甘和苦悶,他允許自己一時消沉,但知道自己難以接受長久的停滯。因為一開始便認(rèn)定了要做小小的事、發(fā)小小的光,所以他既允許自己偶爾的平庸、無力,又享受自己的堅持、向上。“我還可以做些什么?還可以把學(xué)生帶成什么樣?‘螢火蟲教師’還有哪些可能?”這是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他希望以小小的“軀殼”去捍衛(wèi)自己尚未完全風(fēng)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