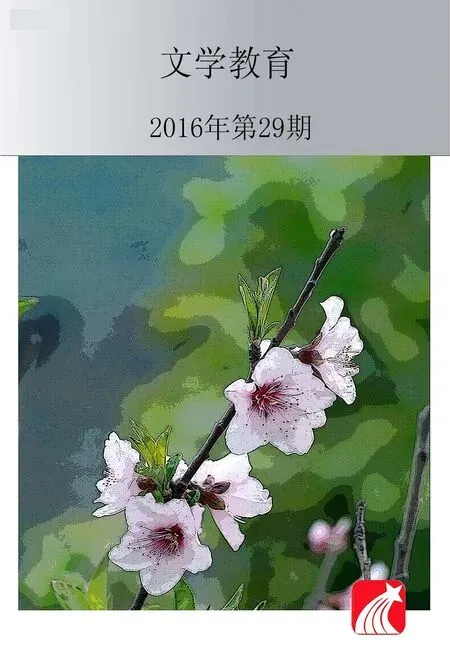在線課堂在中小學教育中的使用
周瑩
在線課堂在中小學教育中的使用
周瑩
教育在孩子的一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隨著科技的日益發達,先進的教育技術已經成為了教學進步的強大動力。同時,我國為了適應這種科技信息化的發展,已經在中小學普及了信息技術教育。針對目前高中物理課堂教學中師生課堂互動不夠充分、課堂教學缺少活為、傳統教學課件局限性較大等問題,本文主要從在線課堂在中小學教育方面進行說明,來介紹在線課堂及其優缺點,來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中小學 信息技術 在線課堂
2010年5月我國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2010年-2020年)》中專列一章闡述教育信息化,并開宗明義:“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影響”,確定了教育信息化的戰略地位。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滲透,在線課堂提供了一個網絡交流的平臺,教育者要積極利用好信息技術,進行信息的交流、反饋,有目的的對受教育者進行德智體美的發展。
一.在線課堂
1.在線課堂介紹。在線課堂是在Internet上構建一個實時在線交互系統,利用網絡在兩個或多個地點的用戶之間實時傳送視頻、聲音、圖像的通信工具。師生進行課堂交流的用戶可通過系統發表文字、語音會話,同時觀察對方視頻圖像,并能將文件、圖紙等實物以電子版形式顯示在白板上,師生可同時注釋白板并共享白板內容,效果與現場開設的課堂一樣。
2.在線課堂與教學的關系:從計算機輔助教學到信息技術的融合。現今,技術早已不單純是輔助工具,技術已成為全新的教育、學習方式應然實現的基礎。從最巧的計算化輔助教學到后來信息技術與學科謀程的整合,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內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今天的信息教育技術己不再是拘泥于與課程的整合,而是進入了與教育的融合階段。融合包含著互不分離、互相滲透、互相作用、一體化的過程,強調有機的結合、無縫的連接。信息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教學信息化從量的積累到全面推動教育質量提升的發展階段,信息技術超越了作為“工具”的輔助性質,強調信息技術與教育系統各要素的深度結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從教育觀念、學校結構、課程教學、政策等角度,多方面推動教育的變革與創新。
二.在線課堂的優越性
1.在線課堂是教師與學生互動的紐帶。在傳統教學模式中,老師和學生通過口頭的上課互動,來的知學生的上課情況,收集作業本來了解學生接受的情況,然后進行一本本批改后下發。這樣整個過程變得復雜同時增加了老師的工作量。
將在線課堂帶進我們的課堂,學生跟老師交流只需要通過計算機設備(如iPad),隨時隨地可以跟老師咨詢問題,老師想要下發任務也只需要通過電子設備,學生再通過上傳來上交。這樣極大的加強了學生與教師之間聯系,對中小學數字化教學革新而言,這種電子設備不僅是對學生身體負擔上的“減負”,更重要的是對課堂教學模式的變革。將傳統的紙質教科書電子化,利用電子設備的交互性、開放性特點,促進課堂教學模式從“教”為中也向“學”的轉變。
2.在線課堂是家長學校聯系的新紐帶。在傳統教學模式中,家長要了解自己的子女在學校的基本情況或學習情況,基本通過家長會,家訪,家校聯系本。但是由于家長時間很難集中起來,所以家長會一般在每學期末開。教師由于班上學生的數量,家訪也只能個別學生。家校聯系本家長只是檢查學生作業完成情況,對質量難以把握的問題仍然存在。
此時,在線課堂顯得尤為的重要。家長可以通過學校分配的用戶名、密碼登錄在線聽課,了解課堂情況。家長在聽自己孩子班的課時可以真實了解學生在校學習狀況。在線課堂的每節課都可以以視頻的形式保存下來,方便課后回看。家長有需要和教師交流的時候也可以通過在線課堂,單獨和老師隨時的視頻交流。在線課堂拉近了家長和學校的距離,能及時得知孩子的學習情況,及時和老師交流。
三.在線課堂的缺陷與解決策略
1.電子設備售價高,學校注重協商管理。電子產品的售價是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會有人質疑花費那么多值得嗎?也有對于普通的家庭來說,電子產品還是屬于奢侈。這時候學校可以統一購買和廠家盡量壓低價格,協商好價格,并耐心與家長溝通。
2.學生學習不專心,加強學生自控力。新鮮事物總是引起學生的“狂熱”,一些學生會把注意力放在電子設備上,而忽視了學習。這時候,教師要加強引導學生,使學生能夠合理安排,提高學習效率,加強學生的自控能力。
總之,任何新事物的產生都會有利有弊,我們在看到在線課堂對教育產生積極推動的影響時,也不能忽視它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我們要積極地看待和解決。
通過在線課堂,給學校和家長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此外,老師還可以將孩子在學校的表現情況、考勤情況、考試成績、每周和期末評語、學校的動態和臨時通知等發布在網上,讓家長在百忙之中也可以輕松掌握孩子的基本動態,同時,家長也可以通過該系統的留言箱,向學校和班主任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議!既可以幫助教師和家長及時解決孩子任何時刻出現的問題,又可以讓教師和家長共同分享孩子身上隨時出現的亮點所帶來的喜悅,使孩子少走彎路,健康成長。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