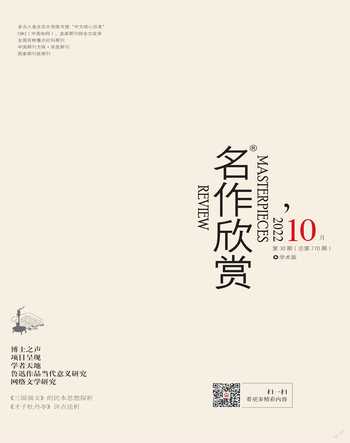論張愛玲的參差對照
黨夢榮
關鍵詞:張愛玲 參差對照 淡化主題 蒼涼 《紅樓夢》
張愛玲的小說有很強的可讀性,她的小說常常描寫生活中無奈的普通人,不追求悲壯而尋求蒼涼。在參差對照的手法里,崇高被解構,主題被淡化,有著《紅樓夢》第三種悲劇的意味;人物的塑造也更加立體,更接近現實里“真正”的人,讓讀者產生共鳴。“參差”是不整齊的意思,參差的對照不是黑白分明的對照,里面沒有直接批判或褒揚人物,沒有劇烈的沖突,這讓主題不再分明,給讀者更多遐想的空間。
一、參差對照的寫作手法——“第三種悲劇”
張愛玲的小說不致力于描寫善與惡、靈與肉的劇烈對抗,而是著重描寫一些普通市井人物的苦澀生活。參差對照指不完全互相對立的對照,不是截然相反的兩面,沒有絕對的壞人,也沒有絕對的好人。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參差的。
叔本華將悲劇分成三種:第一種是由極惡之人造成的,比如《奧賽羅》的依阿古;第二種是由盲目的命運和偶然的際遇造成的,比如俄狄浦斯王;第三種悲劇是由劇中人物地位不同,以及相互間關系所造成的,常常把道德平常的人物,置于一種無可奈何的場景,張愛玲的小說就是如此,人物在地位差距、利益驅使之下,一步步走向單方或雙方的悲劇。比如《半生緣》,曼楨一家是由姐姐曼璐做舞女維持生計,體貼的曼楨一直都很感恩姐姐。后來,姐姐嫁給了暴發戶祝鴻才,祝鴻才用經濟基礎來控制曼楨一家。曼楨對姐姐的歉疚、曼璐對祝鴻才的依賴、祝鴻才對曼楨美色的貪圖、姐姐對曼楨的嫉妒,這些利益關系讓曼璐和祝鴻才把曼楨推向深淵。但曼璐并不是一個完全的惡人,她也有自己的苦衷與欲望。
再比如,《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孤身回到娘家,二十八歲的她,被娘家人冷眼相待,她在家中處于弱勢,想要早日逃離娘家。而范柳原是擁有龐大家產的南洋巨商之子,但喜歡拈花惹草。他們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故事就此展開。正如作者本人所寫: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傾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并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婚了,但結婚并不使他變為圣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a在《第一爐香》中,或是為欲望,或是為愛,或是為利益,人物走向了悲劇的命運。葛薇龍本是一個單純樸素的女學生,可是為了學業,低頭去向姑姑尋求幫助。姑姑想用她來為自己招引男人,便用滿衣櫥華麗的服裝和富人的奢靡生活引誘她。面對繁多的靚麗服飾,她難以抗拒,為了奢華虛榮的生活,違背原則做了姑姑的傀儡。葛薇龍也曾想逃離,卻失敗了。奢華的生活和喬琪喬的吸引,讓她主動留下。經濟關系、情欲關系的交織,促成了葛薇龍的悲劇。她自己寫道,除了《金鎖記》里的曹七巧,她筆下全是不徹底的人物,他們更能代表那個時代的蕓蕓眾生。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已經過去的事情,而蒼涼是持續的狀態。張愛玲通過參差對照來寫這種蒼涼,將人物塑造得更加真實。
二、張愛玲筆下的蒼涼之美
“我喜歡悲壯,更喜歡蒼涼。壯烈只有力,沒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劇則如大紅大綠的配角,是一種強烈的對照。但它的刺激性還是大于啟發性。蒼涼之所以有更深長的回味,就因為它像蔥綠配桃紅,是一種參差的對照。”“蔥綠配桃紅”的參差對照意在營造一種蒼涼的意境,這種蒼涼不是強烈的悲壯,而是一種欲哭無淚的傷感。
在參差對照的寫作里,張愛玲選擇對現實生活中無可奈何的小人物進行描寫。因為在參差對照的寫作里,她盡量減少劇烈的沖突,所以這些人大部分不會將自己的傷感擴大化,做出極端的事情,而是仍然帶著一種只有自己最了解的傷感迷茫地活著,這更加接近現實生活中真正的人。這樣的寫作,沒有了作家主觀上的批判。就算作家筆下的人物做錯了事,在她的小說中也是可以被原諒的。特定的環境因素、地理位置、心理感受把人物推到了這樣的處境,讓人難生恨意,反而為他惋惜,為他感到難過和同情。張愛玲把這種無可奈何的感傷稱作蒼涼,認為這種蒼涼之感更能讓讀者感到回味。
張愛玲用“如匪浣衣”來描述這種悲哀,“如匪浣衣”
表達出一種心中被憂愁纏繞,不想洗臟衣服的感覺:“如匪浣衣”那一個譬喻,我尤其喜歡。堆在盆邊的臟衣服的氣味,恐怕不是男性讀者們所能領略的罷?那種雜亂不潔的,壅塞的憂傷,江南的人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心里很‘霧數。”b比如《半生緣》中的顧曼楨,失去了愛情,生活對她來說就沒有意義。只有和世鈞在一起,她才會感到真正的快樂。在他們最后一次見面時,世鈞心里想:“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說的,他們回不去了。他現在才明白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時間在掙扎。
從前最后一次見面,至少是突如其來的,沒有訣別。今天從這里走出去,卻是永別了,清清楚楚。”這里展現出一種失去愛人,有緣無分,如行尸走肉般空虛蒼涼的感受。參差對照寫法中展現的人物,更符合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的心理,不是每個人都有革命的熱情、浪漫的熱血,與極端的沖動,于是人們在迷惘時,常常會陷入一種虛無的傷感,體會到生命的無力感。
就算是做“錯”事的人,在張愛玲參差對照的寫法之下,讀者也不一定憎惡他們,甚至會為他們感到同情傷感,這種傷感也是張愛玲所營造的蒼涼。在《第一爐香》的開始,葛薇龍是一個積極向上的女學生,可是在梁太太的利誘下,在喬琪喬的吸引下,她逐漸淪為梁太太的傀儡,成為交際花為梁太太招引男人。在愛情上,喬琪喬不愛她,她卻對喬琪喬說:“我愛你,關你什么事?千怪萬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半生緣》中,曼璐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下海,可母親有時候還會覺得她的職業不體面,整天和一些亂七八糟的人混在一起。但她也是一個可憐人,她想要抓住自己渴求的東西,卻無能為力。為了家人,她付出了青春,可是卻得不到母親的疼愛。她想借妹妹的身體來拴住祝鴻才,一開始有了這個念頭,她也覺得不可以這樣做,但是后來,她的初戀情人張豫瑾不再喜歡自己,反而喜歡上了妹妹,她心里的怨氣越來越重,便把妹妹推向了深淵。這個過程是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曼璐歸為好人或者壞人。她害了妹妹,但她也有她的苦衷。以上的例子,讓人們感受到無可奈何的迷惘,這便是蒼涼的體現。
“蔥綠配桃紅”是色彩對比的淡化,不再是大紅大綠的刺眼搭配,在視覺效果上產生了和諧的美感。在人物的塑造上,張愛玲淡化了好壞美丑的對比,使得人物更加多元立體。在他們“如匪浣衣”般蒼涼的生活中,蘊含著古典的哀思之美,如林黛玉嘆息落花逝去的愁緒。參差對照下所產生的傷感不是強烈沖突下的大悲大慟,更類似于淡淡的愁霧籠罩。
張愛玲在自傳小說《雷峰塔》中,就寫出了這種古典的愁思,表達了對蒼涼生活的體悟。琵琶是張愛玲在小說中的化身,面對時代的變遷,她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看見字典里夾著的枯黃花瓣,她便感嘆鮮花今朝艷麗,明日枯萎,傷感落淚。
三、創作之源——《紅樓夢》和美的追求
張愛玲參差對照的寫法受到《紅樓夢》等古典白話小說的深刻影響。她對古典白話小說十分喜愛,從八歲第一次讀《紅樓夢》起,每隔幾年都要重新再讀,而且還有研究著作《紅樓夢魘》,她還將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翻譯成現代漢語。
張愛玲參差對照的寫法從《紅樓夢》中汲取了很多養料,比如在人物的塑造上,將人物寫得復雜,而不是有著簡單的好壞之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說,曹雪芹不再寫女子“如花似玉,一副臉面”,不再“凡寫奸人,則用鼠耳鷹腮等語”。而張愛玲對她筆下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她自己寫道:“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愛,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這種參差對照的手法在人物塑造和故事敘述上形成了一種悲涼的美感。
比如葛薇龍上進求學,卻又囿于虛榮,渴望愛情,最后悵然若失;霓喜干練聰明,卻喜愛物質享受;曼楨善良溫柔,但心軟,不夠堅定;世鈞憨厚老實,卻也自卑多疑;曼璐害了曼楨,但她有自己的苦衷;叔惠世故老成,但和世鈞、曼楨有著真摯的友誼。張愛玲對人物進行了多維度的塑造,不像以往的通俗小說,注重通過充滿戲劇性的情節來推進故事。
張愛玲通過各種細節描寫讓人物豐滿,重心從講故事轉移到塑造人物上來。張愛玲的故事并不復雜,但人物很豐滿。人物性格變得豐富,減少了好壞善惡之分,主題隨之淡化。在《連環套》中,作者巧妙地將霓喜一次次地與有錢男子同居比作連環套。每次失去一個男子,她就去尋找下一個。這些男子貪慕她的美色,但都不與她結婚。她沒有任何名分,那些人隨時可以將她拋棄,但是她為了生計與物質的享受,還是一次次地走入圈套。她曾經也追求過愛,結局卻總是灰心,只得到“殘羹冷炙”。通過張愛玲的講述,我們看到霓喜并不是一個令人厭惡的壞人,她追求愛情,但她也不是冰清玉潔的佳人。這樣既好又壞的人物,使得小說的主題淡化。主題的淡化,留給讀者更多想象的空間,可以使讀者從多元的角度進行解讀。傅雷曾批評張愛玲的小說《連環套》沒有主題,但她小說的引人之處便在于此。沒有了明確的主題,少了說教,多了悲憫,小說意蘊更加豐富,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理解,這比較符合王爾德唯美主義“為了藝術而藝術”的觀點。
在她營造的蒼涼世界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紅樓夢》的影子,尤其是古典式的哀思。在《雷峰塔》中,琵琶看到枯萎的花瓣會落淚,正如《紅樓夢》中林黛玉的“葬花落淚”。《紅樓夢》體現出一種“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的虛無蒼涼,而《雷峰塔》中引用佛家寶卷的話:“今早脫下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生活的不安與彷徨使人們被迫走向虛無與寂寞,誰也不知道明天是何模樣。
張愛玲在自己的小說中常常對事物詳細地羅列,也讓人看到《紅樓夢》的影子。她認為古典文學的細節描寫彌漫著“大的悲哀”,她用古典式的細節描寫來營造蒼涼的氛圍,如《雷峰塔》中寫道:“是夏天,窗板半開半閉,回廊上的竹簾低垂著。陰暗的前廳散著洋服,香水,布料,相簿,一盒盒舊信,一瓶瓶一包包的小金屬片和珠子,鞋樣,鴕鳥毛扇子,檀香扇,成卷的地毯,古董——可以當禮物送人,也可以待善價而沽之——裝在小小的竹篋里,塞滿了棉花,有時竹篋空空的,棉花上只窩著一個還沒收拾的首飾,織錦盒裝的古書,時效已過的存折,長鋅罐裝的綠茶。”c以上是琵琶的母親和姑姑出國時,張愛玲對府中冗雜事物的描述,此處營造出一種沉悶壓抑的氣氛。在小說中,琵琶的弟弟陵要跪三炷香的時間,琵琶在這三炷香的時間中覺得恍若隔世。她在黑暗的房間中聽到窗戶外面街道電車的行駛聲、汽車喇叭、包車夫的小聲叫喊、大甩賣的叫賣聲,樂隊演奏《蘇珊娜》的樂聲……這樣的描寫,讓人感受到琵琶在黑暗房間中的寂寞與孤獨,使人略見《紅樓夢》的影子。面對現實中的苦痛,人們在虛無中走向細節。在這些瑣事中,人們沉浸了自己,暫且擱置了莫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