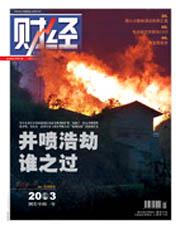發展中經濟的文化遺產定價
由正在消失的北京胡同和四合院引發的社會關注,其實是經濟學面臨的“發展的難題”之一。許多國家在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都無法避免對其文化遺產和傳統價值的巨大破壞。這一西方現代性問題,在一切非西方社會總要表現為“雙重的現代性問題”。不過,我這里要討論的是這一現象包含的經濟學問題本身的性質。
----為獲取“集結經濟效益”而大規模開發老城區所涉及的負面效果,在“科斯定理”的視角下,等價于“河流污染”、“工業噪聲”或“不可再生性資源的開采”這類具有外部效果的經濟學問題。一方面,經濟活動本身帶來正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這些經濟效益的享有者沒有承擔經濟活動所帶來的全部負面效應,于是可能發生“過度”經濟活動的“道德風險”。社會公益的代表者在裁決這類案件時往往感到異常棘手,因為得不到充分信息來判斷經濟活動的“最優程度”。盡管有如此的困難,就眼下這例北京四合院問題而言,卻不缺乏足夠的經濟學根據來判斷其利弊的傾向性。
----讓我把這一判斷先寫在這里:主要由于未來世代人口的時間貼現率低于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代人口的時間貼現率,并且在當代人口與未來人口之間缺少“討價還價”的市場機制,所以城市開發總是傾向于忽略被開發地面上的文化遺產的未來價值。
----圖一刻畫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I、II及III的城市土地價值和地面文物的保存量。注意:土地價值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II增長最快,相應地,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II的后期,文物存量的下降速度最快。這一特征事實可從下面的分析得到解釋。
----文物有兩個突出的經濟學特征:(1)在給定的“長期”內,其供給總量是固定的;(2)地面文物所占用的大片城市土地,在經濟發展中會不斷增值。保存文物需要支付的主要機會成本就是放棄對文物所占的土地進行開發帶來的經濟好處。在僅由一個人構成的“社會”里,這一權衡不帶來任何經濟學上的麻煩,因為這同一個人依照自己的偏好,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消費”較多的文物,在經濟發達階段“消費”余下的文物。圖二刻畫了這一文物消費問題的“最優”選擇。
----在圖二中,彎曲的“投資回收邊界”(由文物所占的土地開發增值的技術條件決定)與兩條直線相切。如果決策者的時間偏好(即未來單位消費品的效用與本期單位消費品的效用之比與1的差)是r0,那么他的最優選擇應當是C0,即在本期消費掉C0單位的文物,而將余下的文物保存到未來去消費。如果決策者的時間偏好變動到了例如圖二所示的r1,那么最優的本期消費量將變動到C1。顯然,C1----當人們處于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時,增長率與資金回報率都比在低速發展階段時高得多,從而人們的時間偏好也相應地高得多。也就是說,如果其它方面都一樣,那么體驗著經濟高速增長的人總會比沒有體驗著高速增長的人更加行為短期化。
----問題在于:未來的人們將處于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的階段(例如圖一中的階段III),而眼下我們這一代人正在經歷的,是前所未有和將來也不大可能持續存在的高速增長(例如圖二中的階段II)。這使得我們當代人口的時間偏好大大地高于未來人口的時間偏好,這相當于圖二中r0與r1之間的對比。如果問題僅僅是時間偏好方面的,那就還構不成經濟學的“發展的難題”。因為兩代人之間可以進行“交易”,在圖二中就是以C0-C1交換U(C1)-U(C0)。發展的“難題”在于:沒有任何市場機制可以讓未來世代的人口與現在世代的人口進行“討價還價”的交換,從而決定一個市場價格來配置這些原本屬于“代際人口”的資源。我們能夠依賴的,只有我們自己的“道德”和傳統留給我們的“禁忌”。
----對“市場”保持懷疑態度的人或許會因此而轉向“政府”去尋找有效配置“代際資源”的途徑。可惜,政府是由一大群與現實經濟有著千絲萬縷利益關聯的人組成的,而且這些人往往正好分享著地產開發的巨大經濟利益。臺灣地產開發與承建方面爆出的無數丑聞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真正代表、或有希望代表“道德力量”的,是來自民間的文物保護分子。他們很少與文物保護發生直接的經濟利益的關聯,也很少有權力以“保護”之名行“腐敗”之實。他們良知所本,不外是對傳統文化和未來世代的關注。讀者們應當行動起來,與社會良知結盟,以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力量幫助建立與未來世代的中國人實行利益交換的機制(例如與我們這代人的養老金掛鉤的保護未來人的文物的“交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