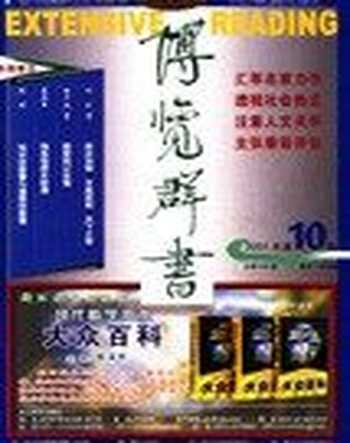學術(shù)評獎:誰來裁判評委
鄧曉芒 趙 林 彭富春
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1994—1998)獲獎成果,于2001年1月22日在《湖北日報》公示之后,學術(shù)界輿論嘩然,一些教授強烈反映,評獎的結(jié)果不能讓人信服,評獎的組織、程序上存在一些問題。
評獎結(jié)果:評委獲獎多
教師反映的問題首先是,評委參評、獲獎特別引人注目。如,哲學社會學學科組全部5位復評評委(負責復評并參加終審)均有成果參評,結(jié)果是獲一等獎2人,二等獎2人,三等獎1人,5位全部得獎,中獎率100%。同是這個學科組負責初評的7位專家(即初評委),4位有成果參評熎渲2位申報哲學社會學組,分別獲二、三等獎;2位申報綜合學科組,均獲三等獎,申報獲獎率也是100%。此次哲學社會學組共評出一等獎3個,其中評委得了2個,占66%;二等獎6個,其中評委得了3個,占50%。其他學科組也存在類似現(xiàn)象。如,歷史組:復評委5人,其中獲二等2人,三等2人;初評委6人,獲一等2人,三等3人。經(jīng)濟一組:復評委6人,獲一等2人,二等3人,三等1人;初評委5人,獲二等2人,三等3人。組濟二組:復評委6人(其中1人兼初評組組長),獲一等2人,二等2人;初評組8人(其中1人兼經(jīng)濟一組復評委),獲二等2人,三等3人。法學組,復評委6人,獲一等2人,二等2人;初評委6人,獲二等2人,三等2人。……(評委沒獲獎者,可能有兩種情況,或是沒有申報,或是申報而被淘汰。即使都是后者,評委獲獎比例亦很可觀。)
其次,從部門獲獎看,一些單位的教研室獲獎比例很高。比如,武漢大學哲學系馬列主義教研室有7人申報,其中有6人獲獎,獲一等獎1名,二等3 名,三等2名。由于同一個教研室內(nèi)近親繁殖的原因,這種同部門獲獎比例就同時表現(xiàn)為同一師承關(guān)系的獲獎比例。武大哲學系馬列室6名獲獎者中,有5名是師生關(guān)系;這些師生中,老師為本次評獎活動中哲學社會學組復評組組長、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委會副主任、省有關(guān)領導和相關(guān)部門負責人參加的聯(lián)席會議成員,而他的一名嫡傳弟子則鬼使神差地被任命為哲學社會學組的初評組組長。師生二人,分掌初評和復評之大權(quán),評委、部門、師承三者的關(guān)系,錯綜復雜地糾結(jié)在一起。
評獎過程:“一錘子買賣”
當記者就教師們反映的評獎問題進行采訪時,負責評獎具體實施的省社科聯(lián)主要領導說:“這次評獎結(jié)果,不敢說是百分之一百都是科學、準確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九十八是客觀公正的”,“這是專家們評出來的,打分的情況就是這樣。評獎的程序正確。我們尊重專家意見。”對于教師們認為哲學社會學組評獎不公的意見,社科聯(lián)召開了復評組、初評組專家的座談會,社科聯(lián)的這位領導總結(jié)說:“座談會認為,評獎是公正的。”哲學社會學組復評組組長在接受采訪時說:“整個評獎是有嚴格程序和規(guī)定的”,“我們尊重初評組意見;在充分尊重初評組意見基礎上作微調(diào)。”“武大的馬哲是211重點學科點,在全國也是較強的。我們多一點,別的學校也沒有意見。”初評組組長說:“我們是執(zhí)行上面的安排、指示,按程序、規(guī)章進行評獎”,“評獎是公正的,大致反映實力和水平。”
那么,評獎是否按規(guī)定的程序進行的呢?
首先,教師們反映,有的學科最后評出的結(jié)果是基本根據(jù)初評排名得出的,復評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按省社科聯(lián)2000年10月23日印發(fā)的《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1994—1998年)評獎實施方案》規(guī)定:“復評:由省評委會學科組負責。各學科組在審閱初評推薦成果材料基礎上,認真復核,充分醞釀,集體評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jīng)Q定獲獎項目,報省評委會終審。”這就是說,復評必須投票。但實際上在復評中,哲學社會學組沒有重新投票(其他組有無投票未詳),只是在初評組打分排名的基礎上作了“微調(diào)”。復評組組長說,復評是在充分尊重初評成果的基礎上作了微調(diào)。他解釋說,因為基本同意初評意見,所以沒有重新投票。社科聯(lián)負責人也說:“復評時,復評組組長提出,初評時排在后面的一位教師的成果沒評上‘很可惜,應評上三等,但因其他評委反對就不再堅持;他對別的評委提出的給其他教師微調(diào)的意見則都能采納,說明這位組長是民主的。”但這正說明:復評沒有投票。教師們反映說,復評高于初評,不能讓初評影響復評。初評不應該排名,如果把初評的排名作為復評的依據(jù),又充分尊重初評的結(jié)果,那么復評就等于是走過場。當然,復評有最終決定權(quán),但是這種最終決定權(quán)不應體現(xiàn)在決定“在充分尊重初評成果基礎上進行微調(diào)”。因為按程序規(guī)定復評必須投票。
其次是終審的投票問題。《<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勵暫行辦法>實施細則》規(guī)定:“終審成果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評委通過方為有效,并以得票多少依次排名。”《實施方案》也規(guī)定,“終審成果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評委的同意,并以得票多少順序排名。”這說明,按規(guī)定,終審必須對每一項成果進行投票(否則就不可能是“以得票多少依次排名”)。社科聯(lián)主要領導說:終審是經(jīng)過投票的;因為票數(shù)都相近,所以每一個獲獎等次中各成果的順序仍按復評時排的順序不變。據(jù)他介紹及他提供的書面材料,終審只用了一天(2000年12月28日。事實上,社科聯(lián)領導對提出意見的教師說:終審與復評是合在一起進行的,復評用了一天半,終審只用了半天)。省評委全體成員即不同學科的47個評委(有的是有關(guān)領導)在一天(或半天)內(nèi)對405個獎項投票,如何投法?
復評主要根據(jù)初評的排名順序,終審又按復評的排名順序,那么實際上就意味著,初評的結(jié)果基本上決定了終審的結(jié)果。難怪教師們強烈反映,這種做法是“一錘子買賣”!如果以有關(guān)規(guī)定對復評、終審的要求來衡量,上述評獎過程中的實際做法,能否說是嚴格按照規(guī)定的程序進行的呢?
評委推選:“隨機抽樣”
終審相信復評(負責終審的評委會就是由各個學科的復評組成員加上有關(guān)領導組成),復評又“充分尊重初評”,那么,初評委的組成員以及他們的投票,其關(guān)鍵程度可想而知。可是,這些初評委是如何產(chǎn)生的,過不過硬呢?
反映意見的教師們對初評委是如何產(chǎn)生的以及他們的代表性、權(quán)威性等問題提出了質(zhì)疑。社科聯(lián)主要負責同志在回答記者問時說:初評組成員產(chǎn)生是先讓各校、科研院所按有關(guān)要求(有正高職稱、水平高等)推選出六百三十多名專家名單,在考慮學科平衡、學校平衡的原則下,隨機抽樣出五十多名(五十三名),分八個組。最后經(jīng)過評委會審定同意。(按《湖北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勵暫行辦法》,評審人員的資格審查權(quán)是聯(lián)席會議而不是評委會。這里暫且不論。)總之,初評委是從六百三十多名專家?guī)熘小半S機抽樣”組成的。
此次廣大教師們反映最強烈的意見之一就是一些學科組的評委水平不過硬,無代表性,無權(quán)威性,但是這些水平不過硬且無代表性、權(quán)威性的初評委們得獎率卻非常高。在初評委五十三人中,共有三十七人獲獎,獲獎比例為69.8%(由于并非每個評委都申報了成果,因此實際上的申報獲獎比例還要遠高于此)。對照全省申報成果約1420項,共評出一至三等獎392項,獲獎比例為27.6%,這兩個比例數(shù)字之間的懸殊是耐人尋味的。
一些教師反映,初評委的覆蓋面不夠廣,形成外行評內(nèi)行;有的學科組設置不合理,如哲學與社會學放在一個組不合適,無論是按國務院的學科分類還是按武漢大學的學科設置,哲學與社會學都不應放一塊評。評委會、社科聯(lián)、復評組、初評組的有關(guān)負責同志也承認,有些學科組評委的專業(yè)設置“不盡合理”,即評委組成的學科覆蓋面不夠?qū)挕脑u出的結(jié)果看,教師們反映,在一些學科中,真正優(yōu)秀的成果沒被評上或評低了,一些粗制濫造的成果卻被評上或獲得高獎項。如果評委確實出于公心,那么,這種評選結(jié)果正好說明評委在學科分布及鑒定水平上有問題。這些應該都是初評委選定不合適造成的。
事后社科聯(lián)負責人也曾承認,所謂的“隨機抽樣”實際上是由社科聯(lián)辦公室的一位主管主任根據(jù)個人的標準“隨機”地定出初評組評委。作為省政府獎評審活動這樣一件嚴肅的事情,其具有“一錘定音”的極大權(quán)力的初評委們竟然是通過如此一種“隨機抽樣”方式產(chǎn)生出來的!
幾點思考:
教師反映,評委參評并獲獎多、獎項高,是本次評獎中突出的問題。按一般的說法是,評委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根據(jù)國情,雖然評委參評的事也不少,但在不得不允許評委有成果參加評獎的時候,一般都進行一輪通訊評審,即通過郵寄參評成果請全國范圍內(nèi)的著名專家評審。
關(guān)于沒有設置通訊評審的原因,社科聯(lián)主要負責人解釋說,主要是經(jīng)費問題。本來規(guī)定是兩年一評,每次評150個獎項;這次卻是5年一起評,要評出375個獎項(實際評出392個),但因財政困難,給的仍是評一屆用的經(jīng)費。先要保證發(fā)獎金,通訊評審的經(jīng)費就不夠了。但教師們反映說,要評就要認真,把真正有水平的成果評出來;經(jīng)費不夠就不要評,評出的結(jié)果不公正,還不如不評,因為不公正的結(jié)果只會打擊積極性。他們提出,到底為什么評獎,是為評獎而評獎,還是為了促進學術(shù)發(fā)展而評獎?
政府委托社科聯(lián)組織實施這次評獎,本來是為了促進學術(shù)發(fā)展。但如果事與愿違,就必須總結(jié)一下了。面對教師們反映的評獎結(jié)果是否公正的問題,社科聯(lián)在總結(jié)時也承認,除了上述評委的學科專業(yè)覆蓋面不夠全面之外,評獎用的時間太短,標準也不十分規(guī)范。但恐怕可總結(jié)之處不只是這幾點。要保證公正,最要緊的是必須在程序的制訂和實施上嚴格把關(guān),即訂好游戲規(guī)則,大家遵守。本次評獎,在制訂和實施游戲規(guī)則上都存在一些不嚴格的地方。一些初評委、復評委及社科聯(lián)負責人都說,評獎是嚴格按規(guī)定程序進行的,是公正、科學的。但上述初評排名直接決定復評乃至終審排名的情況就說明,本來設定的用以保證獲獎成果水平的一些程序,并沒真正起到應有的作用。制訂的程序沒能得到嚴格執(zhí)行,恐怕就談不上科學、公正了。
制訂程序也不是沒問題。比如說,《實施細則》規(guī)定評委會辦公室負責“協(xié)商推薦評委會成員”,但是,跟誰協(xié)商,如何推薦,都沒規(guī)定,結(jié)果就成了辦公室人員的“隨機抽樣”。如果有誰提出評委不該由辦公室的人來推薦,當事人卻可以說《細則》有這個規(guī)定,這是按程序辦;但“協(xié)商推薦”就是辦公室人員“隨機抽樣”嗎?這個程序的制訂,本來就沒打算“講認真”。又如,《實施方案》規(guī)定“初評采取定量打分”,“并按得票多少產(chǎn)生初評推薦名單”,但,按得票多少與按得分多少產(chǎn)生的名單并不可能一致,到底按票還是按分呢?實際操作是按分。教師們對評分制意見很大,因為評分制可能會給予不公正評委更大的影響評審結(jié)果的權(quán)力和空間。這個程序在制定和實施上都有問題。有的評委自己也承認“游戲規(guī)則有問題”。……進一步說,程序即游戲規(guī)則的制訂,是關(guān)乎全部學者的研究、學術(shù)發(fā)展的事,本來應該經(jīng)過廣大學者的討論,從學者中來,又到學者中去,才有可能是科學、公正的。僅僅由某些辦公室人員關(guān)起門來制訂,這種制訂本身就是走過場,并為不公正的評審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程序之外,也有不認真之處。如,教師們反映,初評用五天顯然不夠。一個學科組平均有一二百項申報成果,這些成果每個評委都應看一遍,根本看不過來,如何評審?現(xiàn)在,社科聯(lián)及一些評委也承認評審時間太短。計劃用五天初評、一天復評,是否經(jīng)過論證?或是拍拍腦袋,主意上來?……種種隨意為之的做法就自然地透露出一種不認真的態(tài)度。
話說回來,湖北省這次評獎的問題,只不過是全國類似眾多問題中的一個例子。教師們反映,在全國范圍內(nèi),十余年來,相當?shù)囊恍┰u獎,評職稱、評基金,都是在那里貌似認真地按照程序走過場,實際起作用的主要是人情關(guān)系、裙帶關(guān)系、互利關(guān)系,這已經(jīng)是公開的秘密。這種風氣愈來愈利害。大家都對此深惡痛絕,可是一輪到自己就身不由己,陷入怪圈。這是我們民族幾千年傳統(tǒng)中不良的因素,即宗法觀念、人情觀念等等在起作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情大于法,大于原則,這種風氣跟社會上的腐敗之風有著同樣的歷史文化根源。它已經(jīng)嚴重影響、制約著學術(shù)的發(fā)展,腐蝕著學者的心靈。指出它的危害,喚起全社會的人們來抵制它,是完全必要的,十分急迫的。如果不抵制這種惡劣風氣,不制定出嚴格的學術(shù)競爭機制,恐怕不論誰當事,不管他本來想多么清正,也很難不陷入惡劣風氣的包圍之中。
最后,我想以武漢大學歷史系李工真教授的一段話作為結(jié)尾,看它是否能作為我們的借鑒,以利于學術(shù)的發(fā)展、人才的培養(yǎng):
根據(jù)“柏林大學模式”,無論講師,還是教授,絕不允許在同一所大學里進行職稱升等,而必須換一所大學才能進行。任何一所大學里的教師隊伍,也絕不允許主要由同一所大學畢業(yè)出來的人組成,而要由來自各大學的佼佼者組成。一名學者申請教授資格,需經(jīng)五位校外同行專家評議,這五人必須既與申請者無任何師承關(guān)系,也與他無任何合作關(guān)系。申請者在獲取教授資格后,需要在外校有教授位置空缺的情況下,方能成為正式教授。這不僅掃除了門戶之見,也嚴肅了成果鑒定與職稱評定上的科學性,因為任何一位教授都不能允許沒有真才實學者取得與他們千辛萬苦才換來的同樣地位。這是德國人最先做出來的防止近親繁殖和裙帶關(guān)系的現(xiàn)代化措施,后來也在世界各國現(xiàn)代化大學中普遍推廣開來。熇罟ふ妗丁鞍亓執(zhí)笱模式”及其發(fā)展》,《人文論叢》2000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