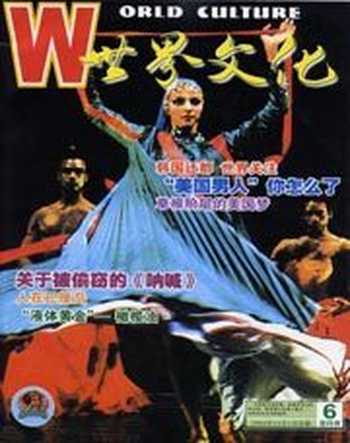俄羅斯的都市“名片”
顏廷劍

埃爾米塔博物館(即冬宮)是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被俄羅斯人稱為自己的盧浮宮;國會大廈建筑是“自己的白宮”;自己的凱旋門比巴黎的凱旋門還要高大。俄羅斯以獨創性自立于世界民族建筑雕塑之林。
紅都
莫斯科曾謂“紅都”。單從建筑角度看,克里姆林宮紅場、紅墻、深紅色的列寧墓和斯巴斯基鐘塔上的紅星,是它的名片。如今面對這“名片”,塔鐘近在咫尺,卻仿佛久遠的歷史回聲若斷若續。
克里姆林宮內,亞歷山大公園騰飛的駿馬(雕塑)在無聲嘶鳴;造型獨特的噴泉雕塑激情奔涌;無名烈士墓雕莊嚴肅穆;普京辦公大樓黃白色相間、端莊靜謐……這是莫斯科的“中南海”,卻同時又是東正教圣殿———克里姆林宮里,金頂燦燦,白墻耀目的教堂十分令人矚目。教堂里裝修得金碧輝煌,各類宗教神祗名典裝飾壁畫琳瑯滿目。搖曳的燭光下,涌動著的各色信徒合手劃十,虔誠地膜拜心中至圣的神祗。
教堂建筑中的政治解碼不言而喻:蘇聯劇變解體后,統一的意識形態瓦解,回歸傳統的宗教便來填補空白。如今,東正教信徒已占俄羅斯人口一半以上。每逢宗教節日,普京總統會率官方政要蒞臨慶典。其政治目的,自然是想藉宗教信仰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難怪信息時代的俄羅斯大地教堂林立,克里姆林宮里的教堂,也如此香火鼎盛。
直觀城市整體建筑,作為世界一流國際大都會的莫斯科,很少紐約、香港那樣櫛比鱗次的摩天大樓,甚至不比北京上海拔地而起的現代建筑群,有的是普通民居多年不變的單調和陳舊(可能與經濟不景氣有關)。但是,很少21世紀標志性建筑的莫斯科,卻有許多一流大教堂巍然矗立、蔚為壯觀。它們將古希臘羅馬建筑、拜占廷、巴羅克式,甚至哥特式、洛可可風格的局部特征兼收并蓄,突出俄羅斯式特征。教堂內七彩玻璃穹頂華光璀璨,似幻似真,墻飾壁掛,宗教名典名畫,馬賽克鑲嵌和噴塑技藝,各逞其妙,流華溢采。
詮釋如此建筑特色,東道主索菲亞博士另有高見:“我們不想讓莫斯科成為鋼筋水泥柱的‘森林,而要她成為綠地、綠樹、綠色小木屋(俄羅斯有錢人都在城郊森林蓋別墅,共名‘小木屋)和綠水青山環抱的‘綠色女神。莫斯科河是她的項鏈,河邊民族特色的建筑(許多教堂)是項鏈上的珍珠……”果真如此這般,莫斯科的城市建筑,她的5個飛機場、60多座大戲院、1000多所學校,大大小小的教堂以及數不清的各色建筑雕塑,全都掩映在綠色森林的懷抱中。20世紀的“紅都”將成為21世紀的“綠都”。
“石頭的史書”
俄羅斯無數個里程碑式的建筑,標識出民族發展史的“無數點的運動軌跡”。這些“里程碑”序時性的排列組合,構成城市發展的編年史;一座城市的“編年史”,大而化之為民族文化發展史———這是“石頭的史書”。莫斯科如此,圣彼得堡的建筑雕塑也不例外。
圣彼得堡的建筑離不開“圣”字:教堂和《圣經》;更離不開“彼得”;耶穌的12門徒之一叫彼得(意為“盤石”)、彼得大帝也名為彼得。圣彼得堡隨處可見彼得大帝的雕像:策馬揚鞭、英姿勃發的“青銅騎士”;文治武功、奠造民族大業的俄國沙皇;劈波斬浪創建海軍、揚帆遠航開疆擴土的民族英雄;正襟危坐、指點江山的千古一帝……總之,彼得大帝的系列雕塑,溢美地突顯了他借鑒歐洲科學技術,拓展俄國“開放”改革的史實,從而打開了俄國“看歐洲的窗口”,奠造了沙俄帝國的鼎盛時代。顯然,彼得大帝的這些雕像不僅是圣彼得堡的“名片”,同時又是民族發展的碑碣,具有民族文化史詩的內涵和外延。
再看葉卡捷琳娜女皇的雕像:高聳入云的巨雕比彼得大帝和列寧的雕像更高大恢宏。氣度非凡儀態萬方的女皇睥睨世界巍然屹立,腳下環侍著她的諸位男性貴族寵臣。盡管雕塑不等于對葉氏的全面評價,但是,單就這雕塑對沙俄時代男尊女卑傳統觀念的反叛和挑戰,已十分令人刮目相看。
總之,建筑和雕塑記錄了、甚至溢美了兩位大帝的歷史功業,它與專制暴政、殘酷壓榨家奴、鎮壓農民起義的血腥統治并行不悖。所以,彼得堡的“白夜”沒有給窮人帶來光明,涅瓦河的流水流淌著農奴的血淚,正如俄羅斯民謠所吟:“人民的兩肋,被老彼得磨平……”
于是,就有阿芙樂爾的炮聲。如今,阿芙樂爾戰艦已改成博物館,冬宮已成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它們本身就是“人民創造歷史”的鐵證。這里程碑式的建筑和雕塑,遍及俄羅斯大地——
不朽的知識巨人羅蒙塔索夫的雕像,將永遠屹立在列寧山上;隨處可見的普希金塑像和博物館;阿爾巴特大街上,激情勃發的詩人攙著夫人娜達麗亞(雕塑),曾經關押過車爾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仁人志士的彼得堡要賽,是個尸骨堆砌、鮮血澆鑄的建筑;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前,工農兵昂首挺胸的巨雕在眺望克里姆林宮的紅星;還有保爾·柯察金的雕像、卓婭的雕像、加加林的雕像,甚至現代派光怪陸離的雕像,特別是氣貫長虹的宇航雕塑……這一切的一切,無聲而又撼聾發聵地確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創造者———這是“石頭史書”的主題。
“土饅頭”
今天,這些“石雕銅塑”向世人銘證:無論帝王英雄還是平民百姓,其物質生命都無一例外地歸于了泥土。“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需一個土饅頭”。但是,俄羅斯的墓碑建筑雕塑,卻是獨具特異風采的藝術精品。
請看蘇軍烈士紀念碑雕塑:碩大無朋、厚重無比的巨書造型,漆黑厚重的巨石書頁翻展開、豎立著,4萬多反法西斯烈士的英名一一彪炳“石冊”、個個赫然在目———這是不朽生命的悲壯史詩、民族英雄的交響樂章!當我們心顫神悸地解讀這血肉筑成的雕塑時,先后有兩對新婚夫婦前來拜謁。身著潔白婚紗的新娘和新郎一起把紅玫瑰花敬獻烈士墓碑———前人的尸骨奠基了后人的幸福———“忘記,就意味著背叛!”
烏蘭諾娃的碑雕,是瑩白大理石浮雕的芭蕾舞(白天鵝)造型;法捷耶夫的墓雕是燙金大字的深紅色大書;而赫魯曉夫的墓碑則是黑白相間的塊壘石雕———圖解著是非功過、皂白分明的歷史評說,也詮釋著民眾心中不平的塊壘……還有鐵鏟戰刀、奔馬蒼鷲、精巧的幾何圖形、怒放的玫瑰、流瀉的五線譜音符、妙曼的豎琴、滯重的鐵錨……凡此種種各逞其妙、各寓玄機的各色墓碑雕塑,使不同身份,不同貢獻和影響的逝者,各得其所地盡展生命華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