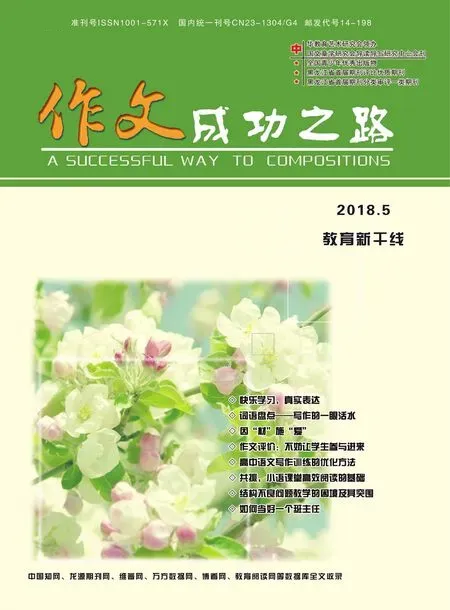本土資源與幼兒園教育的有效結合
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淞南幼兒園 陶艷萍
我園位于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江蘇省歷史文化名鎮——千燈鎮。這里是明末清初著名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的家鄉、昆曲創始人顧堅的故里。古鎮物產富饒,人杰地靈,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優勢,素有“金千燈”的美譽。為我們開發本土文化教育提供了大量的寶貴資源。
一、發掘本土特色,促進園本課程生成
1.結合家鄉特色,開發園本課程
為了立足我園實際,結合家鄉千燈的特色,以“燈、橋、昆曲”為切入口,開發園本課程。我們以年級組為單位,進行思考、撰寫教案、試教磨課,從而不斷的完善以“燈、橋、昆曲”為主的園本課程。例如:小班美術活動《七彩燈籠》、中班科學活動《牢固的紙橋》、大班美術活動《昆曲頭飾》的呈現,都體現了教師間的相互配合和不斷創新的精神。為園本課程的完善增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2.結合本土資料,豐富園本課程
為了更好地生成園本課程,僅僅依靠“燈、橋、昆曲”為主的園本課程往往是不夠的。因此,我們還利用身邊的相關本土的資料、書籍,采用資料里的某一元素,進行創新。使活動更游戲化,課程化。例如:大班韻律活動《跳皮筋》就是一個民間游戲改變而來的。教師通過打節奏的形式引導幼兒跟著童謠來感受節奏。本土資料中不乏有一些很具有傳統文化藝術的手工藝,這次對于幼兒來說是繁瑣、深奧的。經過我們的不斷提煉,向經典工藝的致敬,我們組織了大班美術活動《扎染方巾》。幼兒用紗線、皮筋、繩子等工具在織物上進行扎、縫、縛、綴、夾等多種形式的組合,最后進行染色。就是教師這種不斷探究、不斷專研、不斷創新,才能使園本課程不斷的豐富。
二、利用本土資源,創設特色游戲環境
1.巧用古鎮元素,創設角色游戲環境
根據燈、橋、古鎮等元素,進行角色游戲環境的創設。小班南面角色游戲環境,整體以藍色為基調,北面以黑紅為基調。利用鏤空雕刻,以及古鎮名居特有的屏風為隔斷,名居的屋檐為走廊角色游戲的大門口。為小班幼兒在游戲中,營造一種仿佛在逛千燈古街的氛圍。中班南北面角色游戲環境,利用燈、橋兩種元素。發動家長資源,家園合作,共同制作燈、橋小制作,布置在角色游戲環境中,讓幼兒在逛花燈中欣賞自己的作品。
2.巧用自然資源,創設戶外游戲環境
自然資源的利用已經不但是純粹的觀賞價值,而是更多地將其教育目標融入其中。農村最缺不的是沙土石木水。因此,在玩沙玩水區投放沙、土、水,幼兒使用沙、土、水和顏色創造出各種生動有趣的動植物。在建構區投放不同大小的木材,指導幼兒進行各種探索活動。不同高度的小樹墩成為梅花樁;長長的木板放在一個樹墩上化身為翹翹板;利用木材搭建橋、城堡、車軌等。拾撿河邊大小、形狀各異的鵝卵石,不僅可以進行畫畫、拼搭和建構,還能玩走石墩、小橋、跳房子、比比誰的小石頭多等游戲,較好地發展幼兒的運動能力和數數能力。
三、投放本土材料,開展區域游戲活動
1.根據主題活動投放材料
為了充分發揮自然材料的作用,我們依據主題活動有目的地投放游戲材料,將課程內容與區域活動相結合。在實施主題“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結合水鄉古鎮的環境特點,依次組織《參觀古鎮——千燈》《各種各樣的橋》等活動并結合主題投放相應材料。在美工區,我們幫助幼兒拍攝下參觀的水鄉古鎮的圖片,幼兒利用金粉、黑色卡紙、白乳膠,繪制一幅幅金千燈的小橋流水的作品;在建構區,我們投放各種積塑、廢舊物品(各種紙盒、可樂品等)引導幼兒建構千燈秦峰塔、三橋邀月等景點。投放多種本土材料,為幼兒營造一片新的游戲天地。
2.根據幼兒興趣和需求投放材料,一物多用
種子在區域活動中是比較常見的。在科學區,投放各類種子,啟發幼兒種植、觀察、記錄種子的生長過程;在美工區,通過種子粘貼畫,鍛煉幼兒的動手操作能力;在生活區,用勺子舀種子,用筷子夾種子,發展幼兒的手部精細動作。同樣,我們周圍也有大量的竹子資源。在表演區,用竹子做成木魚、響板、沙球等各類樂器,培養幼兒的節奏感;在手工區,有目的引導幼兒觀察竹制品,并用各種藝術形式表現出來,如折疊、剪切、揉捏和繪畫;在操作區,結合幼兒的實際發展水平,分階段投放不同的材料,提高幼兒的創造能力。這不僅滿足了幼兒自主探究事物的愿望,而且使主題活動體現了幼兒自主發展的功能。
3.根據幼兒的發展投放材料,體現層次性
由于幼兒年齡特點的限制,導致幼兒有不同的探索水平和探索能力。因此,我們要發掘同種材料在各個年齡階段中的利用,讓幼兒以自己的方法去學習與探索。如在編織區投放棕櫚葉,小班幼兒使用棕櫚葉打結、擰成繩子、穿項鏈等;中班幼兒使用棕櫚葉編制圍巾、花籃、圖形等;大班幼兒則使用棕櫚葉編制手槍、房子和小魚等。
人們都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教育應該結合地方特色,學會因地制宜,充分發掘本土資源。因此,在以后的教學實踐中,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打開思緒,開發本土文化教育資源,積累豐富幼兒的文化底蘊,激起幼兒熱愛家鄉之情,培養幼兒的文化創新意識和表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