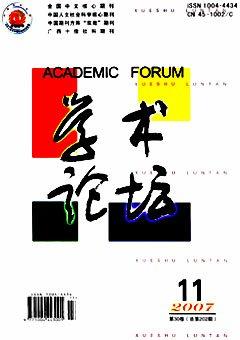湯因比“挑戰-應戰”之文明史論與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
閻 靜 徐臘梅
[摘要]文章闡述了湯因比提出的著名的“挑戰-應戰”文明互動模式的基本內涵,探討了該模式對全球化時代文明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價值和意義,認為文明“挑戰-應戰”模式將始終與人類歷史相伴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也必然要求人們在文明的深度和廣度上探討彼此間的關系。
[關鍵詞]“挑戰-應戰”模式;文明史論;全球化:國際關系
[作者簡介]閻靜,江蘇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博士生,江蘇鎮江212013;徐臘梅,江西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講師,江西南昌330000
[中圖分類號]D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434(2007)11-0065-04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是二十世紀西方史學界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其一生著作頗豐,重要作品多達幾十部,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人類觀察自身的視角。其巨著《歷史研究》十二卷本最完整、系統地闡述了他以文明為主線的人類歷史理論,重點以人類歷史上曾經和仍然存在的三十多個文明體作為研究對象和單位,對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人們對傳統歷史的認識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將新的文明研究的視角引人歷史領域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關于文明的概念,學術界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文明應該具有至少這樣幾種要素:城市化社會,代表更加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組織;共生經濟;公共建筑物與有紀念意義的建筑,代表更加復雜的精神生活。湯因比把某些概念如文化、社會、文明等放在一起綜合討論之后,指出:“在精神的意義上給文明一個定義。它也許可以稱之為創造一種社會狀態的努力,在這個社會狀態中,整個人類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家庭的成員,將在一起和諧地生活。這就是迄今已知的所有文明一直有意無意追求的目標。”可以這樣認為,所謂文明既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過程。它既是人們所追求的在最高水平上最好地實現了的人類集體理性,同時也是這種理性不斷逐步地得到實現的過程。湯因比對人類古往今來的諸多文明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比較,對于各種文明在普遍意義上的起源、發展、興盛、衰落以及解體都進行了獨到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著名的“挑戰-應戰”模式。
一、“挑戰-應戰”的文明互動模式
關于文明的起源,湯因比認為種族因素不是決定性的。歐亞非古代幾大文明再加上同樣輝煌燦爛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分布在世界各地,并非是由單一的種族承擔創造的重任。他也排除了“自然環境決定論”,盡管從某種意義上或者個別文明的獨特經歷來看,環境的嚴峻挑戰確實成就了有些文明的偉大崛起,而另一方面,過于苛刻的自然條件也殘酷地把某些處于萌芽狀態的文明扼殺于襁褓之中,使它們無力闖過生命的第一關。湯因比把文明的誕生,或者說是文明的強烈進發歸因于人類社會對外界挑戰的成功應戰,由此闡發了“挑戰-應戰”的文明互動模式。
人類在文明時代取得了重大的物質和精神進步,但前文明時期的人們同樣有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就,區別在哪?湯因比指出:“文明和前文明社會間的差別不在于是否存在或缺乏某些制度,文明同前文明社會的區別也不在于是否有勞動分工,在這種運動不止和停滯不前的反差中,我們最終看到了文明和原始社會之間的區別之點。每一個已形成的文明社會都指出了人類的目標,都賦予我們實現目標的方法。因此,盡管人類前赴后繼、加倍努力欲實現的那個目標是始終難以看到的,但我們卻知道它到底是指什么。”那個目標就是人類所努力追求的完美狀態,盡管它永遠都不可能實現,但恰恰是這一現實促使人類永無止境地去攀登更高的層次,使人類社會形成了一個完全自覺的能動機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社會區別于原始社會的標志,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文明的本質。人類一旦進入了文明,其歷史便發生了質的飛躍:文明發明期的那些最初挑戰帶來了其后無窮無止的挑戰,人類文明總要在對這些挑戰的應戰和征服中不斷前行。成功的應戰征服了一些挑戰,于是發現自己進入了一片新的未知領域,從而又遇到了新的挑戰。如此往復、生生不息,歷史在螺旋中上升。那種為文明所特有的能動機制就總是以“挑戰一應戰”的模式表現出來,不僅表現在普遍意義的文明中,而且表現在特定文明的彼此關系上,并最終表現在了人類共同文明的征途中。
人類早期的各偉大文明無不是在同環境的艱苦抗爭中毅然奮起:古埃及文明征服了尼羅河三角洲的原始荒蠻,把一片蚊蟲肆虐的沼澤地改造成了歷史上最早的豐饒之地;阿提卡的濱海平原面積有限,山巖裸露,遠沒有內陸彼奧提亞的可耕地那樣可以給人們的農耕帶來豐厚的報償,但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阿提卡的人們卻把自己的商業天才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高度發達的古典時代經濟還使阿提卡成為歐洲政治制度與思想的先驅,到公元前5世紀中葉的時候,雅典就逐步建立起希臘世界最為先進的政治制度“迪莫克拉西”,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政體”,對后世的西方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樣,中華古代文明的興起也與對東亞大河流域自然環境的艱苦改造密不可分。這些都是人類社會在與外在環境“挑戰-應戰”的互動模式中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典型例子。
普遍意義上的人類文明度過最初的發源期,進入蓬勃發展的時代,世界各地許多人類的子文明紛紛興起,彼此互動交相輝映。從這個階段開始,“挑戰-應戰”模式就不僅在人類和外部環境之間存在,而且也在不同的人類子文明之間表現出來,成為文明之間關系的基本模式。如果從人類普遍文明的整體高度看,這一模式促進了不同文明因子的相互交流,客觀上導致了優勝劣汰,在促成交流中析出或是生成了新的普遍文明因素,最終為人類共同文明的誕生發展奠定了基礎。迄今為止的人類各主要文明不論在空間還是時間上都有很大的差異,它們在各自迥然相異的環境中起源成長,克服各自所面臨的自然和社會挑戰;它們各自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就無一例外地都代表著人類的寶貴實踐,體現著人性的頑強適應性和人類高度的主觀創造性,所以,僅從這一點看就都具有同樣重要的普世價值。德國學者森格哈斯認為,許多文明的重要價值實際上都是相通的,他在批判“文明沖突論”時指出:(亨廷頓)顯然低估了西方價值在其他非西方社會中得到的重視,這不是因為它來源自西方,而是因為它具有包括保護個人和個人組合體在內的一些價值取向。在所有非西方社會已經或將要發生的政治與人道的運動中,人們追求的價值取向卻正是產生西方文化的這些價值取向,不管這是否屬于偶然。
隨著文明的深入發展,人類文明的容量越來越大,內涵越來越復雜,各個子文明之間的差異也在不斷加深。不同的事物只要接觸就會相互產生影響;同理,人類不同文明只要交流就會表現出“挑戰一應戰”模式。在文明的分類上,湯因比雖然把人類文明分成了30多個子文明,而且有一些文明從地理分布上來看關系非常密切,比如說古典時代的
希臘-羅馬文明分布于以歐洲中南部為主體的地中海北岸及部分東岸地區,而在其后的西方文明與東正教文明在地理分布上基本和希臘-羅馬文明一致并稍有擴大,但它們卻是不同的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對其后的這兩個姊妹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之間的關系依然符合“挑戰-應戰”模式。當然這是一個明顯的道理,不管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古文明其獨有的內核已經有多少被后世的人們所遺忘或拋棄了,但它終歸要對后來的社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今天總是建立在昨天的基礎之上。湯因比把文明之間的接觸分為時間和空間上兩種:一種是同代文明在空間上的接觸;另一種是不同文明在時間上的接觸。在湯因比看來,這兩種接觸不管是在時間還是空間上,用“挑戰-應戰”模式都可以很好地加以解釋。研究歷史上的文明如何影響今天是非常重要的。關于這方面的互動情況,可以說既往文明對現存文明的“挑戰”和后續文明的“應戰”,湯因比分別從制度、法律和哲學,語言、文學和視覺藝術,以及宗教意識形態等三個方面作了深入探討。他認為,雖然后來文明可以從既往文明的偉大遺產中吸取相當多的智慧與靈感,但新生文明自己的生機活力和開創精神顯然更加重要。所以,一個新的文明可以從逝去的文明那里有所借鑒,但它自身必須具備創造的主體性和決定權,否則就只會成為逝去文明的奴隸而亦步亦趨,并最終陷入到一種非理性的對偶像的崇拜之中,接著就是不可避免地衰落甚至是消亡。
不同歷史時期文明之間的接觸對于后來文明的影響、改造甚至于決定它的命運都可能發揮關鍵性的作用。雖然這兩個單位之間的聯系可以用“挑戰-應戰”的模式加以說明,但更多只是表現在了后世文明對于先前文明挑戰的單方面應戰上面。同時代文明之間的接觸也符合“挑戰-應戰”模式,而且由于它們都是現存的,都有主體能動性,所以它們之間的接觸所產生的影響就不是單向的,兩個互動的文明都會既向對方施加影響,同時也會對自己受到的影響加以適應,能動地改造自己。因此,從這方面來說,同時代文明相互間的接觸可以更好、更全面地展示“挑戰-應戰”模式的深刻內涵。由此可見,“挑戰-應戰”模式在人類文明史中自始至終發揮著重大作用,對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也必然產生深刻的影響。
二、“挑戰-應戰”模式對全球化時代文明與國家間關系的價值
湯因比提出“挑戰-應戰”模式的時候,正值人類社會處于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一方面是二戰結束后,西方發達國家正經歷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時期,另一方面,非西方國家正在紛紛贏得民族獨立和解放,掀開了自己歷史新的一頁;從二戰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來看,這是美蘇冷戰由發軔走向高潮,然后再向緩和逐漸轉變的時期,超級大國之間令人不寒而栗的核恐怖均勢時時威脅著整個人類的生存。作為冷戰時代的見證人之一,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情緒也深深地反映在湯因比的作品當中,僅在《歷史研究》一書中就有至少七八處。作者向當時的人們嚴肅指出了美蘇對抗可能給世界帶來的滅頂之災,并且強烈呼吁和平與人類的和諧共處。
當然,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二戰后的幾十年,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全球化開始啟動并加速向前發展。在世界范圍內,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明格局都真正多元化了,這是因為“1945年以后,非西方強國自1683年以來第一次重新開始在強權政治舞臺上成為重要角色,而且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而是根據自己的意愿。過去大約250年間,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只有現代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天然成員或皈依者彼此爭執不休。現在,由于恢復了正常狀態,文明和文化沖突也就重新進入了國際政治舞臺”。隨著處于西方文明陣營之外的日本、蘇聯和中國先后崛起,東南亞、印度和非洲的非西方社會也開始重申他們獨立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如果再加上伊斯蘭世界核心地區的民族國家,“我們就會更清楚的看到,1945年以后國際關系的重新組合已經提出了一個已經被擱置了250年的文明之間的接觸問題”。
由此可見,雖然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開始于大致與歐洲近代同時開端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但300多年來,由于西方文明對其他人類社會所擁有的巨大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優勢,除了少數的非西方參加者以外(他們包括已近末期的中華帝國,莫臥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等,而且在和西方列強的外交接觸中,這些帝國總是處于下風),其他地區的人類社會基本上都處于被西方支配的地位。“到1914時,歐洲諸強國已并吞整個非洲,并有效地建立了對亞洲的控制;這種控制或是直接的,如在印度和東南亞,或是間接的,如在中國和奧斯曼帝國。歐洲之所以能進行這種前所未有的擴張,是因為三大革命——科學、工業和政治革命——給了歐洲以不可阻擋的推動力和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關系嚴格地說也就是西方文明內部的事情,是歐美強國之間的分分合合而已,其他文明根本沒有和西方文明平等對話的現實可能性。如上所述,西方文明由于經歷了兩次大戰的沖擊,一枝獨秀的局面已經被打破,加上非西方文明強國的再次崛起,使得全球性的文明對話真正有了基礎。
在近現代西方與非西方文明和國家接觸的例子中,由于擁有顯而易見的物質力量方面的優勢,西方文明占有主動地位,從而或多或少地給包括俄國、中國和日本在內的幾乎所有非西方文明都施加了自己的影響,打上了西方的烙印。盡管主動利用或是被迫接受西方的影響有大有小,在文明及國家的相互接觸、“挑戰-應戰”模式中自我改變的程度有深有淺,結局多種多樣,但不論俄國、中國還是日本,都沒有在與西方的接觸中完全離開自己傳統文明的深厚積淀。然而毫無疑問,自從西方因素在這些文明中出現以后,它們的面貌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而西方呢,同樣無法擺脫“挑戰-應戰”模式雙向影響的規律,在一個物質和精神條件都史無前例的全球化時代.任何施加對外影響的文明也必須接受對方的影響;挑戰、應戰是一體兩面,彼此無法分割,而且往往是同時進行。杜維明在談到儒家倫理的現實價值時認為:“按當代人的觀點,當我們承認西歐和北美所作出的示范性現代化事業已成為人類共同遺產時,我們不應無視這種啟蒙工程中固有的嚴重矛盾和體現在現代西方國家進程中的破壞性因素。”現當代西方技術文明所產生的諸種弊端很難僅在這種文明的內部加以解決,吸取綜合其他文明因素的優點才有可能解決某些重要問題。
非西方的某些偉大文明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并創造了卓越的成就自然反映了它們的內在生機與活力,自有這種文明存在發展的合理邏輯在支撐。但反過來說,非西方文明在近代同西方文明接觸中的物質劣勢地位又恰恰是他們的某些致命弱點,而這一點正好是西方的優勢。西方文明的活力第一次真正地把全球都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經過幾代人、幾個世紀的時間,統一的世界逐漸跨上了通向不同成分的文化之間相互平衡的道路,西方的成分將逐漸地降到適度的地位,這就是有待于由
其內在價值與其他文化比較所能保存下來的全部東西——現存的與已消失的,正是由于西方社會的擴張,才使那些文化相互聯系起來”。
在公認的世界歷史全球化時代,第一次真正出現了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的全球性分布(雖然并不是平均分布),各主要文明和國家或多或少都擁有了一定的發言權,文明之間“挑戰-應戰”式的互動不僅會深刻地改變現存的傳統文明,而且還會對未來人類共同文明的構建產生深遠的影響。幾個世紀以來由西方文明和國家支配的、長期的單向文化和政治交流結束了,最終將使得一個民族、文化和國家更愿意承認和接受其他不同文化,并逐步把圍繞著一系列共同價值觀的合作當作是一種盡可能的、必要的需求,其他文明和西方文明平等對話的現實可能性已經存在,一種全球共同文明終將逐漸浮出水面。然而,目前這種人類統一的文明還遠沒有把自己的所有重要特征清晰地展現出來,這有賴于人類生產力的繼續提高,有賴于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和擴展。而且,統一性完全不同于一致性,它不是基于消除各種差別,而是基于使這些差別在一個和諧的整體中整合。自然界證明了這種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沒有整合就不可能有最深遠意義上的生長、進化和發展。人類需要多樣性,而且需要統一性。因此,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也必然要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之間的對話中探討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也只有在尊重各國差異和多樣性的文化的基礎上尋求世界各文明和國家間關系的和諧發展。
三、結語
盡管全新的人類共同文明的輪廓依然模糊不清,但是,“挑戰-應戰”模式在人類創造文明和塑造國家間關系的古老歷史中始終發揮關鍵作用的機制又開始在新的歷史變量中開始自己的精彩演繹。全球化時代充滿了新的“挑戰”,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面臨著許多困擾他們的共同困難和威脅,自然環境、疾病天災、恐怖主義、經濟金融安全等問題早已不把單個國家甚至個體文明當成對手,這些挑戰正在逐漸超越原有的傳統問題,上升到了史無前例的全球層面,要求整個人類前來“應戰”!因此,“挑戰-應戰”模式將始終與人類的歷史相伴隨,人類只有把自己相應地提高到應有的層次才能夠有效地面對它。全球化時代即是這樣一個挑戰,同時全球化也是應戰的唯一途徑。“挑戰-應戰”模式之所以有生命力而長盛不衰,就在于它本質上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類歷史在宇宙中存在的方式,即文明本身。由此,它不僅推動了完整意義上的全球化向前發展,而且反過來,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關系也必然要求人們在文明的深度和廣度上探討彼此間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