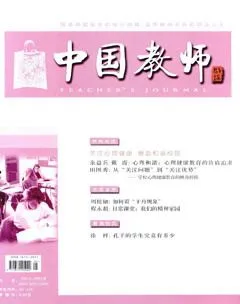徘徊在城市邊緣的民工子弟學校教師
我國現有流動人口1.2億,其中民工占大部分,以學齡兒童少年占2%~3%計算,流動民工的學齡兒童少年就有240萬~360萬。[1]目前,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絕大部分流動人口子女只能在民工子弟學校上學,這類學校在城市中扎根生長,受到各方面的關注的視線。但是目前大部分關注的視線都集中在學校和學生這兩個主體,而忽視了民工子弟學校中的另一個根本性的存在——教師。那些在只能用“貧瘠”兩字來形容惡劣的教學環境下仍然誨人不倦的教師,那些相信著來城市便能改變自己命運但卻不能立馬叩開城市的大門暫且只能在這樣的學校中“借屋躲雨”徘徊在城市邊緣的教師,掉落在了人們談論教育公平問題的話語結構之外。讓我們在這篇短文中,盡量地向他們的生活世界靠近一些。
教師來源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一般具有城市外來人口的身份,又一心想成為城里人的特點。對這一群體仔細再做劃分,還有以下幾類,一是作為學校創辦人的外地教師,二是外地公辦教師,三是擔任過農村民辦及代課的教師,四是地方師范學校畢業后未分配的應屆師范生。
作為學校創辦人的教師,一般都是在自己的家鄉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老教師,敏銳地意識到城市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市場的巨大潛力,在城里辦起了民工子弟學校。應該說,這部分人是民工子弟學校教師隊伍中的精英,不僅獲得了較高的社會聲望,為民工子女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而且也獲得了較高的經濟收入。民工子弟學校作為民辦學校,具有營利性質,通過不斷擴大生源,創辦連鎖分校,增加學校收入,這也就等于增加了創辦人的收入。
外地公辦教師大多是因為經濟原因而流入城市,加入了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隊伍。這部分教師主要來自貧困地區,他們在家鄉的收入無法保證家庭的開支,而城市的民工子弟學校,則為他們提供了比家鄉好得多的經濟保障。
擔任過農村民辦及代課的教師,由于無法轉正及工資太低而到城市尋求新的發展機遇。由于民工子弟學校師資力量的匱乏,這一部分教師也被吸收了進來,成為外來教師隊伍的成員。
而地方師范學校畢業后未分配的應屆師范生,一般都有高中或中專學歷,高的有大專及大學本科學歷,[2]構成了民工子弟學校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高校擴招,每年都有大量的師范畢業生面臨著就業壓力,而公辦學校教師市場的飽和甚至是過飽和,使得應屆師范生進入公辦學校的門檻很高,只能選擇民工子弟學校作為過渡的跳板,希望有一天能夠進入城市的公辦學校工作,或者等待家鄉學校入編的機會。
工作狀況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雖然和公辦學校教師一樣,頂著“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神圣光環,但其工作條件卻與后者無法相提并論。學校硬件設施貧乏,僅能滿足基本教學需求,教師的辦公條件也十分簡陋,只能在擁擠的辦公室備課、批改學生作業。雖然就地理位置上講,他們身處現代化的城市,但卻缺乏學習先進的、現代化教育理念的條件,無力提升自身的素質。在城市公辦學校已經普及的多媒體教學條件,對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來說,是那樣的遙不可及。學校很少提供給教師電腦、網絡等輔助的教學器材,他們僅僅是將傳統農村教育模式在城市邊緣進行延續而已。
隨著越來越多的民工子弟學校在城市邊緣立足,彼此之間生源爭奪也日趨激烈,師資的水平以及教學質量的高低也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民工子弟學校招徠學生的一個很重要的牌子。與民工子弟學校發展初期存在較多門外漢充當教師角色的現象相比,目前民工子弟學校在招聘教師時,設置的門檻已經增高了很多。首先,為保證教師隊伍的專業化水準,應聘教師須有教師資格證;其次,學校對教師的教學工作每學期都有考核,末達標者則走人。以上兩條,成為了保證學校教師質量,獲得家長學生認可,從而擴大學校生源的主要手段。
然而與城市公辦學校相比,民工子弟學校的師資力量依然薄弱,且學校為了節省開支,教師常常不得不身兼數職,承擔巨大的工作量,每天過著超負荷的日子。許多教師除了要教語、英、數的主課,還要兼任體育、音樂等副課的教學。工作的繁重超乎常人的想象,教師疲于上課改作業,無力顧及教學質量。
流動性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工作量遠遠超過公辦學校教師,但工資卻比后者少了許多。由于工資較低(南京外來教師大約每月600元),生活艱苦,教學負擔繁重,工作壓力巨大,教師間競爭激烈,部分校長不尊重教師,部分城市教師歧視外來教師,因此只要能找到更好的出路,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就經常跳槽。而學校間互“挖墻角”的現象,也增大了教師的流動性。有學者對外來教師的流動性作過調查,在69個班級中,發現每學期中途更換教師的情況,比例高達47.8%。最極端的一個班級,甚至創下了一學期更換7名教師的記錄。[3]
外來教師流動性大,轉行做其他工作的也很多,能夠留下來的,多半不是為了錢,而是出于一種對民工子弟教育的責任感。在筆者做的訪談中,一些教師表示自己是憑著一顆良心在教學,良心帶來了責任感,良心帶來了奉獻精神,因為農民工的孩子實在太可憐。然而筆者也注意到,將之稱作為“良心”也好,稱作為“同情心”也好,感情上心理上的羈絆并非穩定流動性的堅固的保證。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還要生活,還有家庭要照顧,也還要很現實地考慮工資待遇。盡管公辦學校的門檻很高,盡管邁進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盡管即便進去了工作壓力依然很大(當然,可能是別樣的一種工作壓力),但一有機會就想往公辦學校(即便可能只是郊區的公辦學校)轉的念頭,已經變成為了一種揮之不去的、正因為難以實現就更渴望實現更向往實現的心理情結。
自我預期和群體認同
民工子弟學校教育處在基礎教育的邊緣,而這種教育的邊緣化又導致了教師地位邊緣化。他們的自我預期較低。對于部分民工子弟學校的創辦人來說,經濟動機壓倒了教育的要求,利潤是第一位的。面對龐大的教師就業市場,他們占據了主動地位,可以用較低的工資雇用教師。所以有的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認為,自己在民工子弟學校當教師也不過是打工而已,與從事體力勞動的打工者不同,他們是從事腦力勞動的打工者。
在城市,民工子弟學校的外來教師遭受到兩方面的歧視:一是外在的制度歧視,即由于戶籍制度、教師編制的限制,他們無法進入所在城市的公辦學校。有被訪者說現在進入公辦學校很難,“因為學校很黑暗,要有關系才能進去”。另一方面是內在的精神歧視,由于“不是城里人,而是農村來的”,他們很少能有機會與城市公辦學校的教師互相學習、交流教學經驗。
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的交往圈子很小,與外界接觸很少,處于“原始時代”,更像是熟人社會中的人際交往關系,交往集中在同學朋友老鄉的圈內。有的外來教師反映,由于工作繁忙,加上租住地的治安不良,很少出門,對城市不熟悉,每天基本上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正是受到這種社會交往網絡的限制,民工子弟學校的教師形成了自己的群體認同感,認為大家都是外來教師,在民工子弟學校教書,相互之間頻繁的日常生活互動(所有教師共用一個辦公室)使得彼此有較多的共同語言,人際關系融洽,在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顧。民工子弟學校里只有學生和教師兩種角色,不存在職務上、工作上的競爭關系,不像公辦學校,為了評職稱等種種利益問題,教師之間經常勾心斗角,人際關系緊張,因此,有較融洽的人際關系,也很值得欣慰。
教師從家鄉走了出來,希望有機會融入城市。但是城鄉間的文化差異,城市中的制度排斥和社會歧視,造成了他們生活上、心理上的不適應,使他們徘徊在城市的邊緣。在這種殘酷的現實下,很多被訪的教師都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茫和無奈。然而迫于生計,他們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態,繼續在民工子弟學校從事高強度的教學工作。雖然前途渺茫,但他們不少人仍對教育制度的改革持樂觀態度,期望著方方面面能夠多關注到他們這一特殊的社會弱勢群體,為他們能夠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條件和可能性。
注釋:
[1]王滌,等,中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調查與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2] [3]辛苦了!民辦小學教師[EB/OL].http://www.xjbs.com.cn/cgi-bin/GInfo.dll?DispInfo&w=xjbs&nid=18173.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社會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