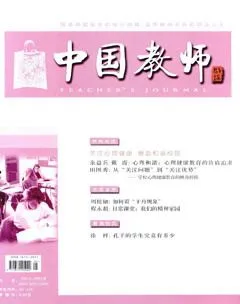有一種愛不能直白
每學期學校都要拿出一筆錢來,對一些家庭貧困的學生進行救助。少則一二百元,多則五六百元,雖然只是杯水車薪,但也足夠那些家庭有困難的學生維持一兩個月的生活費開支了。我在班上做了宣傳,奇怪的是到了截止日期,竟沒有一個同學交來求助申請。是班上沒有貧困生嗎?完全不是。我知道班上至少有一名叫娟子的小女孩肯定符合救助標準的。
小女孩年幼喪母,父親又下崗,僅靠父親在外打工維持她上學和生活。每學期開學時的書本費,常常要拖兩三個月才能湊齊交來。她這學期的校服錢還是我幫墊付的,她要我放心,說這個月底、最遲下個月,父親就會把錢送來,到時肯定會還我的。我把她找來辦公室,詢問為什么不寫申請?原來她擔心拿了學校的救濟款后,會被其他同學瞧不起。我向她承諾,可以讓學校不在櫥窗里公布姓名。她依然搖頭不肯,說只要拿了學校的錢,即使同學們都不知道,但心里總感覺自己好像比別人低了一頭似的。
小女孩倔犟的性格,讓我有些感動。我沉默無語。但依然希望她不要放棄這個難得的機會,因為我知道她實在太需要幫助了。后來,我想了個巧妙的變通辦法,并征得學校的同意,我請小女孩的父親來學校,讓他替女兒寫了申請,并領取了500元的救助金。這個場景,在我擔任小女孩班主任的兩年四個學期里,共出現過四次。每次我都和小女孩的父親約定,永遠也不要讓孩子知道這件事。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大學校園里。據《中國改革報》報道,在中國科技大學,一個學生要是在校內食堂每月用餐60次以上,消費總額在150元以下,也就是說每餐消費不滿2.5元,這個學生就會引起校方的注意。校方會主動調閱該名學生的檔案,通過與學生家鄉的政府民政部門或街道居委會聯系,在核實情況之后,無須學生申請,且在學生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就會有每月160元或者100元的補助,自動進入這位學生的“校園一卡通”賬戶。通過這種“隱形資助”的形式,中國科技大學在3年的時間里為3600多人次貧困生累計發放的補助款近64萬元。
相同的例子在國外也屢有發生。美國紐約的公立小學從來不會因大雪封門而宣布停課,即使積雪已經讓整座城市的交通陷于癱瘓,所有的工廠和私立學校都放假了,它也不會。學校的校車依然要把所有的孩子接到學校上課。學校這樣做的理由是:在紐約雖然有不少百萬富翁,但貧窮的家庭也很多。這些家庭白天沒有暖氣,甚至連孩子的午餐也沒有能力提供,孩子成長所需的營養全靠公立學校供應的免費午餐。有的孩子還會省下免費午餐的一部分拿回家當作晚餐。如果學校停課一天,也就意味著這些窮孩子可能就會一天吃不上飯,還要在家挨一天的凍。
為什么不給其他孩子放假,而只讓這些吃不上飯的孩子到學校上課呢?學校的回答更加令人感動:我們不想讓那些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救濟的對象。
對于身處困境、需要幫助的弱者,尤其是孩子,我們的關愛要格外地小心。他們的心是脆弱的、自卑的,同時又是矛盾的。他們渴望得到關愛,但他們又不愿意接受比別的孩子更特殊的愛。在他們敏感的心中,任何的與眾不同,哪怕是一點點特殊的優惠和照顧,都會被他們誤解成是一種憐憫,一種可憐,甚至是一種施舍,并把接受這種救助,當成是人生的一種恥辱,感覺在人前抬不起頭來。這不但不能給他們帶來一點幸福和溫暖,反而會讓他們產生更大的自卑,給他們要強自尊的心靈造成更大的傷害與扭曲。我們的一片愛心付之東流不說,可能還要收到事與愿違、完全相反的結果。
因此,有的學校在分派有限的資助款時,校方為了顯示自己的公平公正,常常會在學生大會上公開宣讀或張榜公布接受救助學生的名字;有些班主任甚至用評先進時才采用的舉手表決的方式,讓全班學生推舉出班上最貧困最需要救助的學生名單;還有些大型企業、公司和單位,為了向全社會彰顯自己的愛心,不惜讓貧困的孩子在大眾媒體前亮相,在眾目睽睽之下登臺,然后低著羞愧的頭從董事長、總經理或政府領導的手中接過捐助——這些本來并無惡意的種種做法,其實都是不妥當的、不可取的,甚至是粗暴的、野蠻的、殘忍的。面對深陷貧困而又自卑的孩子們,我們在奉獻更多的關懷和愛心之時,還需要開動一下腦筋,講究一點智慧,注意一下方式方法,從而使我們的關愛,能夠不露一點痕跡地傳遞給他們,就像綿綿春雨,滋潤萬物而無聲,就像博大母愛,無處不在卻無痕。從而讓這些貧困中的孩子,能夠像其他孩子一樣正常地成長,讓他們幼小的心靈充滿愛的陽光,而不留下一點陰影。
有一種愛,需要隱藏,不能直白;
有一種愛,需要智慧,不能草率;
無痕的愛,才是人世間的至愛;
無痕的愛,才是愛的最高境界。
(作者單位:江蘇省儀征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