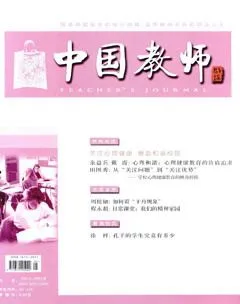孔子的學(xué)生究竟有多少
當(dāng)被問到孔子有多少學(xué)生時,幾乎所有的人都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確,這樣的說法曾見諸正史的記載,而且出自“不虛美,不隱惡”、嚴(yán)謹(jǐn)審慎、文直事核的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話一出,后世幾乎沒有什么疑義,一直承繼因襲,眾口一詞。
1978年10月28日,我國著名文獻(xiàn)學(xué)家、華中師范學(xué)院張舜徽教授在曲阜師范學(xué)院發(fā)表了《如何重新評價孔子》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他對“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之說提出了質(zhì)疑。在他看來,在孔子的時代,無論是交通還是居住條件,都不允許會集幾千人,在一家私人講學(xué)之地讀書;即便不是在一時一地會集,而是先后陸續(xù)參加,也絕對不可能。所以在《仲尼弟子列傳》中,有傳記的不過35人,加上僅列名字的42人,也不過77人。張先生從舊史記載、師生年齡差別、交通和居住條件,尤其是古書的通例多方面考察后得出結(jié)論:“可以肯定‘三千弟子’的傳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夸大數(shù)字。”
張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但這里并不是司馬遷記載的錯誤,而是后人的誤讀。這種誤讀,是不了解古書的通例,特別是不了解古人記數(shù)往往使用虛數(shù)這一慣例造成的。
清朝乾隆年間著名學(xué)者汪中,曾撰寫有《釋三九》一文。清末民初學(xué)者劉師培,在汪中研究的基礎(chǔ)上更進(jìn)一步,寫出了《古籍多虛數(shù)說》。根據(jù)這些研究成果,我們可以了解古人計數(shù)的規(guī)律,從而對“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之說,有一個正確的理解。
古人對于特別繁多的人或事,最常用的辦法是“約之以百”,比如說百工、百物、百貨、百谷,乃至百姓。如果這樣還不足以形容其多,則往往用三百或三千來表示。比如《禮運》說“經(jīng)禮三百,曲禮三千”,《中庸》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史記》說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人”,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呂不韋“至食客三千人”;唐代白居易的《長恨歌》則有“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之說。這里所謂的三千,只是用來表示數(shù)目之多,并不一定限于三千之?dāng)?shù),也不一定足于三千之?dāng)?shù)。孔子“弟子三千”,也是如此,這時是不能拘泥于文字,把虛數(shù)當(dāng)作實指的。
三百、三千的整數(shù)不難理解,這與我們現(xiàn)在“成百上千”的說法相同。古人在表示數(shù)目時,還有一種做法,就是“凡一二之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多。”(《釋三九》)比如《左傳》中的“三折肱知為良醫(yī)”,《論語》15RKe26OTZMT07eitBiE3A==中的“三思而后行”和“吾日三省吾身”,《楚辭》中的“雖九死其猶未悔”,《史記》中的“若九牛之亡一毛”、“腸一日而九回”,《孫子兵法》中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等等。這里的三、九都是言語間的虛數(shù),是不能把它們當(dāng)做實指而信從的。這就如同《楚辭》中的《九歌》,雖然一共有十一篇,但在標(biāo)題的時候,還是署以“九”,不過是表明眾多的意思罷了。歷史文獻(xiàn)中的“九攻”、“九守”、“九變”、“九天”等,都是如此。
古人不僅用三、九,而且還用三和九的倍數(shù),特別是三十六、七十二和一百零八,來表示數(shù)目之多。如《莊子.天運》稱孔子對老聃說自己以六藝“奸者七十二君”。《史記.封禪書》引用管仲的話說:“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說“神農(nóng)管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后世民間還有皇帝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孫悟空有七十二變等等說法,都是因此而來。
明白了這一通例,我們就會知道,雖然孔子的學(xué)生很多,但并不意味著真有三千之眾。“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之說,不過是說孔子弟子眾多,有成就的也不少。如果我們將這樣的說法具體化,認(rèn)為三千或七十二,一個不多,也一個不少,并費盡心機(jī)地去做所謂的考證,那就難免膠柱鼓瑟之病。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