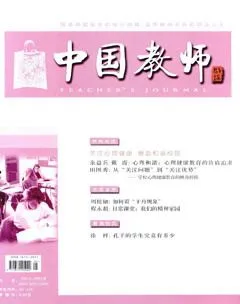諸子簡介·韓非子篇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年),是韓國的貴族,是法家的集大成者。
講到法家,不能不提到法家思想的先驅,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管仲(齊)、子產(鄭)和戰國時期的李悝(魏)、吳起(衛)等,但真正使法治理論走向完善和將以法治國用于實踐的是商鞅、韓非、李斯等。因而法家中有“管商之法”、“商韓學派”之稱。
韓非,口訥,不善言談,卻善于為文。在他之前有商鞅重法,即重視法制條款的厘定,主張以嚴刑杜絕犯罪;申不害重術,強調君王要有駕馭臣民的手段和策略;慎到重勢,強調提高君王的權力和地位是執法的必不可少的手段。韓非吸取了上述三人的成果,檢討了三人的偏頗,將法、術、勢統一起來,建立起以法為核心的抱法、處勢和行術統一的完整法學理論,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以此維系和鞏固帝王的權威和統治,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
韓非曾多次上書韓王,要求變法,但不見用。他對韓王不務修明,造成“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的局面,極為不滿,“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其所著述為秦王政(即后來的秦始皇)所見,大加賞識。韓王安五年(前234年),韓非為韓王出使至秦,即為秦所重用。韓非和李斯都曾師從荀子,李斯自以為不如韓非,便與趙賈向秦王屢進讒言,使其下獄,后又被迫服毒自殺。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嘆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也就是說,他能寫出《說難》,卻不能用其解脫自身的危難。
韓非所處之世,周室衰微,禮崩樂壞,戰亂頻仍,僭越成風,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亦有之。儒家的仁義禮樂,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歸真返樸,都不可挽救時弊,為世所用,只有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厲行賞罰,獎勵耕戰,才能富國強兵,實行統一,這就是法家行時的社會基礎。
韓非在哲學思想上,繼承了荀子的唯物論,并把人性惡作為實行法治的理論根據,完成了他的法、術、勢統一的法學專著,為秦統一六國,建立起君王具有無上權威的中央集權制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強調“緣道理以從事”,反對“無緣而妄意度”;并提出“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等,這些都是唯物的科學處事的理論和方法。
韓非在社會觀上也是比較進步的,他將社會發展分為上古、中古、近古和當今幾個階段,認為歷史是在不斷變化和前進的,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的社會歷史發展觀和社會變革論,這些思想都為后世的社會改革家所采用。法家的思想,雖在秦亡之后,幾乎處于被遺棄的境遇。但后世的改革家,又常是外儒內法或儒法并用。看來,法家思想利于改革,而儒家思想則利于守成。王安石在變法中,就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來否定儒家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證明。
《韓非子》一書,不僅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而且還有不朽的文學價值。學識淵博,文風犀利,辯論透辟,而且善于運用比喻。其中所包含的歷史故事和寓言故事,在先秦文學中堪稱首位,如大家所熟悉的“自相矛盾”、“守株待兔”、“鄭人買履”、“買櫝還珠”、“老馬識途”、“濫竽充數”,等等,都出自《韓非子》一書。我們可以這樣說,寓言故事以先秦為最多,而《韓非子》尤居第一。因而要學習中國古典文化,《韓非子》是一本不可不讀的典籍。
《韓非子》一書,共55篇,為后人編輯,其中少數篇章疑為后人所作,但大多數出自韓非之手,而且是先秦文獻中竄亂較少的典籍。注釋有清王先慎的《韓非子集解》,近人梁啟雄的《韓子淺解》,陳奇猷的《韓非子集釋》,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和《韓非子的批判》,都可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