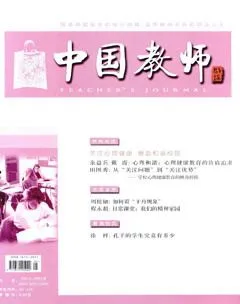漢字起源的文化解讀
相傳上古時期,人們以結繩記事。用大繩結表示10、小繩結表示1的辦法在部落中通行。直到甲骨文中,還保留著這種結繩記事方法的痕跡。甲骨文的數目字“十”寫作 ,像一個繩結的樣子;數目字“二十”寫作
,像一個繩結的樣子;數目字“二十”寫作 (即后來的“廿”,音niàn),像兩個繩結的樣子;數目字“三十”寫作
(即后來的“廿”,音niàn),像兩個繩結的樣子;數目字“三十”寫作 (即后來的“卅”,音sà),像三個繩結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人們很早就將漢字起源與結繩聯系起來。《周易.系辭下》即已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東漢的許慎在講漢字產生前的情形時,也提到了結繩:“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為萌生。”近人朱宗萊更是肯定地說:“文字之作,肇始結繩。”這就是關于漢字起源的重要傳說之一——結繩說。
(即后來的“卅”,音sà),像三個繩結的樣子。正因為如此,人們很早就將漢字起源與結繩聯系起來。《周易.系辭下》即已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東漢的許慎在講漢字產生前的情形時,也提到了結繩:“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為萌生。”近人朱宗萊更是肯定地說:“文字之作,肇始結繩。”這就是關于漢字起源的重要傳說之一——結繩說。
其實,結繩只是一種原始的記事方法。這種方法在我國古代確曾使用過。《莊子.篋篇》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根據這個說法,上古曾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用結繩記事,而神農氏則是使用結繩的最后時代。至于結繩這種記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義》引《虞鄭九家易》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據說,我國怒族解放前仍使用結繩記事,其方法正與此相同。在大部分地區,結繩主要是用于記數。因為在原始社會時期,隨著生產的逐漸發展,人們對數量的記錄和計算產生了迫切的需求,收獲的谷物、獵取的禽獸需要計算,區域的大小、路途的遠近需要標記,甚至歲月時日、生活瑣事也都需要用數字來記錄。于是,他們逐漸探求能夠幫助記數的各種方式,結繩便是其中的一種,這樣,繩結便和數量建立了聯系。
至于有人根據甲骨文“十”、“廿”、“卅”三個數目字的形體很像打結的繩子,認為它們來源于原始的結繩記事法,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之前,我們不能斷然肯定此說純屬虛妄,畢竟在結繩記事中單結的確可以表示10。但即使這種推測能夠成立,極個別的漢字采用結繩形象作為構字符號,也只能說明結繩記事法對漢字的產生有一定影響,而不能由此得出漢字起源于結繩的結論。這正如“目”、“口”等字采用人體器官的形象作為構字符號,而我們卻不能說漢字起源于人體器官,其道理是一樣的。結繩僅僅是一種幫助記憶的實物性記號,不可能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人們之所以把結繩與文字聯系在一起,是因為人類創造結繩記事的方法與發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一件事情要想存儲在腦子里,只有在記憶能力所能達到的時間和準確度之內,才是可能的。但人類記憶的延續時間和可負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外部標志的提示作用,才可能使這些限度有所提高。這種對記憶超越時間限止的需求,正是激發人類發明文字的動因。
可以說,在原始人利用結繩來幫助延長記憶時間的時代,文字產生的主觀要求就已經具備了。原始社會的人群活動范圍還不很大,對記事符號的交際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語言的時間限制比突破空間限制更迫切一些,在這種特定的時代,結繩這種低級的記事符號確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雖然繩結的可區別性很低,其記事的數量和明確性都十分有限,但它畢竟是人類在使用符號方面的一次成功嘗試。隨著社會的日益發展,社會事務越來越繁雜,簡單的結繩再也滿足不了管理社會的需求了。于是,另一種全新的符號體系——文字,開始孕育而生。從結繩到文字,雖然不存在直接的淵源關系,但在用符號幫助記憶的思路上卻是相似的。因此,結繩說雖然不能揭示漢字的真正起源,但其中確實隱含著一些合理的成分。
關于漢字起源的另一個重要傳說是“倉頡造字說”。這種傳說戰國時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