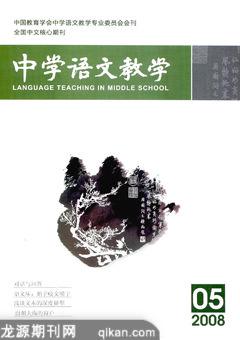于細微處品咂
唐江澎
一次上公開課,講一百四五十個字的短文《與朱元思書》。盡管這是上中學時就背得出又教過許多次的“老熟人”,備課時我還是字字讀來,細細觸摸,在下面幾個細微處品咂出了新味。
“風煙俱凈,天山共色”二句。正是秋高氣爽時節,說是寫得雄壯大氣。但何謂“風煙”?既有“俱”字,是寫“風”“煙”兩景,還是一景?何謂“煙”?是“茅舍無煙”的裊裊炊煙,還是“煙籠寒水”的濛濛霧氣?學生有什么樣的知識儲備可以用來理解“風煙”這一典型的文化意象?“風煙”在古典文學的意象中,一是指“烽煙”,是“萬里絕風煙”的戰訊;一是指“風塵”,是“風煙望五津”的揚塵,即所謂風起塵揚,天地渾濁,而“風塵”多以喻世俗之擾攘、仕宦之混濁。聯系作者的經歷,自應取后者之義。他脫離官場而來,眼見得這一派絕塵除霧的晴空,怎不覺心凈氣清,精神舒展!風定塵絕,霧氣散盡,天地澄澈,好個干凈!是寫眼中景,也是寫心中境,這與下文“鳶飛戾天者”“經綸世務者”來此勝境的“息心”“往返”遙相呼應,正所謂以己度人。正是在這樣的“風煙俱凈”中,作者極目望去,才有了遠山與天際相接、天山一色的境界。這樣品來,體會了作者游目騁懷的感受,也領略了開篇大氣包舉、曠達宏闊的氣象。
“自富陽至桐廬”,或解為點明游蹤。有資料認為富陽在富春江下游,而桐廬在上游,以“自……至……”形式相連,表明作者行舟路線是溯流而上。但前文明明有“從流漂蕩、任意東西”的句子,究竟是“從流”還是“溯流”?探討這個問題,不要讓學生陷入學理分析,而應從字面上讀出作者游歷奇山異水時的精神狀態。我的看法是,“自富陽至桐廬”點明的只是“一百許里”之間的地段,并沒有標出舟行路線,而作者的游歷采用的是放舟水上,“從流漂蕩、任意東西”的方式。這種獨特的隨任方式正與作者自由解脫、舒展陶醉的精神狀態相合!甚至可以想象作者所乘該是什么樣的舟船,在船上他是怎樣的姿態。這些無定論的問題,也可從旁幫助學生深入文本。他不應乘畫舫而來,載他的應是一葉扁舟、一筏木排;他不應危坐船頭,應是開懷散臥,一任奇山異水入目來。
不只是文意的悟讀,字詞的玩味也能品得妙處來。“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妙在何處?自然是“奔”字用得好。為什么好?動詞活用為名詞;如果用了名詞,比如改為“猛浪若馬”便不好。但,動詞用作名詞便一定好嗎?既然如此,為什么不將“急湍甚箭”改成“急湍甚飛”呢?看來不是名詞或動詞的事。實際上,用“箭”字讀者眼前會有一箭飛逝的畫面,“飛”字則比較虛空;用“奔”字也可使人見得群馬奔騰。文字表現的妙處,在于選用的語詞可以設造畫面,使內容有形有象,靈動可感,栩栩如生,這就是形象生動的魅力。這樣說來,“水皆縹碧”的“縹碧”只是解為“青綠色”是否意味不足,太過直白?且不說作者當初調遣語詞時的筆意,單以讀者閱讀獲取的形象而言,“碧”字難道就沒有以“碧玉”狀寫秋水的質感嗎?還有,“夾岸高山,皆生寒樹”一定是山上長著“耐寒常綠的樹”嗎?我無意討論教材的注釋,只是說明解詞與品味語詞妙處不全是一回事,教學的任務不是要讓學生記憶詞義,咂摸玩味可能使學生有更好的語感與斟酌詞句的悟性。
無論是多么熟悉的文本,備課總應找尋一種陌生的感覺,向無疑處生疑,以期獲得新的發現,或者獨到的感受。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在《人的使命》中說過一段話,“凡我所見到的,我都親手觸摸過,凡我所觸摸到的,我都分析過;我曾多次重復我的觀察,我也相互比較過各種現象;只有在我能從一種現象解釋或推斷另一種現象以后,我才心安理得”。費希特顯然不是在講教學問題,但非常適用于論說備課的狀態,對眼見的文本,要親手觸摸,要深入分析,要反復觀察、比較,然后去解釋、推斷,這樣才可以達到“心安理得”的境地。
(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 214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