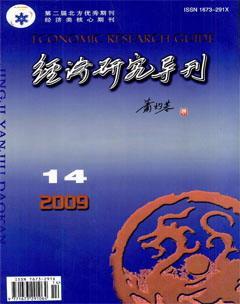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互動研究
王 巖
摘要: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讓我國本土非營利組織得到我國政府正式關注,并為非營利組織提供一個快速成長的契機。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保護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非營利組織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如何在突發公共事件中發揮非營利組織的最大優勢,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成為當前學界研究的主要內容。
關鍵詞:突發公共事件;政府;非營利組織;互動
中圖分類號:F1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4-0207-02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我國政府第一時間組織救災隊伍進駐災區,與此同時,國內外一百多個非營利組織迅速作出反應,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災區,協助政府搶救生命、安置災民、募集捐款,將各種損失降低到最小。雖然政府是救災的主體,非營利組織只是配合政府完善救災工作,但這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仍然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處理突發公共事件時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各自的優勢及區別
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具有不同的組織體制、資源和社會優勢,在參與突發公共事件管理中的著眼點、應急資源來源、活動區域、行為效力以及參與方式上都有著各自的特點。因此,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兩者之間應當相互配合,加強溝通,協同運作,共同應對突發公共事件。
一是著眼點有所不同。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參與突發公共事件管理的目標是一致的,都為了減少危機帶來的損害,盡快恢復社會的正常秩序。但政府著眼于整個國家、社會和全體公民的利益,力求保障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和經濟社會穩定,政治性較強。而非營利組織更著重于保障受災群體的基本利益,緩和社會矛盾,公益性較強。
二是應急資源來源不同。政府作為突發公共事件管理的主體,其在危機處置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可以通過行政手段發動,物質和財力資源可以從各級財政中支出。政府有權力根據實際情況對應急資源進行權威性分配。而非營利組織的應急資源部分來自政府的資助,主要來自社會捐贈以及社會志愿集資。
三是活動區域不同。根據我國的憲法和法律,一個地區的一級政府在突發公共事件管理中承擔著雙重義務:既要負責本地區的危機管理,又要配合上級政府或鄰近地區的政府做好危機管理。而非營利組織在這方面則要靈活得多,一般按自身網絡、政策、資源而定,并沒有法定活動區域[1]。
四是行為效力不同。經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政府可享有一系列緊急權力,其作出的決策和行動具有很強的法律效力,公民必須無條件遵行。非營利組織則強調獨立的志愿人員及被幫助對象的自愿參與,其所做的決策和所進行的活動注重說服力,而非強制力。
五是參與方式不同。政府可以采取豐富多樣的突發公共事件管理措施,除政治、經濟、法律手段外,政府還可以動用警察、軍隊。非營利組織則主要通過溝通、協作、互惠與合作,提供人員支持、資金募集、心理援助等更好的服務來贏得自己的生存權利和空間。
二、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互動中存在的問題
在近年來的幾次大型突發公共事件的管理中,非營利組織的介入逐漸增多,與政府同為管理主體,兩者相輔相成,優勢互補。但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仍然存在著諸多障礙和問題,有政府管理方面的因素,也有非營利組織自身缺陷,還有社會環境的制約。
第一,缺失一套合理的法律體系和明晰的制度設計。在“5·12”地震救援中,全國出現了大大小小的募捐賬戶,大部分以網絡為媒介不斷傳播。除了中國“紅十字”及其政府法定承認的非營利組織之外,其他臨時性非營利組織號召募捐在嚴格的法律意義上都是非法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牛博網事件”。沒有合理的法律確認,各非營利組織便無法以合法的身份在第一時間內展開救災活動;而政府執法部門為保護廣大群眾的利益,防止不法之徒趁機行騙,不得不對每個涉及募捐的非營利組織進行詳細核查。
第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缺乏必須的信任。一方面,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執行力信心不足。政府在對災區進行救援戰略部署時,并沒有將非營利組織看做是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以致大部分非營利組織在趕赴災區之時,并不知道應當執行的任務。山東“農民救援隊”在趕赴災區的路上一度被路政等執法部門懷疑并進行盤查。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對政府同樣缺少足夠的信任。它們并沒有及時向政府及其相關部門匯報信息、應急計劃和措施,而是盲目地選擇了“先到災區再說”。
第三,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信息溝通不暢。“5·12”地震發生之際,能隨時掌握第一手資料的是救災主力軍的政府。如果政府不能將其掌握的信息準確及時地傳遞給非營利組織,它們就無法合理分配物資,不能將物資送到最需要的災民手中,甚至會造成資源過度使用或浪費。北京某基金組織沒有得到最新的救災信息,也沒有經過統一調度,一味地將賑災物資運往映秀災區,到達之后才發現當地災民已基本全部撤離。
第四,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經濟監督不到位。在募集善款的過程中,非營利組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通過政府的正式授權,號召廣大群眾為災區捐獻,通過層級的傳遞匯攏,最終將物資送達災區。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政府沒有對非營利組織進行必要的經濟監督,對物資流轉進行暗箱操作,那么就難免會造成人為的資源浪費流失甚至是貪污。“5·12”地震后,中國“紅十字”會相繼出現了“資金流向不明”、“捐款部分被挪用”等情況,從而使捐助者對其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
第五,非營利組織自身發展諸多不足。我國本土的非營利組織起步較晚,現在仍然處于探索成長階段,與國外相對運作成熟的非營利組織相比,還尚顯稚嫩。在“5·12”地震救援中,本土非營利組織充分暴露了分工不明確,專業化程度較低,缺乏迅速反應能力和統一組織協調能力等問題。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更好地互動溝通。
三、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機制的建立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關系既有密切聯系、良性互動的一面,也有彼此矛盾、非良性互動的一面。為了更有效地滿足社會公眾的需要,提高公共事務管理的績效,促進公共利益的實現,大力推進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良性互動關系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國現行體制下,政府是突發公共事件管理的主力軍,非營利組織以其獨特的優勢承擔了政府不能做、不愿做、做不好的大量工作。在這方面,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密切配合,是推動搶險救災順利進行不可忽視的力量。
其一,政府應盡快出臺處理突發公共事件的相關法律法規。完備的法律法規和計劃安排是突發公共事件管理的制度保障。截至目前,我國已完成國家總體應急預案,25件專項應急預案,80件部門應急預案,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防洪法》、《防震減災法》、《消防法》等等,而《突發事件應對法》的出臺填補了我國長期以來缺乏統一處理突發公共事件的基本大法的空白[2]。在《突發事件應對法》中應明確規定政府的緊急管理權、政府在緊急狀態下的回應措施、緊急狀態下的法律責任等。
其二,明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優勢互補。政府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時具有某些獨特的優勢,如大量的人、財、物資源,嚴密的管理體系,強制性的管理機制等。但由于其結構和權利的局限,往往會造成高成本、資源汲取能力約束、基層動員能力欠缺以及政策執行盲區等“政府失靈”問題。作為政府的“搭檔”,非營利組織發揮自我組織機制所帶來的快速反應、多中心決策所帶來的特需滿足能力、專業化決策所帶來的高效率、貼近社會所帶來的資源動員能力、靈活多樣所帶來的持續作用等優勢,彌補了政府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不足。
其三,完善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處理突發公共事件中的監督機制。“牛博網”和“紅十字”會事件把經濟監督問題擺上了桌面。監督機制應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雙方共同執行,政府在不干涉非營利組織獨立性的基礎上,督促其將資源運轉科學化、透明化。“牛博網”事件最終被警方調查清楚情況,正是因為羅永浩將其募捐賬戶每一筆資金的流動以清晰票據照片的形式在網絡上公開。利用網絡體現百分之百的透明度不僅為“牛博網”證明了清白,同時也為非營利組織資源流動監督機制開辟了一條新的渠道。
其四,保持我國本土非營利組織自身的健康發展。參加“5·12”抗震救災的英、美國際救援隊擁有一整套成熟的組織機構和運作方式,包括充裕的資金來源、較強的專業知識、受過專業化訓練的志愿者、政府的政策研究員等。正是這次地震救援將國外更多的先進經驗帶到國內,促進了本土非營利組織進一步成長。要實現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互動的最佳效果,本土非營利組織必須學習國外成熟的非營利組織的運行機制,從提高專業化素質、提高籌資能力、建立完整的突發公共事件應對機制、創新跨地域應急協同機制等方面入手,不斷加強自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