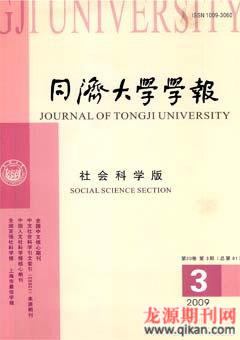論克里斯蒂娃的新女性主義
高宣揚(yáng)
摘要:克里斯蒂娃的思想超越了同時(shí)代各種女性主義,不再單純探討“性”的問(wèn)題,而是從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多學(xué)科的廣闊視野,特別從她的新型精神分析學(xué)和符號(hào)論的角度,集中研究女性在人類文化創(chuàng)造事業(yè)中的特殊貢獻(xiàn),通過(guò)具體個(gè)別的女性形象,包括杰出的女思想家、文學(xué)家和心理學(xué)家的范例,通過(guò)“母親功能”和“女性效果”的特殊的象征性意義,展示人的個(gè)體性及其不同社會(huì)文化共同體的多重異質(zhì)性,為21世紀(jì)人類文化重建事業(yè)提供嶄新的人文主義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女性主義;個(gè)體性;異質(zhì)性;精神分析學(xué);符號(hào)論
中圖分類號(hào):B565.6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9-3060(2009)03-0009-10
人們往往簡(jiǎn)單地把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歸人當(dāng)代女性主義思想家行列中,卻恰恰忽略其思想的特殊性及其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跨學(xué)科研究的深刻而廣泛的基礎(chǔ)。其實(shí),就其思想淵源、內(nèi)容、發(fā)展思路、多學(xué)科視野及其研究方法的多重復(fù)雜性而言,克里斯蒂娃都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同時(shí)代其他女性主義的狹小專業(yè)領(lǐng)域,使她從20世紀(jì)80年代起,就成為了當(dāng)代女性主義思想家的一位新典范,名副其實(shí)地集中反映了當(dāng)代女性主義和西方人文思潮的復(fù)雜性質(zhì)及其在新歷史時(shí)期內(nèi)重建人類文化的重要價(jià)值。
一、女性主義思想的多重復(fù)雜性
女性主義不是單純探討“性”的問(wèn)題,也不能簡(jiǎn)單地歸結(jié)為探索男女兩性關(guān)系以及關(guān)于女性解放的理論范疇。克里斯蒂娃的理論成果表明:女性主義既是一種社會(huì)文化現(xiàn)象,又是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本身所應(yīng)該深入探索的一種理論及其歷史存在的維度,也是社會(huì)實(shí)踐和當(dāng)代實(shí)際生活所面臨和必需解決的重要問(wèn)題。女性解放問(wèn)題固然重要,也需要在實(shí)踐和理論兩方面給予解決,但在克里斯蒂娃看來(lái),女性解放的問(wèn)題,必須超出兩性關(guān)系的范圍,從人類文化及其歷史整體以及多學(xué)科研究的視野出發(fā),把女性主義思想研究納入人類文化和思想史的總體框架中,并緊密地與人本身的多元異質(zhì)性及其復(fù)雜生命體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聯(lián)系在一起。
一般地說(shuō),當(dāng)代法國(guó)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刻變革,經(jīng)歷了三個(gè)理論世代的轉(zhuǎn)變。第一階段是以西蒙·德波娃為主要代表的第一波;西蒙·德波娃在《第二性》著作中闡明富有時(shí)代意義的“第二性”理論,旨在批判古典社會(huì)文化的男女不平等性質(zhì),并試圖走出傳統(tǒng)女性主義的理論框架。
西蒙·德波娃指出: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的男女兩性關(guān)系,并非自然的兩性關(guān)系,并不是自然界的陽(yáng)電和陰電之間的那種關(guān)系。“人類被說(shuō)成是男性的;人和男人,并不是根據(jù)女人自身、而是根據(jù)相對(duì)于他的關(guān)系來(lái)界定女人的。女人并不被當(dāng)作是一個(gè)自律的生命生存物。”“女人,除了男人決定她以外,什么也不是。因此,當(dāng)人們談到‘性的時(shí)候,基本上是想說(shuō):女人主要是相對(duì)于男人才是一個(gè)有性的生命體;也就是說(shuō),只有對(duì)于男人,對(duì)于他,女人才是性的,才是絕對(duì)的女性。……他是主體,他是絕對(duì);而她是‘他者。”在西方社會(huì)中,即使是在實(shí)現(xiàn)了民主化、法制化、科學(xué)化和平等化的當(dāng)代社會(huì)中,女人始終都是被當(dāng)作男人的附屬品,根據(jù)她同男人的關(guān)系而決定其社會(huì)文化地位。“男人在做男人時(shí)是正當(dāng)?shù)模嗽谧雠藭r(shí)卻是不正當(dāng)?shù)模痪褪钦f(shuō),……現(xiàn)在男性就是人類的絕對(duì)標(biāo)準(zhǔn)。”正因?yàn)檫@樣,西蒙·德波娃說(shuō):“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變?cè)斐鰜?lái)的”;女人不單是“女性”,更確切地說(shuō),她是“第二性”。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jì)60年代到70年代被稱為第二波的“解構(gòu)的女性主義”,其主要代表是德里達(dá)、福柯和伊利嘉瑞(Luce Irigaray,1932-)等;當(dāng)時(shí)還年輕的克里斯蒂娃也曾經(jīng)是這個(gè)思想隊(duì)伍的一個(gè)成員。在這一時(shí)期,為了徹底批判傳統(tǒng)的男性夫權(quán)中心主義的西方文化和語(yǔ)言霸權(quán),他們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和思維模式進(jìn)行徹底的解構(gòu),試圖顛覆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理論基礎(chǔ);“解構(gòu)”成為了當(dāng)時(shí)的女性主義的基本范疇。
進(jìn)人20世紀(jì)80年代至今,以克里斯蒂娃為主要代表的第三波,越出了前兩期女性主義的思想界限,使理論探索向兩個(gè)層面縱深發(fā)展:首先跳出二元對(duì)立的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模式,不從“男女對(duì)立”的視野,也不再一般地圍繞“女性”范疇進(jìn)行研究,而是以特殊的“女性身份”,特別是“母親功能”(fonctionmaternelle)為典范,通過(guò)一系列具體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歷史分析,以無(wú)以倫比的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向世人展示貫穿人類歷史的“女性效果”的無(wú)可辯駁性及其不可取代性,更廣闊和更深刻地朝向人的思想及其文化的深度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分析,由此進(jìn)一步揭示人的個(gè)體性及其不同社會(huì)文化共同體的多重異質(zhì)性;其次,在徹底批判迄今為止人類文化及其有限性的基礎(chǔ)上,重新探索未來(lái)人類文化發(fā)展的多重可能性以及女性在創(chuàng)建新型文化模式中的關(guān)鍵角色。
所以,在名目繁多的當(dāng)代女性主義潮流中,克里斯蒂娃的杰出貢獻(xiàn),恰恰在于巧妙地處理女性主義思想與人類文化重建的內(nèi)在關(guān)系,開(kāi)創(chuàng)一種超越傳統(tǒng)“一般/個(gè)別”、“主體/客體”、“真/假”的二元對(duì)立統(tǒng)一模式的新視野,以“現(xiàn)象學(xué)還原”方法,讓“最原初的現(xiàn)象本身自我顯現(xiàn)”,即“通過(guò)生物學(xué)和生理學(xué)的特殊性,使女性身份呈現(xiàn)為一種象征性的事實(shí),也就是說(shuō),變成為一種自我生存的方式,以對(duì)抗社會(huì)的一致性標(biāo)準(zhǔn)和語(yǔ)言霸權(quán)”。
克里斯蒂娃總結(jié)了女性主義的歷史經(jīng)驗(yàn),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代女性主義的內(nèi)容和基本訴求已經(jīng)不是重復(fù)古典女性主義單純爭(zhēng)取改善女子社會(huì)地位和擴(kuò)大政治權(quán)力的口號(hào),也不是像西蒙·德波娃那樣停留于一般地分析女性的條件,而是發(fā)揚(yáng)鄧斯·司各托的個(gè)體化原則,主張把生命個(gè)體當(dāng)做完善的存在,當(dāng)做自然的真正目的,當(dāng)做一個(gè)無(wú)法否定的獨(dú)立實(shí)在,以便向人類整體文化的根本性質(zhì)及其深度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全面探索,試圖解決人類社會(huì)和文化創(chuàng)建以來(lái)長(zhǎng)期埋伏在深層結(jié)構(gòu)中的基本矛盾。
二、人的精神心理層面的復(fù)雜異質(zhì)性
克里斯蒂娃新女性主義的理論建構(gòu),立足于對(duì)近50年理論研究成果的深刻總結(jié),尤以吸收精神分析學(xué)、符號(hào)論、宗教學(xué)、語(yǔ)言學(xué)和文學(xué)評(píng)論的最新成果為重點(diǎn)。
克里斯蒂娃對(duì)于女性的精神分析學(xué)研究,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方面是法國(guó)思想界、特別是拉康和羅蘭·巴特所創(chuàng)建的精神分析學(xué)和符號(hào)論新成果;第二方面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對(duì)女性精神心理特征的專門研究及其重要發(fā)現(xiàn),而在這方面她又比法國(guó)同時(shí)期其他精神分析學(xué)家更重點(diǎn)地吸收美國(guó)女精神分析學(xué)家梅拉尼·克萊因等人的特殊觀點(diǎn)。
1“盡可能趨近話語(yǔ)”
克里斯蒂娃極端重視語(yǔ)言與精神心理活動(dòng)的密切關(guān)系。她引用法國(guó)著名語(yǔ)言學(xué)家埃米爾·本維尼斯的話說(shuō):“正是在、并通過(guò)語(yǔ)言,人才建構(gòu)起自己的主體。”克里斯蒂娃不把語(yǔ)言當(dāng)成不可破解的密碼防線,而是把它當(dāng)成儲(chǔ)備豐富的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的意義儲(chǔ)藏庫(kù),也是一切現(xiàn)實(shí)的和可能的、歷史的和未來(lái)的、現(xiàn)存的和潛在的各種意義的海洋,又是過(guò)往的和即將創(chuàng)建的生命體的誕生搖籃。
因此,只有接近和深入語(yǔ)言,才能揭示進(jìn)行思考和創(chuàng)作行動(dòng)的個(gè)體的復(fù)雜思路,才能揭示其思想奧秘。
為此,克里斯蒂娃嚴(yán)厲批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xué)中采用的傳統(tǒng)線性時(shí)間觀念,特別批判弗洛伊德關(guān)于“記憶痕跡”、“過(guò)度加工精制”
、“轉(zhuǎn)移的解體”的概念,揭示了弗洛伊德采用“主體/客體”模式進(jìn)行精神分析的“非文本間性”的實(shí)質(zhì)。
克里斯蒂娃以新的文本間性符號(hào)論為核心,試圖徹底擺脫深受傳統(tǒng)二元對(duì)立模式影響的古典語(yǔ)言學(xué)及其符號(hào)論基礎(chǔ)。她認(rèn)為,在文本間的所有穿梭和超越活動(dòng),正是為了實(shí)現(xiàn)“盡可能地趨近話語(yǔ)”。
她從符號(hào)研究出發(fā),創(chuàng)造性地運(yùn)用拉康的后弗羅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將文本結(jié)構(gòu)中符號(hào)相互關(guān)系所隱含的人類思想心態(tài),當(dāng)作是文本問(wèn)及文本和非文本相互間進(jìn)行穿插互動(dòng)的基本動(dòng)力和基本內(nèi)容,從而將文本分析不但從單一文本內(nèi)的封閉分析走脫出來(lái),而且轉(zhuǎn)向文本間及文本和非文本間的廣闊領(lǐng)域。在文本間穿越結(jié)構(gòu)的廣闊分析中,她只是將文本符號(hào)當(dāng)成作者、讀者和非讀者間的心態(tài)交流的中介,使符號(hào)分析也從單純的“意義/符號(hào)”和段落間的相互關(guān)系的分析走脫出來(lái),變成為符號(hào)、意義、心態(tài)、文學(xué)風(fēng)格和社會(huì)文化間相互交流的場(chǎng)域。
文本,作為一個(gè)一個(gè)獨(dú)立的文化生命體,雖然是各個(gè)不同的作者的精神產(chǎn)品,但它們比作者們更具有生命力,更含有恒久的再創(chuàng)造精神。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文本間性”不但不是簡(jiǎn)單地替代了原有的作者主體間性,而且,將主體間性進(jìn)一步擴(kuò)大,也進(jìn)一步深化,使之成為文本間和各時(shí)代文本作者和讀者以及非讀者之間相互理解和相互穿越而進(jìn)行創(chuàng)造的中介。
克里斯蒂娃關(guān)于文本間穿插性的概念,最早是在她的著作《符號(hào)單位研究:關(guān)于一種意義單位分析的探究》。中提出來(lái)的。她所說(shuō)的“意義單位”(seme)也被譯為“義素子”。任何由符號(hào)體系所構(gòu)成的文本的基本內(nèi)容,都具有上層和深層的雙重結(jié)構(gòu)。在內(nèi)容的上層結(jié)構(gòu)中,由義素子的相互關(guān)連,往往采取符號(hào)關(guān)系的語(yǔ)句結(jié)構(gòu)表達(dá)出來(lái)。而在深層結(jié)構(gòu)中,義素子始終是作為一種存在于內(nèi)在體系的固定單元。但是,克里斯蒂娃等人并不把意義單位或義素子當(dāng)成某種實(shí)體的東西,它的存在始終是靠它們乏間的相互關(guān)系及相互轉(zhuǎn)化來(lái)保障的。因此,在她看來(lái),文本是某種具有意義的符號(hào)不斷地進(jìn)行能指化的實(shí)踐活動(dòng),它并不受到亞里士多德邏輯的約束。文本和文本間的運(yùn)作方式采用某種類似于由語(yǔ)法和對(duì)話活動(dòng)所混合構(gòu)成的特殊方式。任何文本的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都必須在文本間加以考察,因?yàn)闃?gòu)成文本內(nèi)容和意義的基礎(chǔ)因素,并不僅僅是負(fù)載意義的符號(hào)及其關(guān)系網(wǎng),而且還包含滲透于其間的對(duì)話要素,也就是文本間的生命交流性。文本中所運(yùn)載的上述內(nèi)容和意義的復(fù)雜性,使文本有可能采取符號(hào)及類似于符號(hào)的各種象征體系,包括各種姿態(tài)、嘉年華活動(dòng)以及各種文學(xué)藝術(shù)形式等等。
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穿插性基本范疇,也使她進(jìn)一步在文學(xué)藝術(shù)和社會(huì)文化型態(tài)的多種領(lǐng)域中,探討多種形式的“說(shuō)話的主體”及其運(yùn)作和實(shí)踐過(guò)程。她綜合地運(yùn)用辯證唯物主義、語(yǔ)言學(xué)和精神分析學(xué)的方法,深入分析畫(huà)家基奧多和貝里尼的繪畫(huà)形式,也研究阿爾托、喬易斯、瑟林、貝克特、巴岱和梭列爾等人的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以便透過(guò)會(huì)話和文學(xué)語(yǔ)言等多種符號(hào)運(yùn)用方式,探索不同文學(xué)藝術(shù)和文化產(chǎn)品間進(jìn)行文本間穿越性的運(yùn)作的可能性。
根據(jù)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間性概念,所有的文本,不管是明顯的或者隱蔽的引用其它文本,都是以其它文本為基礎(chǔ)而建構(gòu)和不斷生成的。因此,文本就是同它相對(duì)話的其它文本的閱讀和再閱讀。不僅如此,文本間性也把文本的生產(chǎn)力和自我更新超越文本語(yǔ)言結(jié)構(gòu)的范圍,從而使文本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過(guò)程擴(kuò)大到人類文化歷史領(lǐng)域,使文本有可能超出語(yǔ)言的范圍,成為超語(yǔ)言領(lǐng)域內(nèi)各種社會(huì)文化力量同語(yǔ)言文字網(wǎng)絡(luò)相互滲透的中介。正如克里斯蒂娃本人所說(shuō),文本的文字結(jié)構(gòu)不過(guò)是文本表面的交叉點(diǎn),它實(shí)際上是多種文字的一種對(duì)話,它是創(chuàng)作者同接受者、同實(shí)際文化脈絡(luò)以及同歷史文化脈絡(luò)之間的對(duì)話。
社會(huì)和歷史一旦透過(guò)文本本身呈現(xiàn)出來(lái),在對(duì)話中的各個(gè)主體也在文本的閱讀中呈現(xiàn)出來(lái)。由此可見(jiàn),文本間性的概念同時(shí)也包含著主體間性的概念。
這樣一來(lái),通過(guò)符號(hào)和文本間的廣闊空間和視野,創(chuàng)作者可以自由地超越時(shí)間的一線性和單向性,超越“主體/客體”的二元維度,借助于“中性書(shū)寫(xiě)”的中介,利用語(yǔ)言文字以外的新符號(hào),在“語(yǔ)言的潛意識(shí)”中釋放出無(wú)限的創(chuàng)造能量,來(lái)回游戲于符號(hào)和文本間的結(jié)構(gòu)夾縫中,以便充分發(fā)揮由幻覺(jué)和想象力所開(kāi)拓的“無(wú)中心”和“無(wú)邊界”的新思路王國(guó)的可能疆域,創(chuàng)造出各種適合于創(chuàng)作理念的新意義,把無(wú)窮無(wú)盡的符號(hào)創(chuàng)作游戲引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創(chuàng)建“對(duì)于意義的渴望”新范疇
克里斯蒂娃不滿足于單純?cè)诰穹治鰧W(xué)范圍內(nèi)研究人的異質(zhì)性,把原本屬于傳統(tǒng)本體論的超越性和內(nèi)在性,轉(zhuǎn)換成精神分析學(xué)的研究范疇,一方面使本來(lái)抽象的哲學(xué)問(wèn)題得到了具體而深刻的精神分析學(xué)的說(shuō)明,另一方面又把精神分析學(xué)提升到形而上學(xué)的新高度。
她認(rèn)為,從精神分析學(xué)的角度來(lái)看,超越性和內(nèi)在性實(shí)際上都源自人性中“對(duì)于意義的渴望”。
克里斯蒂娃強(qiáng)調(diào)指出:“對(duì)于意義的欲望”同基于性欲的“快感欲望”具有內(nèi)在的密切聯(lián)系。在本質(zhì)上,人始終是受到“對(duì)于意義的渴望”和“對(duì)于快感的欲望”的雙重驅(qū)使下的存在者,不斷地追求具有文化審美價(jià)值的“崇高”,并由此持續(xù)地推動(dòng)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創(chuàng)造活動(dòng)。
3在宗教信仰中揭示“原初心理基礎(chǔ)”
克里斯蒂娃在精神分析學(xué)方面的研究成果,近幾年來(lái)更集中在對(duì)于人的宗教信仰心理的探索方面。她指出,人不只是滿足于現(xiàn)實(shí)的活動(dòng),也不滿足于現(xiàn)實(shí)的欲望,而是不斷尋求弗洛伊德所說(shuō)的那種“對(duì)不存在的世界的幻想”,而且,這種“作為幻想的幻想”,往往是人的各種信仰活動(dòng)及其社會(huì)文化實(shí)踐的最初基礎(chǔ),也成為人類更復(fù)雜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的原初根基。
克里斯蒂娃強(qiáng)調(diào)了人在信仰中把“思想”、“行動(dòng)”和“言說(shuō)”統(tǒng)籌在一起的絕妙生存特征。換句話說(shuō),人是一個(gè)“在說(shuō)話中思想和行動(dòng)的創(chuàng)造者”,但人的這種特殊存在形式必須以“相信”(croire)為出發(fā)點(diǎn)。沒(méi)有最起碼的信念,任何人都無(wú)法生活和生存,更無(wú)法開(kāi)展思想和行動(dòng),也無(wú)法說(shuō)話。所以,“說(shuō)話的生存物就是相信的生存物”。
克里斯蒂娃說(shuō):“人的身體和心理精神世界隱含著能量無(wú)比的創(chuàng)造基因,這也就是古希臘圣哲亞里士多德用Energeia概念所要表述的人類固有的潛在創(chuàng)造能力。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出發(fā),通過(guò)對(duì)于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各種文本和文本問(wèn)的互動(dòng)以及人類行動(dòng)本身所不斷發(fā)出的意義信號(hào),在符號(hào)論和精神分析學(xué)的光輝照耀下,思想家們可以進(jìn)一步深入揭示宗教領(lǐng)域的各種奧秘,揭示在這些奧秘中所隱含的人類本身的奧秘。”
克里斯蒂娃認(rèn)為,唯有通過(guò)宗教心理的分析才能使人類精神和身體的生命奧秘徹底地揭示出來(lái)。
作為人性的集中表現(xiàn)和特殊表現(xiàn),女性對(duì)信仰的思想情感可以典型地展示人性信仰基礎(chǔ)中的最復(fù)雜結(jié)構(gòu)及其運(yùn)作模式。正因?yàn)檫@樣,在她最近的對(duì)話錄中,克里斯蒂娃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女性的個(gè)人生命創(chuàng)造能力,同時(shí)也突出女性心理結(jié)構(gòu)中最能體現(xiàn)人類原初情感的“愛(ài)”的因素,凸現(xiàn)女性精神心理的優(yōu)點(diǎn)和創(chuàng)造性品格。克里斯蒂娃指出:“女性的豐富多產(chǎn)性及妊娠期至今仍然是想象的極有魅力的對(duì)象,而且還是神圣性的一個(gè)隱居所。對(duì)當(dāng)代宗教信仰來(lái)說(shuō),所謂‘彼岸不再是超越我們頭頂?shù)漠愄帲窃谀?/p>
親的肚子里。因此,成為一個(gè)母親,在今天,就意味著面臨真正的宗教情感的幸存者。”
為此,克里斯蒂娃除了在她的《才女系列》三卷本中探索女性的復(fù)雜而卓越的心理世界以外,還在《女性與神圣》。和《德列絲,我的愛(ài)》。等書(shū)中特別深入分析基督教歷史上出現(xiàn)過(guò)的“圣女”的心理世界;正是在她們的特殊的心理世界中,克里斯蒂娃進(jìn)一步發(fā)現(xiàn)人性的純潔性、高尚性和無(wú)限創(chuàng)造性及其信仰基礎(chǔ)。
這樣一來(lái),克里斯蒂娃把女性心理分析進(jìn)一步朝向縱橫兩方面發(fā)展:一方面通過(guò)多學(xué)科的迂回和交錯(cuò),延伸到更廣闊的總體人類學(xué)研究和非人本中心的文化研究;另一方面,通過(guò)與語(yǔ)言學(xué)、心理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特別是宗教人類學(xué)和精神病理學(xué)的研究的結(jié)合,更深入地探討人類的信仰和生活世界的“最原初”深層結(jié)構(gòu),把“母親”與幼兒的最初心理和語(yǔ)言聯(lián)系模式,當(dāng)成人類個(gè)體和群體信仰的普遍性心理基礎(chǔ),更深入地說(shuō)明人類創(chuàng)造活動(dòng)的復(fù)雜性。
三、女人的獨(dú)一無(wú)二性
為了更深入理解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義思想的獨(dú)特性,我們不妨從她的《獨(dú)自一個(gè)女人》。一書(shū)的基本思想談起。
《獨(dú)自一個(gè)女人》這個(gè)題目還向人們宣示:女人,突出地顯示一切生命的獨(dú)一無(wú)二性;女人,以其個(gè)體的特殊存在方式,以其獨(dú)創(chuàng)卓絕的精神和肉體,是任何象征強(qiáng)權(quán)力量的男人所無(wú)法取代、不可化約和不可同一化的創(chuàng)造生命體;“獨(dú)自”兩字,不是表示“孤立無(wú)援”的絕望存在,而是強(qiáng)調(diào)她和她們的“獨(dú)自不可取代的尊嚴(yán)”。
克里斯蒂娃由此一再地號(hào)召所有的女人:“你們要一再地使自己不再成為過(guò)去的自己,你們務(wù)必要以自身的奇特性,創(chuàng)造你及你們自身。”“女人應(yīng)該也完全可以不被同類化,不被一致化;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也有比其他生命體更優(yōu)越的條件,使自身成為隨時(shí)變動(dòng)和隨時(shí)創(chuàng)新的自由生命。”
克里斯蒂娃的特殊的女性主義,典型地體現(xiàn)在她的“女性天才系列”三卷本:《阿倫特》、《梅拉尼·克萊因》、《柯列特》。在談到她的“女性天才系列”時(shí),克里斯蒂娃明白地指出:“訴諸于每個(gè)男人或女人的天生才資,并不是低估歷史的意義,而是試圖超越女性的條件,就好像超越一般人的條件那樣,超越生物學(xué)、社會(huì)和命定的界限;這也就是要強(qiáng)調(diào)主體有意識(shí)地或無(wú)意識(shí)地反抗各種決定因素的規(guī)定而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價(jià)值。”
1哈娜·阿倫特
克里斯蒂娃指出:“生命”是哈娜·阿倫特整個(gè)作品的核心,也是她的女性經(jīng)驗(yàn)和猶太人遭遇的“不可動(dòng)搖的支柱”。作為女性思想家,阿倫特極度熱愛(ài)生命和非常珍視生活。阿倫特為此竭盡全力維護(hù)和捍衛(wèi)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生命,關(guān)注“積極的生活”和“深思熟慮的生活”;為此,寧要自由,寧愿死去,也不要奴顏婢膝地活著。她贊賞塞涅卡所說(shuō)的一句話:“生活若缺乏懂得死去的美德,那無(wú)異于受奴役。”
克里斯蒂娃由此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種生物學(xué)的過(guò)程,而是在持續(xù)應(yīng)對(duì)生活遭遇所提出的問(wèn)題中尋求生存的意義。生命,作為生與死之間的空間,始終緊密地同行動(dòng)聯(lián)系在一起;所謂生命的自由,就植根于不斷更新的重生。在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生命就是愛(ài),愛(ài)普通的人和他人。正是女性的身份才有可能把生命的本質(zhì)當(dāng)成愛(ài)。女性的天性,把生兒育女,把生命的出生,當(dāng)成對(duì)生命自身和對(duì)他人的生命的愛(ài)的集中體現(xiàn)。所以,阿倫特所理解的生命,除了對(duì)他人的愛(ài),別無(wú)其他。
克里斯蒂娃通過(guò)對(duì)哈娜·阿倫特生平的記述和分析,強(qiáng)調(diào)母親角色對(duì)形成人類社會(huì)和文化的本體論意義。
2梅拉尼·克萊因
克里斯蒂娃高度評(píng)價(jià)梅拉尼·克萊因的才女個(gè)人形象及其對(duì)發(fā)展精神分析學(xué)的貢獻(xiàn)。在克里斯蒂娃看來(lái),梅拉尼·克萊因首先通過(guò)其自身親歷的“不幸的母親”的傳奇式女英雄經(jīng)驗(yàn),向人們提供了一個(gè)不可顛覆的見(jiàn)證:一個(gè)女人,憑借她個(gè)人的天資才氣和創(chuàng)造性力量的結(jié)合,通過(guò)其不可戰(zhàn)勝的頑強(qiáng)氣質(zhì)和堅(jiān)忍不拔的女性特有毅力,跨越難以忍受的艱難困苦,逾越現(xiàn)有制度的各種界限和禁忌,終于在對(duì)精神病和自閉癥(autism)的研究中,一方面發(fā)展了弗洛伊德的無(wú)意識(shí)理論,另一方面又徹底地與傳統(tǒng)精神分析學(xué)決裂。克里斯蒂娃認(rèn)為:梅拉尼·克萊因是第一位揭示精神發(fā)展中的“弒母罪”(matricide)角色以及指明“母親是一切創(chuàng)造和思想的真正源泉”的卓越思想家。
3柯列特
選擇柯列特作為典型的才女,目的在于:通過(guò)對(duì)柯列特的特殊的生命歷程的描述,特別是針對(duì)柯列特極其浪漫的愛(ài)情故事,克里斯蒂娃試圖重新估價(jià)柯列特在法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地位。柯列特以作家的身份,突顯出她描述自己所觀察到的自然、世界和他人的奇妙寫(xiě)作技巧。克里斯蒂娃還注意到柯列特的特殊寫(xiě)作風(fēng)格:往往通過(guò)她對(duì)自己童年時(shí)代的回憶,顯示柯列特自己的精神世界的神秘內(nèi)容。
四、人的多元異質(zhì)性
在多種多樣的生命體中,人是唯一最復(fù)雜的多元異質(zhì)性的典范。人的生命的多元異質(zhì)性達(dá)到無(wú)法加以簡(jiǎn)單歸納的程度。
這里所談到的,并不是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所指的“人的本質(zhì)”,不是那種可以脫離人的具體屬性而被抽象出來(lái)的“實(shí)體”,也不是已經(jīng)從活生生的生命活動(dòng)中歸納概括出來(lái)的一般性范疇,而是一方面指人在身體和內(nèi)心精神活動(dòng)層面的雙重多元異質(zhì)性,另一方面又指?jìng)€(gè)體及群體的人的思想文化創(chuàng)造活動(dòng)及其產(chǎn)品的多重異質(zhì)性,包括個(gè)體和群體的人所使用的語(yǔ)言的多元異質(zhì)性。人及其思想文化活動(dòng)的任何一個(gè)性質(zhì)和特征,不管是易以清晰地在外表上呈現(xiàn)出來(lái)的表情、形態(tài)和動(dòng)作,還是深深地掩藏在內(nèi)心底層的心緒、深慮、想象、隱情和思念等“不可見(jiàn)性”,都無(wú)一例外地包含人的身體和精神、個(gè)體和群體兩方面的多重因素所復(fù)雜交錯(cuò)構(gòu)成的生命運(yùn)動(dòng)。
人的多元異質(zhì)性不只是表現(xiàn)在各個(gè)不同的獨(dú)立自主的個(gè)人生活中,而且也表現(xiàn)在同一個(gè)人的內(nèi)外世界的結(jié)構(gòu)及其運(yùn)作方式上,特別是表現(xiàn)在每個(gè)人之間所構(gòu)成的社會(huì)世界及其萬(wàn)花筒式的變幻形象中。同時(shí),構(gòu)成人的各種內(nèi)外因素雖然相互緊密相連,而且也相互獨(dú)立,維持其各自的自律性和獨(dú)立創(chuàng)造性。更主要的問(wèn)題還在于:各個(gè)具有獨(dú)立生命體的個(gè)人及其生活世界,又在多維度的時(shí)空結(jié)構(gòu)中,不斷創(chuàng)造出多元異質(zhì)的社會(huì)文化現(xiàn)象,形成了復(fù)雜多變的歷史、宗教、藝術(shù)、哲學(xué)、文學(xué)、經(jīng)濟(jì)和政治等交錯(cuò)件領(lǐng)域。
1從內(nèi)心世界的復(fù)雜性談起
克里斯蒂娃在2007年出版的《對(duì)信仰的難以想象的渴望》一書(shū)中指出:“重要的問(wèn)題是,思想的主體總是最大限度地把他的思想同他‘在世生存中所遇到的一切聯(lián)系在一起,并由此將思想主體生命內(nèi)外的一切因素都連貫起來(lái),使之在人的生命運(yùn)動(dòng)中相互發(fā)生作用,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人本身的生命創(chuàng)造運(yùn)動(dòng)。”
人的內(nèi)心世界是由精神和情感的無(wú)數(shù)因素所構(gòu)成的;而且,這些無(wú)形的因素叉具有強(qiáng)大的生命力和再生產(chǎn)的能力,以致使它們能夠遠(yuǎn)遠(yuǎn)地超出生產(chǎn)和運(yùn)載它們的身體及其周在世界的有形結(jié)構(gòu);同時(shí),這些內(nèi)在因素,還能夠在其運(yùn)作的過(guò)程中形成某種獨(dú)立于有形世界的“自律性”(autonomie),反過(guò)來(lái)又對(duì)產(chǎn)生和運(yùn)載它們的身體及其周在有形世界發(fā)生強(qiáng)大的反作用,不但牽引著、而且也決定著身體和有形世界的命運(yùn)。
在涉及到有形和無(wú)形、有限和無(wú)限的相互關(guān)系的時(shí)候,事物的邏輯就是如此怪異和富有諷刺性:
內(nèi)在的精神力量和無(wú)形的因素,原本根源于有形的和有限的身體及物體,但前者一旦產(chǎn)生和運(yùn)作起來(lái),卻超出后者的范圍及其約束,反過(guò)來(lái)成為后者的命運(yùn)的決定者。其實(shí),一切事物都是這樣,處于“第二性”的事物,起初往往處于劣勢(shì)和被宰制的地位,但它們卻有望在其生存和運(yùn)作中轉(zhuǎn)弱為強(qiáng)或轉(zhuǎn)劣為優(yōu),倒過(guò)來(lái)成為主宰實(shí)際生活的強(qiáng)大力量。而在男人與女人的相互關(guān)系上,上述邏輯尤其突出地表現(xiàn)出來(lái)。
2信念和欲望的深不可測(cè)性及其頑強(qiáng)性
人的復(fù)雜本性的深不可測(cè)性,不但植根于生命深處的信念和欲望的相互交錯(cuò)性,而且還由于源自生命根底的欲望和信念的不可遏制性、自我生產(chǎn)性及其生生不息性。
信念和欲望是推動(dòng)人的生命不斷頑強(qiáng)地更新和發(fā)展的難以控制的動(dòng)力和源泉。欲望和信念,作為人類心理精神的基礎(chǔ),不僅是實(shí)體性的心理因素,貫穿于生命的始終,也穿梭于人類生命的整個(gè)歷史以及象征性地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整個(gè)人類文化體系。根據(jù)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欲望和信念首先是人類生命,包括其肉體和精神兩個(gè)方面的自我保存和發(fā)展的原動(dòng)力;正因?yàn)檫@樣,欲望和信念也協(xié)調(diào)了人類身體與精神心理世界的各種復(fù)雜因素之間的關(guān)系,使人的生命體的各種相互矛盾和相互交錯(cuò)的異質(zhì)性的異質(zhì)因素能夠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包容地運(yùn)作起來(lái),保障人類生命的復(fù)雜要求的實(shí)現(xiàn),也造成人類生命的復(fù)雜需求的不斷更新和不斷超越。
欲望和信念不只是在調(diào)整和推動(dòng)人類生命體(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的過(guò)程中扮演基礎(chǔ)動(dòng)力和協(xié)調(diào)力量,而且也成為人類生命體及其外在生存世界的極度復(fù)雜構(gòu)成因素的中介性協(xié)調(diào)力量。因此,欲望和信念不只是留存在人的生命內(nèi)部,發(fā)揮其創(chuàng)造性作用,保障生命運(yùn)動(dòng)的不斷更新和成長(zhǎng);而且也擴(kuò)展到生命之外的人類生存世界,與環(huán)繞著人類生命存在的外在世界保持緊密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因此,欲望和信念,使人有可能在生存世界中,超越自我封閉的獨(dú)立生命體的身份,使人自身同他的外在世界有機(jī)地聯(lián)系在一起,并在生命過(guò)程中,不知不覺(jué)地?zé)o形中把人自身嵌入到他的生存世界中,變成了其所處的生存世界的有機(jī)組成部分,以便有利于創(chuàng)建人的自我創(chuàng)造地位。
總而言之,欲望和信念既是生命的基礎(chǔ)和動(dòng)力,又是生命存在和發(fā)展的基本條件;兩者在生命運(yùn)動(dòng)中的作用,向內(nèi)可以無(wú)限地滲透到生命的深不可測(cè)的基礎(chǔ),向外則延伸到無(wú)限的生存世界,包括生存世界的現(xiàn)實(shí)性、可能性和神秘性的部分。
在自我中的無(wú)窮欲望促使人向自身心理底層和向生存的外在世界進(jìn)行無(wú)限的探索和無(wú)止境的追求。但是,自我同他的外在世界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通過(guò)欲望的發(fā)泄與更新的途徑,最早是表現(xiàn)在幼兒同母親的關(guān)系中,根據(jù)梅拉尼·克萊因的研究,幼兒在同母親的關(guān)系中隱含著最早的雙方互動(dòng)欲望之間的模糊界限,使嬰兒的自我中所隱含的欲望同母親的心理欲望產(chǎn)生復(fù)雜的混淆過(guò)程,進(jìn)一步隱含著人類心理發(fā)展一切復(fù)雜過(guò)程的最初原型。
3信念和信仰的人類學(xué)基礎(chǔ)
克里斯蒂娃在改造傳統(tǒng)精神分析學(xué)欲望概念的同時(shí),也創(chuàng)建了具有深刻意義的“信念”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xué)中,信念是作為一種虛幻的超越精神,作為一種消極的否定性生存力量,在向彼岸的宗教世界的過(guò)渡中呈現(xiàn)出來(lái),具有消極的背離文明的意義。但在克里斯蒂娃的新型精神分析學(xué)理論中,經(jīng)過(guò)了徹底改造的欲望概念同信念概念連接在一起,構(gòu)成一個(gè)新的文化理論的基本范疇。克里斯蒂娃指出:人是說(shuō)話的生命體,也是信仰的生命體。
在克里斯蒂娃的欲望概念中,既然對(duì)愛(ài)的對(duì)象的寬容力量超過(guò)使用暴力進(jìn)行征服欲望對(duì)象的手段,那么,在對(duì)于欲望對(duì)象的愛(ài)的追求中,最原初的推動(dòng)心理或心理沖力,就是對(duì)其所愛(ài)的“他者”的一種無(wú)可懷疑的信念,一種神秘不可測(cè)的信仰,一種對(duì)于他者的毫不動(dòng)搖的信念。這樣一來(lái),欲望和信念便同時(shí)產(chǎn)生于人類的最初心理。
克里斯蒂娃所說(shuō)的信念,雖然包含著宗教神學(xué)意義上的信念和信仰,但同時(shí)又遠(yuǎn)遠(yuǎn)超出它們的范圍,具有哲學(xué)本體論和精神分析學(xué)以及人類學(xué)的意義。
克里斯蒂娃認(rèn)為,東西方哲學(xué),從其開(kāi)端便研究了人的信仰問(wèn)題,并把人的信仰問(wèn)題的奧秘性當(dāng)成人性之奧秘的集中表現(xiàn)。人類為什么要信仰,也就是人為什么要生存的問(wèn)題,也是人為什么要思考以及人為什么要說(shuō)話的問(wèn)題,最后,還是人為什么要相愛(ài)的問(wèn)題。換句話說(shuō),人的生存、行動(dòng)、思想、創(chuàng)造和愛(ài)情,都必須以具有某種對(duì)于其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絕對(duì)信仰為基礎(chǔ)。只有相信他者才能夠相信自己。自身的確定性,歸根結(jié)底要靠自身之外的他者的確定性來(lái)保證。所以,克里斯蒂娃從人的自戀出發(fā),引導(dǎo)出人的信仰的欲望,論證了說(shuō)話的人必然成為信仰的人。
人的超越性和內(nèi)在性,使人的生存永遠(yuǎn)伴隨著創(chuàng)造活動(dòng);而不停的創(chuàng)造又必定伴隨著無(wú)止境的憂愁、煩惱、苦惱以及心理的痛苦。正是在這種必然包含著創(chuàng)造與痛苦的雙重矛盾中,人類渴望著信仰,渴望通過(guò)信仰來(lái)鎮(zhèn)定自己,確立自身的生存基礎(chǔ)。快樂(lè)與痛苦,必然絕望的期待和永遠(yuǎn)充滿光明的煩惱,所有這些表明上極端矛盾的心理狀態(tài)構(gòu)成了人生在世的基本心態(tài),也成為人類信仰的最初動(dòng)力。
如果說(shuō)在弗洛伊德那里,信仰包含著幻想的性質(zhì),那么,克里斯蒂娃更多地把信念和信仰當(dāng)成“確定性、充滿激情和感性、具有超生意義的生存心態(tài)以及導(dǎo)致精神狀態(tài)陷入創(chuàng)造性高潮的中介”。
當(dāng)然,在克里斯蒂娃的信念概念中,也絲毫沒(méi)有忽視宗教的作用,沒(méi)有忽略宗教意識(shí)和信仰活動(dòng)對(duì)人類文化建構(gòu)以及對(duì)人的個(gè)人心理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在基督教的圣經(jīng)和神學(xué)中,愛(ài)是作為世界形成的最初條件。克里斯蒂娃的著作《起初是愛(ài):論精神分析與信仰》充分肯定了基督教神學(xué)的“愛(ài)”的概念的正面意義,她強(qiáng)調(diào):“愛(ài)”(agape)是人與神之間的最大中介。
基督教神學(xué)認(rèn)為:假定上帝作為愛(ài)向人顯示他自身,那么,這就意味著神是通過(guò)愛(ài)來(lái)促使人認(rèn)識(shí)他的存在。也就是說(shuō),人對(duì)神的認(rèn)識(shí)是通過(guò)神對(duì)人的愛(ài)以及人對(duì)神的愛(ài),而在這過(guò)程中,人也就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他的“鄰人”的愛(ài),這也就是對(duì)“他人”的愛(ài)。
當(dāng)然,對(duì)于人來(lái)說(shuō),還存在著另外一種不同于對(duì)神的愛(ài)的愛(ài),也就是說(shuō),人總是在尋找其自身的幸福的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對(duì)其自身的愛(ài),同時(shí)也通過(guò)他的欲望和激情的實(shí)現(xiàn),完成他對(duì)他人的愛(ài)。
由此可見(jiàn),通過(guò)對(duì)愛(ài)的概念的分析,克里斯蒂娃進(jìn)一步論證了宗教的信仰與人的欲望之間的一致性,也由此發(fā)現(xiàn):信仰和欲望一樣構(gòu)成為人性深處的最原初的基礎(chǔ)。
五、母親:人類社會(huì)和文化的真正原型
克里斯蒂娃強(qiáng)調(diào),在幼兒同母親的既復(fù)雜又模糊的心理關(guān)系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愛(ài)的力量。傳統(tǒng)精神分析學(xué)把愛(ài)的決定性意義幾乎全部轉(zhuǎn)移到性愛(ài)關(guān)系中,特別是強(qiáng)調(diào)了父親在兩性相愛(ài)關(guān)系中的決定性角色,從而產(chǎn)生了人類男性父權(quán)中心主義的一切文化創(chuàng)造模式的基礎(chǔ)典范。與此相反,從梅拉尼·克萊因開(kāi)始,再經(jīng)過(guò)克里斯蒂娃的加工和發(fā)展,更進(jìn)一步明確了在幼兒的欲望展現(xiàn)和追求過(guò)程中,決定著人類心理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并不是以父親的名義而形成的兩性關(guān)系,更不是在父親的權(quán)威的庇護(hù)下的男性性欲作為根底的創(chuàng)造性欲望,而是在幼兒同母親的關(guān)愛(ài)關(guān)系中的“愛(ài)”的因素。這是真正樹(shù)立人的心理精神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也就是說(shuō),是人類形成個(gè)人的自我與社會(huì)的道德規(guī)范之間相互連接
的基礎(chǔ)。
同時(shí),幼兒同母親的愛(ài)的關(guān)系也是整個(gè)社會(huì)和文化創(chuàng)造的典范,因?yàn)樵谄渲兄该髁巳说挠捌錆M足的過(guò)程始終離不開(kāi)自我與他者的合理關(guān)系,同時(shí)也離不開(kāi)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相互寬容。作為人性最原初的模式,幼兒心理中最早形成的母子關(guān)系,盡管呈現(xiàn)出極其模糊和極其紊亂的形態(tài),但它恰恰是任何個(gè)人、人類社會(huì)以及整個(gè)文化的不可否認(rèn)的原型。這樣一來(lái),作為精神分析學(xué)基本概念的欲望,就從原來(lái)男性父權(quán)中心主義的邏輯框架中解脫出來(lái),也從充滿暴力潛能的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模式中解脫出來(lái),轉(zhuǎn)化成為有利于創(chuàng)建人類生命體本身的不斷更新以及社會(huì)不斷創(chuàng)新的仁慈生命力。
克里斯蒂娃還進(jìn)一步把“母親功能”提升到形而上學(xué)的高度,強(qiáng)調(diào)它在探索人性基礎(chǔ)和人生意義方面的絕對(duì)重要性。克里斯蒂娃為此集中環(huán)繞“母性時(shí)間”和“母性語(yǔ)言”兩個(gè)關(guān)鍵范疇,強(qiáng)調(diào)母性情感及其自然心理機(jī)制在建構(gòu)人類文化方面的存在論意義。
克里斯蒂娃首先揭示母性時(shí)間的特殊意義。她指出:母性時(shí)間不像父性時(shí)間那樣只注重單向的延續(xù)性、系統(tǒng)性和封閉性,而是極端重視原始性、循環(huán)性、重生性和開(kāi)放性。在父性系列中時(shí)間是有始有終,是從生到死的系統(tǒng)。但在母性時(shí)間中,嬰兒的誕生并不只是與死亡相對(duì)立的“初生”,而是作為“愛(ài)”和作為“與他者相融合”的新起點(diǎn),是永遠(yuǎn)向多維度延伸和有可能重生的條件。克里斯蒂娃說(shuō):“母性時(shí)間既不是瞬間,也不是不可逆轉(zhuǎn)的時(shí)間流;而男人比女人更易于執(zhí)著那種不可逆轉(zhuǎn)的時(shí)間流。母性時(shí)間則是盡其所能地導(dǎo)向重生的一種延續(xù)性。”
母性時(shí)間的上述特性也使母親有可能真正把握人生的自由本質(zhì)。克里斯蒂娃指出:“自由的邏輯并不像人們簡(jiǎn)單地認(rèn)為那樣,以為自由就是超越;相反,自由恰恰是開(kāi)始的能力。”所有真正的好母親,就是最善于為孩子留出自由思考的時(shí)間的媽媽。
克里斯蒂娃進(jìn)一步集中研究母親和幼兒的特殊語(yǔ)言,將它們當(dāng)成揭破語(yǔ)言?shī)W秘的主要途徑。母親與幼兒的互通語(yǔ)言是非常奇特的語(yǔ)言使用場(chǎng)域,在其中,母親表面上是向幼兒教會(huì)說(shuō)話,但實(shí)際上,母親卻是“不斷重新學(xué)習(xí)新語(yǔ)言”的角色。克里斯蒂娃說(shuō):“兒童學(xué)習(xí)語(yǔ)言,對(duì)母親來(lái)說(shuō),就是重新學(xué)習(xí)語(yǔ)言,就是對(duì)語(yǔ)言的再學(xué)習(xí)。”。正是在反復(fù)學(xué)習(xí)說(shuō)話的過(guò)程中,母親不斷地將自身提升到新的高度,使自己脫出原來(lái)的主體的約束。人的更新,新生命的獲得,都首先必須從舊的主體中跳出來(lái);都必須在向他人學(xué)習(xí)的過(guò)程中,換句話說(shuō),在使自己成為“他人的他人”的情況下,才能實(shí)現(xiàn)。所以,克里斯蒂娃說(shuō):“我就是始終都懷有試圖跳出原有自我的欲望的人。”
作為“他者”的幼兒,實(shí)際上,已經(jīng)作為存在論意義上的人類原初存在,作為人類社會(huì)和文化的基本因素,產(chǎn)生和孕育于母親體內(nèi)、并自始至終得到母親的身體和精神雙方面細(xì)心滋潤(rùn)哺育而成為一種最基礎(chǔ)的社會(huì)文化關(guān)系的原型。母親對(duì)幼兒的關(guān)系建立在純粹的“愛(ài)”的基礎(chǔ)上。“母愛(ài)”是一切“愛(ài)”的根基,它體現(xiàn)了愛(ài)的“無(wú)條件給予”的本質(zhì)。這種原初的“愛(ài)”是沒(méi)有終點(diǎn),沒(méi)有目的,沒(méi)有功利,沒(méi)有計(jì)算,不計(jì)回報(bào),乃是“付出本身”,因此,它永遠(yuǎn)都“無(wú)所喪失”。
一切人,不管是女還是男,都是由母親生出和變來(lái)的,也是從母親演變而來(lái)。母親從女性的身體和心靈的審美活動(dòng)中形成并不斷鞏固。克里斯蒂娃受到英國(guó)兒科醫(yī)生兼精神分析學(xué)家維尼克特的臨床經(jīng)驗(yàn)和研究成果的啟發(fā),強(qiáng)調(diào)母親同她的孩子之間的原始關(guān)系已經(jīng)深深地包含了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一切因素,同時(shí)也隱含了人的存在的奧秘。
克里斯蒂娃在她的《女性與神圣品》中指出:海德格爾所揭示的“存在的安詳寧?kù)o特征”,恰恰植根于“母與子”的原初關(guān)系中。正是在母親和幼兒的原初關(guān)系中,典型地體現(xiàn)出“人不斷地學(xué)會(huì)使自己成為他者”的最珍貴的原初經(jīng)驗(yàn)。克里斯蒂娃一再地強(qiáng)調(diào):每個(gè)人都必須學(xué)會(huì)使自己異于自己;每個(gè)人都要盡可能地設(shè)想自己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異己者”。也就是說(shuō),如果要學(xué)會(huì)愛(ài)他者,善待別人,就首先必須時(shí)時(shí)體驗(yàn)自己的“異己性”,體驗(yàn)自己處于他人地位時(shí)的真正處境,切身體會(huì)到自己急需別人把自己當(dāng)成“他人”的情景。這一切只有在母親與嬰兒的關(guān)系中才能淋漓盡致地“原形畢露”出來(lái)。
由此出發(fā),人類才有可能進(jìn)行各種創(chuàng)造活動(dòng)。母親就“在那兒”,她原初自然和直截了當(dāng)?shù)嘏c其親子保持共同存在和相互替換的關(guān)系。所以,在簡(jiǎn)單明了的“母親”中,就包含了她自身與“他人”;母親就是“與他人在那兒”的原型。她也是一切區(qū)分的開(kāi)端,是存在和世界的所有差異的“黎明的曙光”。
在母親那里,集中體現(xiàn)了“安詳”、“感激”、“忠誠(chéng)”、“獻(xiàn)身精神”;開(kāi)展行動(dòng)的渴望,恰恰被懸掛在有效的仁慈情懷中。母愛(ài)是一種被推遲和被延緩的性愛(ài),一種出于等候狀態(tài)中的欲望。而就在延緩和等候中,它開(kāi)啟了生命的時(shí)間,也開(kāi)啟了精神心靈的時(shí)間以及開(kāi)啟語(yǔ)言的時(shí)間。所以,母親的存在中所蘊(yùn)含的,是一種無(wú)所認(rèn)識(shí)、無(wú)所意指和無(wú)所區(qū)分的純時(shí)間,在其中,無(wú)所謂“善與惡”、“真與假”的區(qū)分。而且,由于它的包容和慈善本質(zhì),它又悖論地已經(jīng)包含了具有性欲滿足傾向的“父親”成分在內(nèi)。
因此,女人具有高于男性的心理特質(zhì),這就是她們的堅(jiān)韌性、寬容性、仁慈性和創(chuàng)造性。這是她們的高效率創(chuàng)造和生產(chǎn)的精神基礎(chǔ),也是她們?cè)谌祟愇幕a(chǎn)和再生產(chǎn)中的關(guān)鍵地位的先決條件。
(責(zé)任編輯曾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