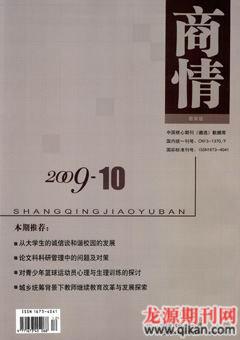讓鏡頭像心靈本身一樣被打動
苗雨青
【摘 要】要想拍出好的攝影作品,就應該首先學會如何去解讀照片。攝影作品鑒賞的形象思維,是審美過程。攝影作品是一種直觀的視覺表現藝術。心的陶冶,心的修養和鍛煉是替美的發見和體驗做準備的。
【關鍵詞】解讀 審美 心靈 感動
學習攝影以來,一直在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問題:好照片的標準是什么?而做了老師開始講授攝影專業課程之后,就更是時常地被同學問到:怎樣才能拍出一張好照片?
就如同先學做人,后學做事一樣,要想拍出好的攝影作品,也應該首先學會如何去解讀照片。攝影作品不同于語言文字作品,它用畫面來表現主題,攝影師通過鏡頭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圖片用形象發言,有著語言文本所沒有的視覺沖擊力。而且,同語言文字相比較,一幅照片可以被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人們所理解,它是一種世界性的通用語言。那么,要學會了解圖片的相關背景,盡可能準確地解讀圖片的內涵,通過畫面了解事實真相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一種交流手段。關于怎樣才算是好照片的問題,若僅僅從技術上、規律上、理論上加以系統地分析,應該說還是能夠相對地說明白的。比如說,照片中是否主體聚焦和曝光是否正確、背景聚焦是否清楚、主體和背景的顏色看上去是否自然、主體在照片中的位置是否做到特別吸引人、圖片所要表達的或是所要的視覺沖擊力是否得以充分地表現、照片的景深表達又是否完善了畫面,……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可以讓我們通過照本宣科的手段去毫無生趣地解讀一幅照片,但是,這又有什么意義呢,這僅僅只是停留在觀看的層面上,要真正地去品評一張照片的好與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學會去鑒賞它,要去用心感受他,要去試著讀懂她。
攝影作品的鑒賞的形象思維,是審美過程。攝影作品是一種直觀的視覺表現藝術。對任何藝術作品的鑒賞都是一項復雜的審美活動,它的實質是形象思維。對攝影作品的鑒賞也不例外。攝影構思與意圖固然重要,但不能夠以生動的圖像形式表現出來,再好的構思與意圖也沒有用途。在圖像語言中,熟練清晰的表達同語言寫作中的清晰表達一樣重要。掌握自己創作手段的象征符號是成功的關鍵。就如同作家在創作中的象征符號是詞匯一樣,攝影者在拍攝時也擁有自己獨特的象征符號,我們在鑒賞任何一件攝影作品時都會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光線、色彩、構圖等,即,攝影者在攝影技術上的妥善處理;攝影作品內含有的作者的個人意志與性格以及表現對象的直觀外形與內在精神的關系。
我們姑且先將攝影的美放置一旁,而先看看美學名家宗白華老先生對其追尋美的一些感悟:
“啊,詩從何處尋?
在細雨下,點碎落花聲,
在微風里,飄來流水音,
在藍空天末,搖搖欲墜的孤星!” ——(《流云小詩》)
在這里,我們看到,詩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藝術的美,一是自然的美。可是,細雨、流水、藍天、孤星這些都只是外界事物的客觀現實,我們大多的人每天經歷著這些卻置若罔聞、無動于衷,這些人以為這些事物就應該是這樣的存在著,殊不知,這是上天恩賜給我們人類特有的美麗,因為,對美好事物的感受,只有我們人類才能夠擁有。在法國導演菲利浦慕勒執導的電影《蝴蝶》中,有一種名為“伊莎貝拉”的蝴蝶,它只有3天3夜的壽命,它藍綠色的雙翅璀璨無比,它用自己有限的生命盡展其美倫美幻的美麗。3天3夜,它相對于人類來說,太短暫了,而人類呢,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壽命,在浩瀚的宇宙面前,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影片中的小主人公8歲的麗莎有問不完的問題,她的“兒童邏輯”非常簡單,例如:為什么情侶要親吻?因為鴿子們咕咕叫;為什么漂亮的花會凋謝?因為那是游戲的一部分;為什么木頭會在火里燃燒?是為了我們像毛毯一樣的暖;為什么狼要吃小羊?因為他們也要吃東西;為什么太陽會消失?為了地球另一邊的裝飾;為什么我們的心會滴答?因為雨會發出淅瀝聲?;為什么你要我握著你的手?因為和你在一起,我感覺很溫暖……我們可以看到,國學大師宗白華老先生和8歲的麗莎一樣的幸運,他們擁有著多么美好的語言、多么輕靈的思緒、多么幸福的心靈。
每一種藝術表現手段都需要某些機械輔助設備,就好比畫家的畫筆或文學創作中的電腦打字,攝影作為一種非語言表現手段,并非比繪畫或文學創作“機械”多少,它也僅僅是利用相機記錄影像的功能表達出有形的畫面及無形的思考。攝影者不應該把攝影僅僅當作謀生的唯一方法,而應該在意識到攝影手段潛力的基礎之上,努力改進自己的工作方式,明確自己的見解和理論,為作品構思、選擇被攝體與方法并最終確定自己獨有的表現形式表現出有深刻意義的具體形象。形象不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形式中每一個點、線、色、形、音、韻,都表現著內容的意義、情感、價值。自己住在現實生活里,沒有能夠把握它的美的形象。等到自己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相當的距離,從遠處來看,才發現家在畫圖中,溶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詩人華滋沃斯曾經說過:“一朵微小的花對于我可以喚起不能用眼淚表達出的那樣深的思想。達到這樣深入的美感,發見這樣深度的美,是要在主觀心理方面具有條件和準備的。美的蹤跡要到自然、人生、社會的具體形象里去找。但是心的陶冶,心的修養和鍛煉是替美的發見和體驗做準備的。創造“美”也是如此。捷克詩人里爾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隨筆》里有一段話精深微妙,“……單要寫一句詩,我們得要觀察過許多城許多人許多物,得要認識走獸,得要感到鳥兒怎樣飛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的姿勢。得要能夠回憶許多遠路和僻境,意外的邂逅,眼光觀望它接近的分離,神秘還未啟明的童年,和容易生氣的父母,當他給你一件禮物而你不明白的時候(因為那原是為別一人設的歡喜)和離奇變幻的小孩子的病,和在一間靜穆而緊閉的房里度過的日子,海濱的清晨和海的自身,……可是單有記憶猶未足,還要能夠忘記它們,當它們太擁擠的時候,還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們回來。因為回憶本身還不是這個,必要等到它們變成我們的血液、眼色和姿勢了,等到它們擁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別于我們自己了,那么,然后就可以希望在極難得的頃刻,在它們當中伸出一句詩的頭一個字來。”這里是大詩人里爾克在許許多多的事物里、經驗里,去蹤跡詩,去發現美的話語。同樣的,這樣的一段話又是多么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攝影創作的精髓所在。
在茫茫的宇宙中,若沒有一顆純真的摯愛之心,又如何能夠感知這滋潤萬物的光芒,你的心又怎么能夠因愛與美的融合而產生出巨大的創造力。讓我們再次回到攝影鏡頭前,那么,你在自己的心里聽到“麗莎”的聲音了嗎?你在你的鏡頭前看到那翩翩起舞的“伊莎貝拉”了嗎?如果你聽到了、看到了、感受到了,就請快一些,快一些舉起你的鏡頭吧,因為,此刻,它也正如你的心靈一般被深深地感染著、打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