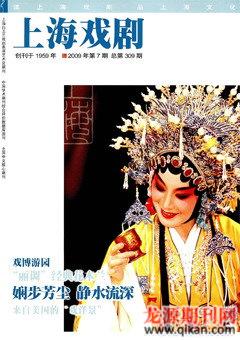一座令人失望的《櫻桃園》
吳曉鈞
記不清是誰說過:“有一百個導演,就有一百座《櫻桃園》。”
作為契訶夫絕筆之作的《櫻桃園》,不僅是劇作家全部創作思想和藝術的總結,也是他的最為復雜的一部作品。復雜,主要體現在主題思想的多義性、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和模糊性,如何理解劇作的喜劇性以及對其的把握與體現。總之,劇作為舞臺二度創作提供了寬闊深廣的多元化闡釋空間,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此,契訶夫早有預見,他認為自己的劇作“從誤解開始,以誤解結束,這就是我的戲的命運”。
作為“林兆華作品”的《櫻桃園》,雖然具有其一貫的先鋒精神和鮮明的創作個性,卻是一座令許多觀眾,甚至包括曾經喜歡“大導”作品的人感到失望的《櫻桃園》。
首先是人物形象的單一化。這與林兆華的指導思想有關。林兆華認為:“在這個戲中,思想和性格相比,我認為主要是表現思想。我不要性格的細節。”所以在戲中,當柳鮑芙證實了櫻桃園已被拍賣之后,她躺倒在地哭喊翻滾。此時,演員蔣雯麗在臺上聲嘶力竭,還哪像是個曾在巴黎生活過的貴族,分明是電影《立春》中一心想要進入京城成為歌唱家,在目的未果后尋死覓活的縣城教師王彩玲的形象。這一幕中,還有一個使人別扭之處,就是羅巴辛在獲得櫻桃園之后的張揚,表現為活脫脫一個暴發戶似的鄉鎮企業家的腔調。可能是導演太想讓這一人物“為當下中國的觀眾服務”了,卻不知在羅巴辛的內心深處,他是對這位女貴族懷有某種特殊而微妙的情感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他一直婉拒著柳鮑芙的義女瓦里雅的愛情。
其次是人物形象體系的簡單化。契訶夫戲劇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多主人公”或是“無主人公”,《櫻桃園》也是如此。全劇有名有姓的12個人物(林兆華刪減了2人),從根子上講是兩個群體——個是貴族、地主,是被人侍候的;另一個是侍候人的,或是過去,或是現在,或是其長輩。但契訶夫絕不是表現他們之間的對立,而是以“有其主,必有其仆”的諺語,通過仆人來反映主人,以主人和仆人的共同點來揭示人的本性和本質,包括不同階級、不同層次、不同身份的人在新舊交替之際所面臨的困惑與痛苦,以及所暴露出來的人性弱點。正像文學批評家雷蒙-威廉斯所言,契訶夫戲劇結構的真正獨創性在于“不是怎樣戲劇性地解決單一個人的命運,而是如何協調人們對共同命運的不同反應”。(《現代悲劇》)但林兆華卻弱化了形象體系的整體性,主觀地將整體性集中在所謂三種文明人的代表身上——即沒落的貴族柳鮑芙、新興的資產階級羅巴辛和理想主義者彼嘉,并強化了他們各自的個人體驗。于是,那個具有荒誕色彩和生活哲理的女家庭教師夏綠蒂(這一人物是契訶夫為其妻子奧爾加寫的)不見了;俄羅斯文學中具有經典性的奴才形象之一的雅沙和自命不凡的女仆杜尼雅莎一起成了“活寶化”的人物;具有雙重身份的瓦里雅大多數時間里總是板著臉直著嗓子:那個老是涎著臉借錢,自稱祖先是“種馬”的地主皮希可咸了來無蹤、去無影的達申卡父親;作為舊俄時代標志人物的老費爾斯形象被模糊了,尤其全劇最后那個畫龍點睛之筆,也被處理成了地底下的呢喃……
《櫻桃園》與契訶夫的其他劇作的結構相比,有~個明顯的不同。那就是它有一個全劇性的主要事件一拍賣櫻桃園。不過,契訶夫劇作的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的——仍然不是表現事件的本身,而恰恰是表現事件對人物的心理、情緒以及生活狀態的影響。因此,契訶夫還是堅決地將事件推到了幕后。但林兆華卻將幕后的事件摳了出來,硬是將其推到舞臺的強光燈下,而且將人物逼到其跟前加以烘烤,使其發出強烈的直感。上文提到的第三幕,就是實例。其實,就是現在第四幕中被部分評論所稱道的一些舞臺語匯,也是對櫻桃園拍賣這一事件直接感受的外在表現。另有一處也很能說明問題——對于柳鮑芙的兒子格里沙溺死的情節,契訶夫是僅將其作為“戲外的”事件、前史來處理的。但林兆華卻將其放大了,不僅在說明書里提到了那條河,而且劇中幾次讓柳鮑芙在臺口仿佛對著那條河講述著“格里沙之死”。就這樣,契訶夫營造的平淡生活的詩意被無情地打破了。
但林兆華畢竟是林兆華,在他的《櫻桃園》里還是有使人感到新鮮和閃光之處的。比如“永遠的大學生”彼嘉的出場,就很有特點,他從舞臺的頂層鉆出來,然后跨在懸于半空的梯子上。這一亮相的設計,極其準確地抓住了彼嘉的形象本質——這是一個不切合實際、不能腳踏實地的人物,是一個“漂蕩”的形象。又如音樂的整體構思既單純又比較符合契訶夫劇作特有的詩意抒情喜劇的風格。尤其全劇結尾時那一陣著名的“斧子砍伐樹木的聲音”被林兆華砍掉了,林兆華稱自己“不忍聽到那殘酷的聲音”,而是將單一的鋼琴聲取而代之。但這樣做同樣能使人聯想起斧子的砍伐聲。這一處理倒是加深了人們對蕭伯納的那句著名評價的認識——在《櫻桃園》里,“契訶夫的手段比易卜生柔和,所以也更為毒辣”。
林兆華的《櫻桃園》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當下,對像《櫻桃園》這樣的經典劇目,我們應以何種方式讓其與觀眾見面?
曾有一說,西方人是通過看戲認識契訶夫的,而中國人則是通過讀小說知道了契訶夫。此說絕非虛言。就以《櫻桃園》為例,據統計,該劇是在問世35年之后的1939年才由一家俄僑俱樂部在上海首次搬上舞臺,從那時起到現在的70年問,該劇在我國僅上演了7次,也就是說平均10年才演出一次,且只是在京、滬兩地。由此可見,中國觀眾對契訶夫的《櫻桃園》的熟悉程度,遠遠不及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和《哈姆雷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等外國名劇。在相當多的中國觀眾對《櫻桃園*這樣一部極為復雜的劇作還很不熟悉、不甚了解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實驗、革新甚至顛覆,是否合平時宜?在沒有比照的情況下,它是否會使觀眾以為契訶夫的戲劇藝術、契訶夫的《櫻桃園》就是這樣的?
隨之而來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應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櫻桃園》?這部巔峰之作是契訶夫蘸著自己生命的燈油創作的。當時他已處于肺結核的晚期,有時一天只能寫兩行字;一度不僅停止寫作,甚至連口述也難以進行。與此同時,他還要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和壓力——妻子奧爾加與妹妹的姑嫂之爭;斯坦尼和丹欽科或通過奧爾加,或直接寫信給契訶夫頻頻催稿,奧爾加更是常常站在正在寫作的契訶夫的身后直接督促。就在謄寫草稿時,契訶夫又失望了——對話的處理、人物的心理分析不當,顯得過于冗長。于是他又重寫了某些段落。劇本發出之后,盡管先后收到丹欽科和斯坦尼發來的對他贊美有加的電報,但契訶夫擔憂“莫藝”會強行安排一些他不喜歡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