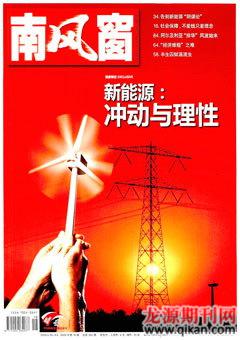理性看待新能源
楊 軍
新能源是發展方向,是未來的希望,也許有一天它會是新的一輪經濟起飛的引擎,但是現在還不是,它還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護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長,妨礙了它的大好前程。
新能源要發展壯大,關鍵是技術突破。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即使國家的財政支持再多,產業也不會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目前的技術研發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落后,當然這跟我們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比較弱有關系。世界經濟陷入陰霾,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能源聚焦了太多目光,也被賦予了太重的使命,這些是新能源產業能背負得了的嗎?本刊記者特意走訪了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俊峰。
新能源無力讓經濟走出低谷
《南風窗》:在金融危機下步步后退的世界經濟似乎把新能源當成了救命稻草,美國新復興計劃的核心是培植新技術和產業,特別是新能源。歐盟各國為了強化其在新能源領域已經獲得的相對優勢,也進一步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中國、印度等很多國家也把新能源放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有這樣一種說法,新能源的發展可能會引發第四次技術革命。新能源被認為是帶動世界走出本次經濟危機的領頭產業,新能源能否擔此重任?
李俊峰:與歐盟的綠色能源計劃相比較,奧巴馬的能源新政其實并沒有新意,但是它卻在我國國內形成不大不小的沖擊波。有不少經濟、科技和能源的“三棲”名人將其比喻為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和克林頓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提出了所謂引導論,鼓吹每次危機都會發生一些技術革命,都會誕生一些新的技術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危機的觀點,提出了“新能源技術革命可能是引領本輪世界經濟走出危機的靈丹妙藥”的高論。我不知道哪次危機是靠技術走出來的,金融危機還是得由經濟學家們多想想辦法。人們常說“頭疼醫頭”不對,但頭疼總不能醫腳吧。
發展新能源也不是美國浪潮,中國對發展新能源一直比較重視,目前中國光伏發電占世界40%,風電僅次于美國。中國是德國之后第二個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的國家,很多政策都是在國際上也比較先進的。中國在新能源方面政策還是比較連續的,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出臺了一些相應的政策。第一階段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是為了解決農村能源問題,提出發展沼氣和小水電,一直延續到80年代。第二階段到90年代末期,是為了改變能源結構,解決能源多樣化問題。第三階段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因為從90年代末期開始,節能減排和大氣污染壓力越來越大。
大家把新能源看得過高,能源是經濟問題中的一部分,新能源又是能源問題中的一部分,依靠一部分中的一部分去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危機不容樂觀。發展的東西都是充滿不確定性的,看不清楚,變化的東西太多了,我們現在的認識都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現在新能源技術,還處在弱小的發展階段,不可能承擔大任。能源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大約為6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世界各國國民生產總和的10%左右,新能源占能源的10%,也就是說,目前新能源只占到世界經濟的1%。媒體喜歡用新能源革命,但是還沒到那個時候。即使現在一年增長100%,新能源也還不是主流。
新能源是發展方向,是未來的希望,也許有一天它會是新的一輪經濟起飛的引擎,但是現在還不是,它還很弱小,很幼稚,需要呵護和扶持,而不是拔苗助長,妨礙了它的大好前程。目前國內新能源占的比重很小,產業規模也很小,太陽能發電全國不到20萬千瓦,風電1200萬千瓦,電網接收能力、儲能等遠遠不夠。我們規劃到2020年,才占15%,到2030年占20%,到2050年占30%。如果按這個時間表做到,已經很了不起了。
新能源發展前景不是無限的
《南風窗》:前段時間有人說中國的風電裝機40%不能上網,影響了新能源的發展,而這是因為技術和政策問題,是這樣嗎?
李俊峰:這種說法是不對的。盡管許多能源企業遭遇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是我們的企業總體看來還是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國政府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制定好了許多的行業政策,鼓勵和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比如說2005年頒布的《可再生能源法》,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的幾個為新能源行業立法的國家之一。在這個立法之后,又陸續出臺了10多個細則,涵蓋上網電價、太陽能光伏補貼,新能源項目特許權招標等多方面。
新能源問題雖然被整個社會重視了,但是由于可再生技術本身的特征,要讓社會完全接受還有一定的距離。比如說太陽能,有陽光才能發電,沒有陽光就不能發電;風電也是一樣,高度依賴自然條件。這種情況下就要電網去適應它,接納它。現在的電網建設不論政府還是企業都高度重視,希望電網能夠做好接納新能源發電的一些準備。
先澄清一個問題,過去認為中國電網落后,其實我們的發電裝機容量和發電量僅次于美國,大部分設備是新增的,一半以上的電網是2005年以后建立的,還很新。而日本電網是上世紀80年代建立的,美國是60年代末,歐洲是70年代末,相比之下,中國是很年輕的電網,用了最先進的技術。所以,技術上不存在風力發電上不了網的問題。
并網的問題有兩個原因,一是《可再生能源法》有缺陷,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的規定,像國家電網、南方電網這樣的電網企業,應該全額收購其電網覆蓋范圍內的可再生能源并網發電項目的上網電量,并提供上網服務。但我國的風能資源大部分分布在偏遠地區和海上,離大城市密集區和負荷中心遠,風電大多不在電網覆蓋地區。
二是當初誰也沒想到風電發展會如此迅速,制定規劃的時候一年風電只有50萬千瓦,當時覺得5年增長10倍,到500萬千瓦已經是很快的速度了,沒想到2007年就達到了600萬千瓦,2008年則達到1200萬千瓦。按照原來國家風電的建設規劃,電網是到2010年能接受1000萬千瓦風電。因為在現實執行中存在困難,有一些個別的地區風電上網和外送有困難,例如蒙西地區,東北電網等,由于發展快,布局集中,所以大家希望政府和相關企業更應該加強統籌布局,有計劃地發展,防范一頭過熱、一頭過冷的失衡現象。
另外,應該澄清的是,過去說的1200萬千瓦的裝機只有800多萬千瓦并網是一個誤解,可再生能源發電并網的正常程序也需要約三個月的時間,調試要兩個月的時間。調試完了再驗機,需一個月。在驗收合格前不能并網是正常的。吊裝完成的容量和實際并網發電的容量有差別是正常的。
《南風窗》:解決了這些問題,在中國新能源是否就會像現在人們希望的那樣迅速發展起來?
李俊峰:首先,世界能源市場有限,一旦某種裝備建成之后經濟壽命是20年左右,
技術壽命更長一些,例如中國的電廠大都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新能源短期內很難對其進行替代,新能源發展的最大市場空間是新增容量。
同時,還要認識到,當前條件下新能源的發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市場容量是政府政策提供的,即使某一天各種新能源變得具有市場競爭力,其市場容量也是有限的,不僅新能源技術之間相互競爭,還要面對傳統能源低碳化技術的強有力競爭。例如同類中的太陽能不僅要與風電、水電、生物質發電競爭,未來還要與帶有CCS(碳捕獲和封存技術)的燃煤和燃氣發電競爭。大量發展風電、太陽能等間歇式的能源,還要有儲能技術和系統的支持以及電網調度技術和系統的改革,也就是大家所說的“智能電網技術”的支持。
簡言之,近期不考慮氣候變化的因素,新能源發展市場空間取決于政府政策,而未來的發展取決于各類新能源技術之間的相互競爭及其與CCS技術的競爭。中遠期的未來(大約50—100年之內)新能源發展成本的上限是帶有CCS裝置的燃煤和燃氣發電技術。新能源的發展前景是廣闊的,但并不是無限的。對新能源的認識要回歸理性。
關鍵是掌握核心技術
《南風窗》:除去籠罩在新能源產業上的光環和泡沫,對新能源產業來說,要想健康地發展起來,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俊峰:新能源要發展壯大,關鍵是技術突破。像對于國內光伏產業來說,目前面臨的最大瓶頸就是技術無法真正突破而導致成本過高,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即使國家的財政支持再多,產業也不會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國目前的技術研發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落后,當然這跟我們整個國家的創新能力比較弱有關系。
隨著新能源發展熱潮的興起,各地政府也紛紛出臺各自的新能源發展規劃,一批新項目迅速上馬,但是相關的質量保證體系卻遲遲沒有出臺。目前新能源產業迫切需要的兩個標準,是新能源類產品本身的質量認證體系,另一個則是新能源電力入網的接入標準。
如果沒有加以很好的引導,難免會造成新能源產業的產業鏈盲目集中于技術含量不高的個別環節,造成局部的產能過剩、全行業整體競爭力上不去的問題。因此,我們希望這些部門和企業,都應該在技術研發方面有更多的投入。現在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很弱,沒有國家的研發團隊,新能源產業的關鍵技術、材料和裝備都依賴進口,連生產線都靠進口。
《南風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三資企業的興起,中國自主研發創新技術越來越少,在很多重要領域都不掌握核心技術,如何確立中國新能源產業在世界中的位置,使新能源產業得到良性發展?
李俊峰:在長期發展的規劃中,應當通過政府的扶持,建立一系列大型的國家實驗室和服務社會的研發機構、技術中心、試驗平臺,以此突破新能源產業現有的核心技術瓶頸。研究人員不養了,全世界沒有這樣做的。像德國有弗朗霍夫研究院,美國能源部下面有十幾個實驗室等等。這些研究人員是為全社會服務的,不是為一家企業服務。
而中國在能源領域除了我們研究宏觀政策層面的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沒有一個國家的或者是為社會服務的能源研究所了。原來一些出名的比較大的能源類研究院所都歸了企業。石油科學院歸了中石油,核能研究的院所劃歸了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中國電力科學院歸了國家電網等等。一堆研究院所都是依附于企業。這些屬企業所有的研究院所不可能服務整個社會,失去了國家研究機構本來的功能,比如中國電力科學院,當然只聽國家電網公司的。
不管國家財政出錢也好,私人基金也好,中國需要為社會服務的研究所。比如,像美國的聯合技術,不僅為美國企業服務,也為世界各國的企業提供技術服務。我們有數不清的國家實驗室、國家研究中心,但是,就是缺為全社會服務的研發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