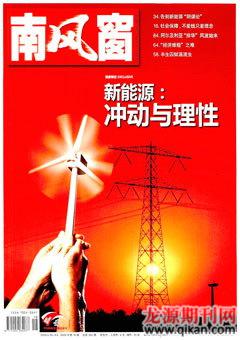阿爾及利亞“排華”風(fēng)波始末
陶短房
一些到非洲“淘金”的中國(guó)人認(rèn)為非洲落后、非洲人“原始”,不屑和當(dāng)?shù)厝私慌笥眩膊辉概c當(dāng)?shù)厣鐣?huì)發(fā)生太多交集,這不僅容易在溝通時(shí)產(chǎn)生誤會(huì),目一旦,“孤立事件”爆發(fā),也會(huì)妨礙彼此的協(xié)調(diào)解決,更會(huì)給某些極端勢(shì)力和別有用心者提供挑撥離間的機(jī)會(huì)。
當(dāng)也時(shí)間8月3日午后,在北非國(guó)家阿爾及利亞的首都阿爾及爾市郊,爆發(fā)了少數(shù)中國(guó)人和當(dāng)?shù)厝碎g的群體沖突。
這場(chǎng)被某些媒體稱(chēng)為“排華”,而被另一些媒體渲染為“中國(guó)僑民尋釁”的風(fēng)波,盡管事件旋即平定,人員傷亡和物質(zhì)損失也并不嚴(yán)重,卻在倏忽之間驚動(dòng)天下。8月6日,中國(guó)駐阿爾及利亞大使館發(fā)表聲明,將事件定性為“不影響中阿雙邊友好關(guān)系”的“孤立事件”,這一定性迅速得到阿爾及利亞政府的認(rèn)同。
事件的來(lái)龍去脈
據(jù)阿爾及利亞《庫(kù)巴敘事報(bào)》報(bào)道,沖突發(fā)生在阿爾及爾郊區(qū)埃蘇亞區(qū)(BahEzzouar)一個(gè)被俗稱(chēng)為“中國(guó)城”(Chnaoua)的街區(qū)。當(dāng)時(shí)一名中國(guó)人將車(chē)停在當(dāng)?shù)厝税⒉级艩柨死锬?s Abdelkrim)的家電商店附近,自己到附近商店購(gòu)物,引發(fā)后者不滿(mǎn)。據(jù)阿布杜爾克里姆對(duì)記者稱(chēng),當(dāng)時(shí)雙方發(fā)生口角和爭(zhēng)執(zhí),中國(guó)人對(duì)他進(jìn)行了“言辭侮辱”,雙方發(fā)生“推搡和揪扯”,后被他人拉開(kāi),中國(guó)人開(kāi)車(chē)離去,他“以為事情已過(guò)去”,但幾小時(shí)后,那名中國(guó)人帶著50多個(gè)同胞“手執(zhí)鐵棍和刀”毆打店主和在店里的其他人。阿布杜爾克里姆被打得滿(mǎn)臉鮮血,一名叫卡德?tīng)柕漠?dāng)?shù)厝耸直郾豢硞凇盎鞈?zhàn)”中當(dāng)?shù)厝斯灿?人受傷,傷者被送往當(dāng)?shù)刈畲蟮乃_利姆-茲米爾利醫(yī)院。而該國(guó)中央電視臺(tái)稱(chēng),當(dāng)時(shí)有60名以上阿拉伯人對(duì)中國(guó)人動(dòng)了手,法國(guó)《巴黎人報(bào)》則稱(chēng)阿拉伯人隨后攻劫了一些中國(guó)人的店鋪。
阿爾及利亞當(dāng)?shù)貓?bào)紙和電視臺(tái)均未報(bào)道中國(guó)人的傷亡情況,也未說(shuō)明究竟是誰(shuí)先動(dòng)手,但阿布杜爾克里姆曾對(duì)路透社記者承認(rèn)是“先給了中國(guó)人一拳”。《庫(kù)巴敘事報(bào)》的報(bào)道稱(chēng),中國(guó)人“后來(lái)躲入一家店鋪避難”并“要求中國(guó)大使館庇護(hù)”。而法國(guó)《巴黎人報(bào)》的報(bào)道則援引中國(guó)大使館方面的信息稱(chēng),中方有十多人受傷,5家店鋪被搶劫。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近年來(lái)阿爾及利亞大量基建工程上馬,許多中國(guó)公司中標(biāo),加上不少中國(guó)人來(lái)此經(jīng)商,據(jù)法新社的估計(jì),中國(guó)人在埃區(qū)總數(shù)已達(dá)3.5萬(wàn)以上。據(jù)《阿爾及爾自由報(bào)》的文章稱(chēng),埃蘇亞區(qū)由于中國(guó)商戶(hù)越來(lái)越多,當(dāng)?shù)鼐用駥?duì)該區(qū)“太多的亞洲人”感到越來(lái)越不滿(mǎn)和憤怒。一些居民對(duì)媒體抱怨,這些亞洲人“胡作非為,不尊重當(dāng)?shù)亓?xí)俗”,他們“玩女人,喝葡萄酒,赤膊或穿背心在馬路上行走”,和當(dāng)?shù)厝四Σ猎絹?lái)越多。雖然此前類(lèi)似此次的惡性械斗極少發(fā)生,但某些激進(jìn)分子早已在網(wǎng)絡(luò)上鼓吹“讓亞洲人滾出阿爾及利亞”,而一些對(duì)中國(guó)人的蔑稱(chēng),如“食貓者”(穆斯林是不許吃貓肉的)、“阿里巴巴”(意即“小偷”)早已連小孩子都能喊出。
事件發(fā)生后,當(dāng)?shù)鼐W(wǎng)站出現(xiàn)了一些極端的聲音,如“殺死中國(guó)人”、“對(duì)亞洲人打一場(chǎng)新的解放戰(zhàn)爭(zhēng)”,一些人在網(wǎng)上將中國(guó)人稱(chēng)為“黃禍”,攻擊中國(guó)人“褻瀆穆斯林的土地”、“承繼西方殖民者衣缽”等等。許多傳媒在敘述械斗時(shí)只說(shuō)中國(guó)人動(dòng)手,不說(shuō)當(dāng)?shù)厝耍诿枋鍪軅闆r時(shí)卻只說(shuō)當(dāng)?shù)厝耸軅瑢?duì)中國(guó)人只字不提。盡管阿布杜爾克里姆在入院前便坦承“自己先動(dòng)手”,但當(dāng)?shù)孛襟w最初幾無(wú)例外地選擇性無(wú)視。幾家阿拉伯語(yǔ)網(wǎng)站和個(gè)別報(bào)紙將阿布杜爾克里姆滿(mǎn)臉鮮血的照片放在醒目位置,甚至放大至一個(gè)整版,一度令氣氛激化。
8月6日,中國(guó)駐阿大使館一方面敦促阿方盡快查明真相,一方面表示將給予埃蘇亞區(qū)一定“額外幫助”,得到阿官方認(rèn)同。部分阿官方媒體開(kāi)始更客觀地報(bào)道事件,逐漸冷靜下來(lái)的當(dāng)?shù)厝艘查_(kāi)始在網(wǎng)站上反思,并檢討“狹隘排外情緒”。當(dāng)事人阿布杜爾克里姆表示,當(dāng)事的中國(guó)商人已主動(dòng)要求協(xié)商和解,一度揚(yáng)言要“起訴”或“請(qǐng)求政府下令驅(qū)逐華人的一些當(dāng)?shù)厝藞F(tuán)體也偃旗息鼓。盡管8月6日當(dāng)天,當(dāng)?shù)匕⒗Z(yǔ)《埃爾卡巴爾報(bào)》稱(chēng),在距阿爾及爾80公里的一個(gè)中國(guó)筑路公司生活營(yíng)地發(fā)現(xiàn)炸彈,基地組織北非分支“伊斯蘭馬格里布”也試圖借機(jī)生事,但事態(tài)仍迅速得到控制和平息。
異乎尋常之處
近年來(lái)隨著走出國(guó)門(mén)的中國(guó)人、中國(guó)公司和項(xiàng)目與日俱增,“排華”事件時(shí)有耳聞,但此次阿爾及爾發(fā)生的事,卻有不少令人矚目的異乎尋常之處。
首先,以往“排華”事件,多為當(dāng)?shù)厝藝トA人,而華人基本處于逃避、受害的純被動(dòng)地位;此次阿爾及爾事件中,雖然對(duì)方也承認(rèn),是當(dāng)?shù)厝讼葎?dòng)手,但事件卻是因雙方的同時(shí)不冷靜而猝發(fā),且在沖突當(dāng)中,中國(guó)人同樣動(dòng)了手。
其次,以往在類(lèi)似事件中,中國(guó)人、尤其中國(guó)小商人很少抱團(tuán),此次事件中卻出現(xiàn)幾十名中國(guó)人“并肩上陣”的景象,連當(dāng)?shù)厝硕几械绞衷尞悺?/p>
此外,自始至終,這些中國(guó)商人都沒(méi)有如以往類(lèi)似事件中慣常的做法一般,用錢(qián)或關(guān)系,尋求當(dāng)?shù)卣母深A(yù)或“私了”。法新社的報(bào)道稱(chēng),他們?cè)谏啼伇还ソ俚牡谝粫r(shí)間就請(qǐng)求中國(guó)使館干預(yù)、保護(hù),事態(tài)初步平息后又主動(dòng)找到對(duì)方當(dāng)事人,尋求溝通和調(diào)解。
更引人矚目的是,當(dāng)?shù)貥O端勢(shì)力和“伊斯蘭馬格里布”恐怖組織的介入和企圖渾水摸魚(yú)。以往的類(lèi)似事件,其背后盡管有時(shí)也有極端組織的影子,但此次卻直接和“基地”組織掛上鉤,且被對(duì)方刻意與新疆7·5事件相聯(lián)系,試圖將事件擴(kuò)大化、政治化、國(guó)際化。
孤立事件中的非孤立因素
從上述描述可知,這次阿爾及爾風(fēng)波的確是孤立事件,甚至很難將之形容為一次“排華”事件,但孤立事件中,卻有不少非孤立因素。
許多當(dāng)?shù)孛襟w都指出,幾名商人間的沖突被瞬間放大為族群事件,和大量中國(guó)建筑工人、商人擁入當(dāng)?shù)兀町?dāng)?shù)厝擞X(jué)得飯碗被奪有關(guān)。
在阿爾及利亞和許多非洲國(guó)家,法律規(guī)定外國(guó)工程項(xiàng)目必須雇用一定比例的當(dāng)?shù)毓と耍捎诋?dāng)?shù)毓と怂刭|(zhì)和工作效率較低,且在中方看來(lái)“不聽(tīng)招呼”、不便管理,因此經(jīng)常繞過(guò)法律條文,超額雇用中國(guó)勞工。如在阿爾及利亞,住房部(AADL)招標(biāo)項(xiàng)目規(guī)定當(dāng)?shù)赜霉け壤坏玫陀?0%,但許多中國(guó)中標(biāo)項(xiàng)目,所用中國(guó)勞工比例都達(dá)到80%,甚至90%。非洲是平均失業(yè)率最高的大洲,這類(lèi)做法雖有一定苦衷,但客觀上卻危及當(dāng)?shù)厝说母纠妫轻j釀一個(gè)個(gè)“孤立事件”的普遍性溫床。
中國(guó)商人的大量擁入,為當(dāng)?shù)貛?lái)價(jià)廉物美、品種豐富的商品,總的來(lái)說(shuō)是很受歡迎的,但在經(jīng)營(yíng)中存在低價(jià)傾銷(xiāo)、以次充好、盲目上量和破壞當(dāng)?shù)劁N(xiāo)售網(wǎng)絡(luò)的行為和現(xiàn)象,對(duì)當(dāng)?shù)厣虘?hù)構(gòu)成較大威脅。此次發(fā)生沖突的埃蘇亞區(qū),幾年間中國(guó)商戶(hù)如雨后春筍般增多,而當(dāng)?shù)劁亼?hù)卻有不少難以為繼而關(guān)門(mén),這種現(xiàn)象在非洲許多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出現(xiàn),一旦因某些偶發(fā)因素產(chǎn)生沖突,便有可能引發(fā)平時(shí)積郁的宿怨,“新賬老賬一起算”,最終小故釀成大端。
許多當(dāng)?shù)厝硕贾赋觯舜伟LK亞區(qū)“排華”情緒之所以一點(diǎn)就著,和中國(guó)人不尊重當(dāng)?shù)仫L(fēng)俗有關(guān)。由于許多到非洲“淘金”的中國(guó)人對(duì)當(dāng)?shù)厍闆r并不十分了解,且不同程度存在著“以我為主”、把國(guó)內(nèi)做法帶到當(dāng)?shù)氐牧?xí)慣。一些中國(guó)人認(rèn)為非洲落后、非洲人“原始”,不屑和當(dāng)?shù)厝私慌笥眩膊辉概c當(dāng)?shù)厣鐣?huì)發(fā)生太多交集,這不僅容易在溝通時(shí)產(chǎn)生誤會(huì),且一旦“孤立事件”爆發(fā),也會(huì)妨礙彼此的協(xié)調(diào)解決,更會(huì)給某些極端勢(shì)力和別有用心者提供挑撥離間的機(jī)會(huì)。
傳統(tǒng)上,中國(guó)企業(yè)、項(xiàng)目在非洲習(xí)慣于用“封閉式管理”來(lái)避免類(lèi)似事件發(fā)生。但隨著中非經(jīng)濟(jì)交往的多層次化,許多類(lèi)似此次埃蘇亞區(qū)這樣、由大量民間小商人構(gòu)成的中國(guó)社區(qū)開(kāi)始出現(xiàn),他們和當(dāng)?shù)厝穗s居、共生,呼吸相通,雞犬相聞,“封閉式管理”根本行不通。當(dāng)?shù)貢r(shí)事網(wǎng)絡(luò)日?qǐng)?bào)TSA事后曾感慨,中國(guó)大使館要求阿方保護(hù)中國(guó)商人的安全“非常合理”,但由于中國(guó)商人散處社區(qū),難度很大,而這些商人缺乏組織,又讓當(dāng)?shù)厣鐖F(tuán)調(diào)解、溝通的嘗試顯得甚為吃力。如何在這些松散的僑民、商戶(hù)中建立相應(yīng)的組織,如何協(xié)助這些“體制外僑民”更好地了解、適應(yīng)當(dāng)?shù)厣鐣?huì),是有關(guān)方面必須深思的。
8月6日,中國(guó)駐阿使館啟動(dòng)“樹(shù)立海外中國(guó)公民文明形象宣傳月”活動(dòng),并向僑民發(fā)放了《海外中國(guó)公民文明指南》和《中國(guó)公民安全海外常識(shí)》,受到當(dāng)?shù)剌浾摵蜕鐓^(qū)的好評(píng)。然而必須認(rèn)識(shí)到,避免形形色色的“孤立事件”,僅做這些尚遠(yuǎn)遠(yuǎn)不夠,必須善于從“孤立事件”中尋找“非孤立因素”的脈絡(luò),方能對(duì)癥下藥,防患于未然。